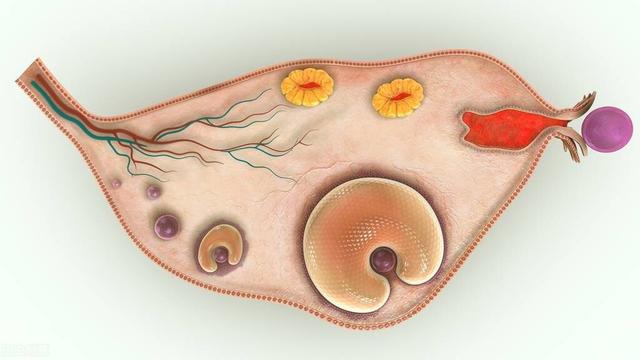原创 郑世骥

四师老师长赵增林
1964年8月 ,正是一年中最为酷热难忍的三伏天,十团八连在莎車县六十里巴扎(维吾尔语巴扎即集市)进行野营训练。师长赵增林同志带工作组来到我们连队蹲点。我在连队当班长。
赵师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他一到连队就“约法三章”: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要求大家做到的,工作组首先做到;生活不搞特殊化。刚开始,连队干部看到师长与大家吃同样饭菜有点儿“于心不忍”,就悄悄让炊事班多加个菜。赵师长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始终不动这个菜。此后,炊事班便不再加菜。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后,整个新疆军区仅仅保留了我们这一个师,驻守在北到伊犁河谷、南到昆仑山麓两千多公里的边防线上,点多线长,非常分散,不少战士当三四年兵都没有见到过师首长。起初,战士们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军姿端庄、肩扛两杠四星的师长,都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经过短暂的接触,大家发现这位仪表堂堂、看似威严的师长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头顶烈日在在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训练,他始终都坚持跟班作业,与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发现问题现场纠正,讲要领、做示范,言传身教,常常弄得浑身都是土也毫不在意。休息时,他就拿着一把扇子和一个小收音机,到各班的帐篷里坐坐。那时收音机可是个稀罕玩意儿,他一边让大家听听戏,一边与大家聊聊天、谈谈家常,询问连队的情况,了解战士们的想法和要求。戈壁滩昼夜温差特别大,他还经常深夜由组织科长陈华昭陪同到各班查铺查哨,,为战士盖被子、掖被角······

野营拉练途中,赵师长(中)与战士在一起。
大家看到赵师长这么平易近人,也都消除了顾虑,把连队训练强度大、粮食不够吃等等这些心里话,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抖落出来。有的说,最想当炊事员,这样就可以吃饱肚子;有的说,最喜欢去炊事班帮厨,可以放开肚皮吃一天饱饭。有个战士还对师长夸海口:“首长只要让我吃饱,即使再苦再累,我都不怕!”赵师长看着这个可爱的战士,笑眯眯地故意问:“真是这样吗?你可不要吹牛哟!”另一个战士立即插话说:“他是全连有名的大力士,力气大着哩!首长只要让他吃饱,就是发给他一个铁裤衩,,他都能给戳个洞!”逗得赵师长笑的前仰后合······
有道是,“人心换人心,黄土变成金”。赵师长就是这样像兄长一样,在与大家不经意的闲谈说笑中,了解到连队的具体情况和战士们的真实想法。
星期六晚上,一个“特大喜讯”传来:星期天下午饭全连不定量,大家放开吃。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别提多高兴了,都在盼望着这个“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年部队星期天都吃两顿饭。刚刚开过早饭,司务长就从全连抽了十多个“公差”到炊事班帮厨。大家从兄弟连队借来案板,就在几棵大树下面摆开“战场”,有的和面,有的擀面,紧张忙碌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五袋多面粉全都擀成了面条,整整齐齐地摊放在雨布上。
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天,连队就像过节一样,一个个喜笑颜开,兴奋异常,有的同志走路都哼着小曲儿。开饭的时间还未到,大家便早早地拿着碗,静静地坐在帐篷外面等待着。人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谁若表现得过于活跃,过分高兴,就会给人留下“没吃过饭”“没出息”的印象,遭到众人耻笑。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开饭的军号吹响,就像“盘马弯弓”地等待总攻发起的冲锋号一样。
开饭的军号终于吹响了。炊事班的两口大锅接连不断地下着面条,各班值日员排队一盆一盆地盛着面条,大家一碗接一碗地咥着面条。赵师长笑眯眯站在旁边,就像慈祥的母亲观察子女们争抢着吮吸奶汁一样,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把一碗碗面条往那个似乎填不满的肚子里倒。这顿面条吃的什么菜,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它是我入伍之后,除了过年、过节会餐和帮厨之外,吃到的头一顿饱饭,真是太过瘾、太解馋了!
这一顿饭,全连平均每人吃了二斤多面。面对这一“辉煌战果”,赵师长决定,全师从即日起在八连进行伙食管理试点,粮食不定量,大家放开吃,超支的粮食由师里补助解决。
我当兵两年多了,在连队经过的各种试点不算少,有军事训练的,有营区正规化建设的,也有田间管理的。试点往往时间紧、任务重,上级工作组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连队出大力、流大汗,加班加点,突击完成官兵体力消耗特别大。工作组就让每天午饭给大家加一个馒头,满口答应超支粮食由他们解决。可当现场会一开过,工作组就立马走人。司务长到机关找这些干部解决超粮补助问题,他们就互相“踢皮球”,找谁都不解决。无奈之下,连队只得从官兵嘴里把超支的粮食一点儿点儿地再抠回来,我们战士们对这些“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试点,可以说打内心是不欢迎的。但赵师长在连队进行的伙食管理试点,对我们来说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太实惠了,我们都拍手叫好,举双手欢迎。
这顿捞面条及由此开始的全师伙食管理试点,对于八连每个同志来说,都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我正是从这顿饭开始,彻底地告别了饥饿,从根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赵师长在我们八连伙食管理试点不久,全师所有机关、部队从1964年10月开始,就全部取消了定量分餐。这说明赵师长在我们连的试点对全师还有指导作用呢!我们既吃饱了肚子,享受到试点的“丰硕成果”,还给全师摸索了经验,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才是真正的“双赢”呢!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究竟吃过多少顿饭确实是数也数不清了,其中不乏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但都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唯独赵师长在八连蹲点期间的这顿捞面条,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永久记忆······
赵师长后来调到北疆军区担任副司令员.1983年4月29日因突发高血压脑出血不幸去世,年仅61岁。大家感到十分震惊和惋惜,至今都怀念和敬重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军队建设呕心沥血,对部属关怀备至、“爱兵如子”的老首长!

赵增林师长
附:怀念敬爱的赵增林师长
我这篇《刻骨铭心一顿饭 》见报后,老战友纷纷点赞、鼓励,赵师长远在浙江宁波工作的儿子赵建民代表全家写来情感真挚、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更使我我深受感动。我很清楚,大家夸的不是这篇文章本身,而是异口同声称赞、怀念我们敬仰的赵师长。
我最早接触赵师长是在十团八连。当时我仅是一名中士班长,与大校军衔的师长真可谓是“戴草帽亲嘴——差得太远”,我这个小兵即使蹦起来也“够不着”。因此,只能通过吃饭这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写出令我们敬仰的赵师长。
我与赵师长接触较多还是1966年调到四师作训科之后。我作为一个新参谋,可以说十分无知,啥都不懂。记得有个星期天,我在科里值班,赵师长急匆匆地来到作战室,让我给十一团起草一个“预先号令”,并讲了电报要点,让十一团抓紧准备,接到命令立即出发。我到作训科半年了,重要文电都是由老参谋起草,根本轮不到我。以前在军校虽然学过拟制“军用文书”,但都是“纸上谈兵”。这次突然要“真枪实弹”上战场,我顿时就傻眼了。我急的抓耳挠腮,仅前面两三句话我就写了撕,撕了再写,废纸堆了一桌子。咳!真是“万事开头难”啊!赵师长急得两次过来问我写好没有。他一再告诉我把刚才讲的要点写上就行了,并特意叮嘱我,他在办公室里等着,写好马上送他签发。我忙得手忙脚乱,终于把电报写好送给赵师长。他笑眯眯地一边耐心修改,一边给我讲修改理由,短短上百个字的电报,竟改的面目全非,有的段落等于首长又重新写。修改好后,我期待着首长签发,他却笑着对我说,因等不及了,我已经写好让机要科发走了,你把这份电报拿回去抄整齐再好好看看,权当一次学习吧!我当时面红耳赤,非常羞愧。赵师长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责怪我的话,就像父母亲在教儿女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样,那样耐心,那样慈祥。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赵师长对我们年轻人是多么关心、爱护并寄予多大的希望啊!从此我便“知耻而勇”,虚心向首长和老参谋请教,刻苦钻研参谋业务,不断提高了工作能力。
库车新营区建成后,师首长和司令部同在一幢平房里办公。首长办公室在东头,作训科在西头,首长上下班都要路过作训科,经常到科里坐坐,有时与我们谈工作,有时与我们聊天,与师首长接触的机会就多了。那时全师星期天都吃两顿饭。我看到赵师长常常吃过早饭,就端着保温杯,从家属院来到办公室,一呆就是大半天,有时我们吃过下午饭回到办公室,他才端着保温杯回家属院,其勤奋敬业精神让我们这些“单干户”(部队对未结婚或家属未随军干部的戏称)十分敬佩。
当年,师后勤部在库车县东河塘公社(八区)有个农场,师里多次组织机关、直属队官兵徒步拉练去农场劳动。赵师长与年轻官兵一样背着背包徒步行军,战士们多次抢他的背包,他都不让,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密切。这个农场是在戈壁荒滩开垦出来的,盐碱特别严重,需要在田间挖很深的排碱沟排碱。赵师长开始和大家共同劳动,警卫连的战士看到首长年龄那么大,就夺过工具把他硬拉上来,说什么都不让他干,还像下命令一样,让他负责给大家烧水、送水,弄得他毫无办法。有时他趁着给战士递水的机会抓住砍土镘刚干两下,战士们就把工具抢走,三推两拽把他拉上来。他只得坐在沟排碱沟上面,一边烧水,一边给大家背诵“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大家都十分惊讶。赵师长毕竟已四十多岁了,平时工作那么忙,能背这么多文章,他要下多么大的功夫啊!对赵师长更加敬佩了。全师官兵都喜欢听赵师长讲话、作报告,他常常是不拿讲稿,滔滔不绝地讲国内外形势、讲评全师教育训练情况,他的讲话生动风趣,有骨头有肉,没有那些干巴巴的空洞说教和官话、套话,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大家听的津津有味。“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这都是赵师长孜孜不倦、勤奋刻苦学习的结果啊!
赵师长顾全大局,党性特别强。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新疆分为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部队虽不参加“四大”,但受社会上严重派性、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影响,官兵中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观点。赵师长是从二十一军跨军区调到新疆的,因而看问题比较超脱和客观,不像有人那么绝对。有的部门领导由此对他产生偏见,在下面散布过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想必赵师长也耳有所闻,但他不为所动。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和高风亮节,始终严格按师党委统一的口径发表讲话和处理问题,一如既往地抓部队训练和管理,保持了全师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再次赢得了全师官兵的敬佩和赞扬。
还有一件小事我印象很深。师直工兵营二连裴炳山连长带领连队外出执行任务时,为抢救战士而光荣牺牲。师里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悼念这位舍身救人的英雄。库车县两派各级群众组织为争高低,送的花圈越来越大,有几个竟超过机关干部宿舍平房。政治部领导请示师党委的花圈做多大?赵师长指示我们不赶潮流,仍按通常大小制作。在众多的花圈里,四师党委的花圈虽然最小,最不起眼,,但却显得更加肃穆、庄重,受到官兵好评。
赵师长经常带工作组下连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科长每次都是派老参谋陪同,由于我资历太浅,竟没有轮到过一次。否则,我会从赵师长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使我的军旅生涯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我对此十分遗憾。
我入伍后,在连队摸爬滚打了两三年,得到了扎扎实实地锻炼,学到了许多以前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我由衷的感到,连队确实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大学校。
我热爱文学,喜欢写一些东西。我在学生时代就给报刊投过稿,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脱离生活,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内容空洞。后来,我就没有再投稿了。
来到部队以后,丰富多彩的连队生活,又重新燃起了我的写作热情。特别是当了文书以后,因为管理着全连武器弹药和战士档案,就有一个单独的房间,由个人支配的时间也比较多了。那个时期,各级对训练要求特别严格,每周都要求各连队逐级上报训练的详细情况,不仅要有训练的各种统计数据,还要有一周训练的典型事例和好人好事。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我就经常到训练场、到各班了解情况,然后综合上报。因此,我对连队训练情况掌握得比较多。除了完成情况上报任务以外,我还写成稿件,送到团政治处宣传股。负责宣传报道的干事侯立志同志非常热心,我每送一篇稿子,,他都逐段逐句一边耐心帮我修改,一边给我讲修改的理由,,对我帮助很大。他将全团的稿件集中寄往《新疆解放军》报(刊头由朱德委员长题写)。那时的社会风气特别好,报社认稿不认人,还没有找熟人、走后门那一套。不长时间,我写的稿子就陆续见报了,有反映连队好人好事的,如《好管家》边志先、《受人称赞的理发员》杨秀先的事迹,也有反映连队野营训练遵守民族政策、搞好军民团结的,如《杏子熟了的时候》尽管篇幅都不长,大多是一些“豆腐块”, 但连队自己的事情上了报纸,大家十分高兴,都争抢着报纸看,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写稿的热情更高了。我不但写些新闻报道,也写一些诗歌。我结合自己当兵的亲身感受,写了一首诗《我站在高山之脊》,寄往报社后,很快就发表了。如今底稿已经丢失,我只记得开头几句:“我站在高山之脊,双手紧握武器。狂风吹我不倒,像青松傲然挺立……”1963 年冬天,连队正在喀喇昆仑山下进行冬季野营训练,我们居住在维吾尔族老乡家里。当听到我军击落美制国民党 U—2 型飞机的喜讯以后,我非常激动,连夜写了一首欢庆这一伟大胜利的诗歌寄往报社。整首诗我早记不得了,只记得诗里有这么几句“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齐喝彩……刚刚还张牙舞爪,转眼间兴尽悲来。一记响亮的耳光,正打中肯尼迪要害……”一个多星期后,报纸就登出来了。在 1964 年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我写了一首《敌人磨刀我磨刀》的诗歌,先后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上。
1966 年初,在军区步兵学校参谋训练队即将业时,我利用春节放假休息的三天时间,写了歌颂爱民模范卡德尔的对口词《时代的尖兵》和《我叫领巾》两篇稿件,寄出不到一个星期,《新疆日报》就先后全文发表了。
在写稿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实践是最好的课堂,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身临其境,亲自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才有吮吸不完的乳汁,才有永远写不完的素材,也才能写出水平高、质量好的东西。
当干部以后,我虽然很少再投稿了,但在连队打下的写作基础,却使我受益无穷,对我此后调到机关工作帮助很大,特别在军用文书写作方面,尤为明显。无论是写训练情况报告和总结,还是写军事学术论文等,我都尽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以便了解掌握更多的情况,使材料尽量做到内容充实,事例生动,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我执笔起草的1967年全师训练总结,呈送给赵增林师长审阅后,他不仅一字未改,还在上面批示“很好”,这在以往也是很少见的,一度在机关传为佳话。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我参加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调查组到十四军等参战部队调查研究,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打仗要有两手准备》的评论寄往《解放军报》,很快就在军报头版显著位置以《头脑中要有辩证法》为题刊登出来。我写的两篇军事学术论文曾获得全军优秀论文一等奖。
我在连队利用自己学过音乐、会识乐谱的特长,经常给大家教一些新歌,平时连队集合唱歌或营、团组织歌咏比赛,我都担任指挥。每当营、团组织文艺会演,我和宋宝斋等几个同志就抓紧编写节目,认真组织排练,在全团汇演中还得过奖呢!那年,我调到咸阳部队工作,宋宝斋听说后就来找我。他一见面也不说话,让我猜是谁?他看我茫然的眼神,知道我没有认出他,就唱了几句当年我们在六连自编自演的歌曲,我听到熟悉的旋律才恍然大悟,原来眼前这个陌生人,竟是当年在六连当兵的老战友啊!我们分别三十多年了。
往事如烟。几十年军旅生涯中的那些陈年旧事,许多已经记忆模糊甚至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但在昆仑边关短短两三年的连队生活,却像刚刚发生在昨天似的,始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仿佛再次回到遥远的昆仑边关,再次回到连队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家”,感到那样的亲切温暖,那样的美好幸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