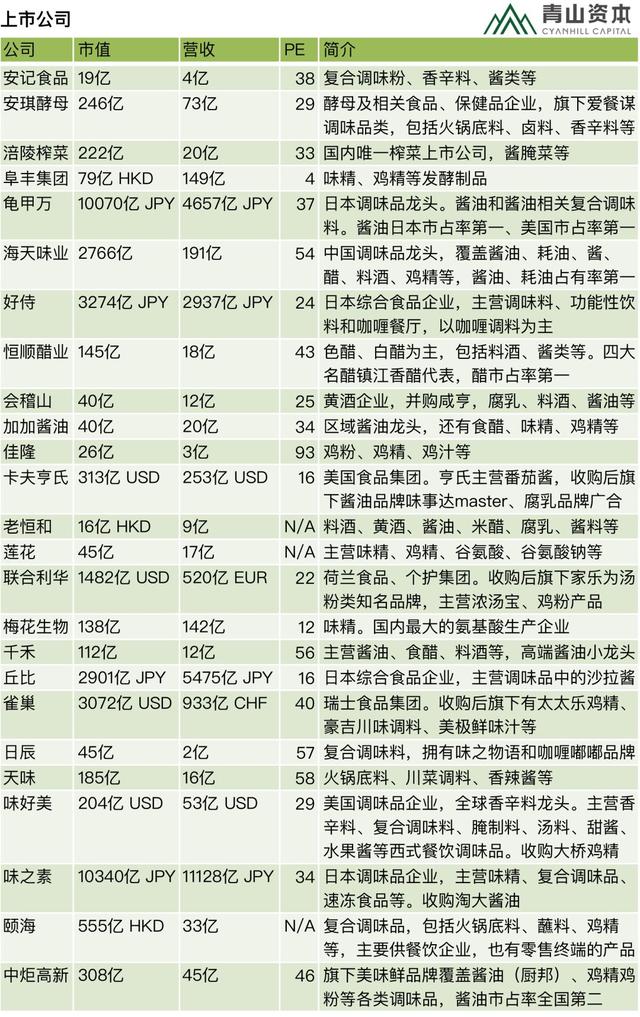鲁迅不仅有着很强烈的个人审美偏好和很好的艺术修养,也非常重视生活中的设计细节,对于书籍装帧更是格外用心,他十分注重大力提携青年设计师,其中最偏爱的当属陶元庆——这位年轻设计师的作品让人深深感到,民国虽然过去很久,但几乎所有的艺术格局,那时就基本奠定。
当时的书籍封面绘图大多是刻板印刷,单色或双色套印,颜色、线条、画面复杂度都大受影响,因此呈现效果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但“戴着镣铐”,反而成全了这一时期封面设计的简洁、朴拙、凝练,强烈。当色彩和形状轮廓都无法随心所欲的种种条件限制,追求意境的东方传统精神反而得到了抽象与升华。
1924年《苦闷的象征》是在鲁迅好友许钦文介绍下陶元庆为鲁迅作品画的第一个封面,据说鲁迅特别满意,就让许钦文介绍邀请陶元庆过去聊聊,之后陶元庆的名字更是频频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成为鲁迅最为欣赏的封面装帧设计师。

这幅封面由一个半裸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舔三刺戟的尖头便化而成。
钱君匋评价道:
郁悒的线条藏着无底的悲哀,我们看了毛管自然会竖起来。
1926年的《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封面也由陶元庆设计,画面上的三个人同坐一把椅子上,看着逐渐西移的落日。那种天之将晚,想有所行动,又缺乏果敢决心的精神状态,大概和鲁迅《彷徨》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恰到好处的贴合吧。

鲁迅说:
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许钦文记录道:
对于《彷徨》封面画的评价很高,包括德国的一位美术家Eche。这画好就好在太阳的不圆,抖抖抖抖地移下地平线下去的样子,画出了落日的动态。
1926年的许钦文小说《故乡》封面,大概是鲁迅最喜欢的一个。这就是他一再提起的《大红袍》。为了这幅封面,鲁迅甚至亲自挑选并用自己的版税帮助《故乡》结集出版。《大红袍》中矗立持剑的女性形象,以其无限丰富的时代寓意直到今天依然感染力十足。
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青年一样,陶元庆也处于极其困窘的人生境遇,甚至买不起作画工具,这幅图画在用两个拆开拼拢的信封上。

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记录道:
那本是个‘恐怖美’的表现,去其病态的因素,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态京戏的武生,加以便化、统一表现就是了。
1926年的鲁迅杂文集《坟》,鲁迅再次拜托他喜爱的陶元庆作封面,强调想要的是“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只是陶元庆依然采用了“坟”的意象,用抽象、几何却高度凝练的坟的意象作为封面,鲁迅于是非常满意。

这幅看似简单的插图,其实有极多的讲究,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钱君匋《陶元庆论》
底色的外形非常特殊,棺棹与坟的排列及古木的地位都是最好的设计,不可移动一点。全幅画的色的情调颇含死的气息
鲁迅自己还为《坟》画了一张扉页,就是那个著名的“猫头鹰”形象,鲁迅自己也以夜枭自居,这只猫头鹰,真是不可多得的传统图案设计的经典。

绘画和设计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却又截然不同,区分度很高。总的说来,设计更强调高度凝练抽象的思维方式和对所表现事物克制而饱满的情绪,绘画的好坏则和更多因素相关。绘画大师大多设计感非常出众(画匠画师画手往往欠缺这一点),但好的设计师却不一定能画出优秀的好画——毕竟设计为“物”服务,强调语境而非自我表达。陶元庆和鲁迅的概念感和美感都非常好,他们无论绘画技巧,都有成为一流设计师的潜质。
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封面,一位古装白袍的女子,从花园里抱回一根残枝,枝上的花朵已经凋零。橘黄的底色加重了人生秋意。这幅插画放在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具有现代感。

陶元庆画封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碍于人情,他一生的创作,大多和鲁迅、许钦文两位相托有关。即使这样,陶元庆也很讨厌给人画封面。鲁迅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托他画许多书面,实在难于再开口了……”,“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甚至在书信中用“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这样的措辞,可见他也知道画封面这件事对于陶元庆极勉强。以至于陶元庆最好的朋友许钦文相求画封面,“八册书就闹了八场。”
对陶元庆来说,画封面无非是闲余,但这雕虫小技却成了他的主要身份,也许真是“无心插柳”吧。
陶元庆一生,为许钦文画了最多的封面,除了著名的大红袍,还有《鼻涕阿二》、《蝴蝶》、《毛线袜》、《若有其事》等等,其中《一坛酒》还是许钦文在陶元庆死后拿他的一副作品充代的遗作。
在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鼻涕阿二》,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少女的神韵,据说其故事内容是极其悲惨的“多出来的女孩”的一生,对比之下,更见惊心。

《鼻涕阿二》(1927)

《蝴蝶》(1928)

《毛线袜》(1926年)

遗作《一罐酒》以上都出自许钦文的小说封面。
对民国整体文化界的任务而言,大约不脱“新”“旧”,“东”“西”,转型中的中国需要迅速跟上世界文明的脚步,此时,任何的尝试,哪怕极不合逻辑,都有一定合理性。而陶元庆本身的气韵,让他在这方面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一致认可。民俗学家钟敬文称赞陶元庆的画。
他的绘画的取材、表现等方法,虽大概属于西方的,但里面却涵容着一种东方的飘逸的气韵。
鲁迅也强调:
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这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陶元庆绘于1925年的《唐宋传奇集》、《工人绥惠略夫》等,都暗合着这“民族性”“东方气韵”的追求。

《唐宋传奇集》(1925年)
素朴静穆,古风悠然,画中人物、马车、旗幡,排列有序,很有意趣,这种用写意的手法表达性情也是他特色之一。

《工人绥惠略夫》(1926)
强调不读中国书,一生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鲁迅,和他谈论的“竹林七贤”一样,不是讨厌“中国文化”,而是爱得太深。他个人不仅有着浓浓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气质,审美品位也极其追求“民族特色”。他曾大量购入老拓本、汉画像等古代纹样,将其融入自己的设计中,终于成就民国一流设计师之名。


鲁迅亲自设计的两个封面,可以看到他明显的审美情趣。
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陶元庆因伤寒引发心脏衰竭遽然去世,终年不过三十七岁。他一生都以“自然”画家自居,很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做“图案”画家也就是封面设计师,由此抗拒画封面。他画的封面不算很多,但却弄巧成拙恰巧成为影响深远的封面作者。
不过陶元庆并没有从设计中获利,他一生贫困,付不起房租而连续搬家等,最后因暑天蜗居在又热又闷又小的居室中患病死去。他死后,鲁迅为他寄去了300元的治丧费用,为他选择墓地,又联系各方出资为他办画展,办纪念堂。不过纪念堂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洗劫,画作一张也没能保存下来。而他的墓地,也因为要修植物园,被夷为平地。陶元庆,终归是什么也没能留下来。所幸他不情愿画下的封面,因为出版物的发行,才能让人一睹他的设计才华。

1925年《往星中》
高度抽象的图案,有点涂鸦感。

1925年《出了象牙塔》
依然是简洁,很有个性的线条风格。
一九三一年,鲁迅在陶元庆赠他的《元庆的出品》一书上题笺:
此漩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稀,留此为念。乌呼!
是的,草露易晞,但毕竟,还是有些什么活在今天我们的记忆里,并成为铸就我们灵魂的新的文化资源。
在世界读书日,顺带推荐一本挺有意思的小书,总体上来说对于普通读者文字有些深艰,不过读进去会觉得角度有不少洞见,毕竟,未来五十年,“民族主义”恐怕会成为与我们朝夕相对,必须面对甚至是最迫切的重大问题。

民国设计文化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