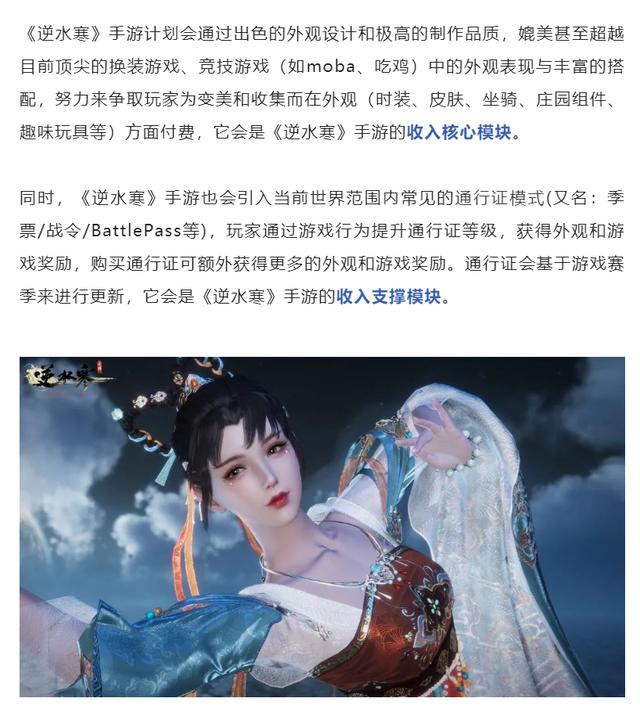作家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走过西班牙人烟稀少的空心村,想到数千年前,从库纳克萨战役败退的色诺芬。那位来自异邦的骑兵将领,面对尼尼微的废墟,感到一无所知的陌生。
类似的陌生感击中了莫利诺。生长于斯的西班牙人莫利诺,面对国境线内荒野连片的空心村,同样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从一个名为弗恩蒂杜埃尼的村庄出发,驱车前往30公里之外的马德里工业区,城乡风貌以一种泾渭分明的方式区隔开来——行至城乡分界之处,凛冽的高原风貌骤然消失,稠密的交通网络和大商圈瞬时撞向眼前。
1950年代,西班牙开启农村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百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在城郊与棚户定居。短短二十年间,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两三倍,内陆地区上千座乡村随之消逝,广袤的土地荒芜,孤零零排列着空心的村庄。
空心村和城市大约各占西班牙国土面积的一半,后者却容纳了超过80%的人口。
“西班牙‘无人村’里为数不多的居民感到自己被抛弃。”莫利诺将之形容为一种“大伤痛”。在一些空心村,公共生活难以为继:医生一周只出现一次,废弃的学校里还挂着1931年退位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徽章,村长居住在一百公里外的城市里,只在周五下午来到村里行使职权。一周只开业几个小时的酒吧,是村镇里为数不多的“公共服务”。
城市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但移居于此的农民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大伤痛”:无家可归的心理感受弥漫在进城一代中间。他们携带乡土经验进入城市,发现自己从平原和山脉上生长出来的生存之道,在这里丝毫派不上用场,城市对于自己终究是异乡。他们的后代,只能从古老的节庆、习俗、方言中捕捉父辈生活的精神遗迹,遥远得如同神话。
“存在着两个西班牙。”莫利诺毫不讳言,空心村是西班牙的国中之国。2022年3月,他的纪实作品《断裂的乡村》中译本出版。他在书中形容,那个城市化、欧洲化了的西班牙,和那个荒芜的、被称为无人村的西班牙,差异大到已然是“不同的国家”。

《断裂的乡村》作者,西班牙作家塞尔吉奥·德尔·莫利诺(受访者/图)
传统的西班牙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
1979年,莫利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城乡移民家庭。母亲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人,出于“至今也弄不清楚”的理由,放弃了大城市里不错的工作、朋友圈和稳定的生活,来到索利亚省的一个市镇定居。父亲则在索利亚省的一个村庄长大。两人在市镇定居的行为颇令邻里讶异。当时,“这个市镇本地的年轻人都跑去了马德里”。
在瓦伦西亚沿海的一个村庄,莫利诺度过了漫长的童年。他和哥哥享受着宜人的气候和开阔的自然条件,脑海中却始终追问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没有人住在那里?”
原来,蒸汽机时代,父亲的家乡一度是铁路运输枢纽上重要的停靠站点,火车在此处卸运煤炭、更换车头。电气化时代到来后,火车不再在此停留,本土所有的就业机会都失去价值。后来,莫利诺的姑姑卧轨而死,在他看来,姑姑的死亡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象征,这个村镇走向消亡了。
莫利诺做过十年新闻记者。在《阿拉贡先驱报》工作时,他经常探访西班牙的无人村。当记者的那些年,他发现西班牙的无人村在外界的想象中,有时涂抹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成为远离城市卑琐生活的田园牧歌。
莫利诺去过一个名为塞拉布罗的村庄。1970年代后,这里曾沦为一片废墟。1990年代,陆续有人抱着挣脱城市管理束缚的愿望来到此地,想要建设一个理想国。在西班牙国内,这种过惯了城市生活而选择去乡村的定居者,被称为“新农村人”。据《纽约时报》报道,西班牙一些地区曾有过“rurbanismo(逆城市化运动)”的风潮,在一个名为维拉纽瓦的村庄,“新农村人”在此种植作物、自给自足,有时用蔬菜换取商品或者公共服务。也有艺术家们修复本地的农舍和房屋,来此建设艺术家社区。
不过,莫利诺去塞拉布罗时,这个由“新农村人”重新建设起来的村庄,最初的建设者早已离开。他发现,不少新农村人表现出“偏执的惊恐”,因为安保系统不像城市那么发达,他们时常感觉到对环境的不安。
2007年,莫利诺去一处名为法戈的空心村跑新闻。在那个仅仅容留31人生活的小村庄里,他碰上的是外界对于空心村想象的另一面——充斥着暴力与蒙昧的“黑色西班牙”。
莫利诺到达法戈时,那里不久前刚发生一起凶杀案——死者是“恶霸”村长,居民们普遍觉得他把村里搞得民不聊生,凶手正是一位新农村人。“包括后来的凶手在内的一些居民认为,村长在法律和行政上的步步紧逼,击碎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梦想——他们来到这深山里就是为了清静自由。”
一位女性告诉莫利诺,她去往附近的人家时,要经过一条荒无人烟的森林小径,在一次和市政厅产生争端后,“随时感觉生活在威胁之中”。有人在冬季的夜晚难以成眠,“总觉得冬季的某个夜晚会有人破门而入,了结他们的性命”。
看上去,这是传统部落生活逻辑的延续。莫利诺却不这么认为。
“传统的西班牙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哪怕是最偏远的村庄也已经受到了全球化影响。”莫利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生活在法戈的多数村民,仍然依靠储备柴火熬过冬季。冬天住在空心村,与城市生活的区别更多在于休闲娱乐方式的匮乏,“城市的各项娱乐(显然)有助于释放情绪……但大多数小村庄没有有线电视,能接收到的广播频道很少,网速也很慢。”因此一些生活在小村庄的人们,烦恼基础公共设施不完善,不能和现代生活接轨,要求改善交通、通讯和吸引投资,不受歧视地生活在21世纪。

作家莫利诺将他记录西班牙空心村的书命名为《断裂的乡村》,他形容,西班牙城市和空心村的差异,大到已然是“不同的国家”(受访者/图)
“这代人总觉得自己是外人”
快速的城市化和缺乏身份认同的农民移民涌入,在过去数十年间,为西班牙的城市建设带来了问题。
“在拉美许多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着所谓的‘贫民区’‘棚户区’。棚户区人口主要由新来的农村移民构成,他们无力建造或购买住宅,只能用纸板、树枝、铁皮、芦席等材料搭成窝棚。”学者韩琦曾在论文中介绍,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农民移民能够安居的地方,环境不佳。作为欧洲国家的西班牙,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有类似问题。
“一般来说,这里(西班牙)的城市景观是丑陋和功能性的,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就被一些丑陋的建筑和廉价住宅包围着。”莫利诺在萨拉戈萨居住时,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周围的建筑几乎没有古罗马时代的遗迹,都是20世纪以后建造的。“这在欧洲(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因为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有很强的历史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关照。”莫利诺遗憾提到,除了几个代表性的古城(比如萨拉曼卡、塞维利亚、托雷多、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西班牙在发展中并不尊重自己的历史。
百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心理上感受到融入的困难。“这代人总是有一种无根的感觉。随着年岁的增长,他们的乡愁也在堆积,出生之地在心里逐渐变成了一个神话。”
莫利诺介绍,自己的祖父就拼命想要回到“那个失落的天堂”——一个只有不到100名村民、名为布维耶尔卡(Bubierca)的小村庄。但对莫利诺来说,布维耶尔卡成了一种“非常抽象、模糊不清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记忆只能停留在后一代人的脑海中,成了一种离开了实践经验的纯粹文学叙事。”莫利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小在城市街道上生活的第二代移民继承了父母的乡村记忆,继承也带来融入的困难。莫利诺察觉到,农村的身份认同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负面的情感。“他们全盘否认这样的身份,声称自己是城里人。”莫利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是一代反叛自己农村出身的人。”
语言是难以融入城市的一道关卡。西班牙人为自己保存了多样的语言而自豪,哪怕是阿兰语(奥克语的一种方言)这样使用人数少于1万人的语言,至今仍保持活力。
但这种多样性却引发了语言排外和歧视。
在巴塞罗那,农民移民几乎没人会说本地城市人口通用的加泰罗尼亚语。马德里南部的街区和市镇,聚居着大量的农民移民,他们的西班牙语带着明显的拉曼恰和安达卢西亚口音,与土生土长的马德里人有很大不同。
“这些移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马德里人。”莫利诺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当一个移民要去市中心,会说“我要去马德里”。“可他们住的地方明明也隶属马德里。”
“不再让一个人成为二等公民”
“今天的西班牙人相信,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一样复杂。”莫利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是不可逆的,目前的经济模式,已经不需要建立在传统农业和畜牧业基础上的村落。”
因此他并不寄望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期待的是,空心化不再成为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国内对城市与乡村有着对应文明与愚昧的高下判断。据莫利诺介绍,现代西班牙的源头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存在强烈的关联,这两个帝国都建立了繁荣的城市。“文明”一词便源自于拉丁文civitas,意思是“城市”。“罗马人和阿拉伯人都认为农村只是为城市提供给养的地方,是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之间的那片空白地带。农村不是文明的一部分。”
“今天,对一个人来说,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差别是很大的。理想的状态是实现平等的原则,居住地不再成为影响一个人行使权利的因素,不再让一个人成为二等公民。但我们确实可以让生活在西班牙无人村的居民感受到平等和尊重,让他们不被歧视。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需要平等对待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人。”莫利诺说。
除了确保最低限度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关键的维持是文化和教育在村庄内运转。1931年,西班牙曾经存在过一个名为“教育使团理事会”的组织,这项存在了五年的“农村拯救计划”,试图将文学、艺术、电影,以及基于此搭建的教育体系带往西班牙最为偏远的地区。
“西班牙有一个延伸到最偏远村庄的巨大的公共自行车网络,当地的一些机构也会组织音乐会、讲座,在即使很小的地方维持文化中心的运转。”莫利诺介绍,近年来有新兴的力量填补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在西班牙一个名为乌鲁埃尼亚的村庄,最新人口为100人。过去的十来年间,在本地政府的支持下,这里存在着11家书店,“比学生的数量还多”。人们试图在这里建设一个理想的文化社区。
公共教育系统同样为空心村输送师资。西班牙教育系统在招收年轻教师时,会将他们派遣去一些偏僻的空心村做临时教师。但由于工作临时性强,很少有教师真的住在村里。多数情况下,这些年轻教师得早起驾驶60公里甚至150公里前往村庄上班。“他们把城市生活的映像带去农村,就像上门推销员所拿的一份小样品,可是很少有人在当地找到归属感。”
在莫利诺看来,这些外来的帮助力量,始终无法解决核心的问题。“在那些地方不能形成一个文化社群,因为能够组织和培育它的人在每天下班后就离开了。如果中产阶级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教师也包含在其中)不住在村庄内,不能使当地的文化生活活跃起来,那村庄还是会慢慢死去。即使获得再多的投资,它也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展示橱窗。”
(感谢许卉、Clara Fernández Garcia 为本文提供西班牙语翻译)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