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后商
在2017年雅布提奖长篇小说类一等奖作品传记小说《马查多》(Machado)中,巴西作家西维亚诺·桑提亚戈(Silviano Santiago)回顾了巴西文学大师马查多·德·阿西斯最后四年的生活,他的艺术、孤独和癫痫病。行将终老的阿西斯,在两名女佣的帮助下,努力和癫痫症共处,与此同时,巴西第一共和国对中央大街开始了现代化的改造——就在不久前,阿西斯还被调到了工业部。私人生活和历史变迁汇集于《马查多》,阿西斯渴望成为现代人,但又是以保守的、不公正的方式。例如,阿西斯从社会意义上否认自由劳动的存在,但又从本然意义上不声张地反对奴隶制,阿西斯的矛盾恰恰是一个典型。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年生于里约热内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头像被印在面值一千的纸币上。1897年创办巴西文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生前身后发表了众多作品,涵盖了全部文学体裁,共计十部长篇小说,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戏剧作品,代表作有《沉默先生》《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金卡斯·博尔巴》等。
1.文学上的世界主义者
阿西斯生于1839年,是混血人油漆匠和白人洗衣妇的儿子,其血统中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但他一生都在努力隐藏自己的黑人身份。他的教育生涯很短,只读过小学,他的启蒙来源于一位拉丁神父和刻苦的自学。有资料可查,阿西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穷人刊》上的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斯的职业生涯从国家印刷局起步,此后又先后做过校对员、编辑、撰稿、主编助理等——为报刊等媒体撰稿是阿西斯坚持一生的事业。三十多岁的阿西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彼时的巴西还是佩德罗二世治下的巴西帝国,尚未废除奴隶制。阿西斯先后在农业、商业、公共工程部履职,官至公共工程部局长——考虑到拉美文人的政治色彩,这种行为并非迂腐的表现。
在文学方面,阿西斯无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在文学谱系上,他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没有那么明晰——他分头吸纳了巴洛克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归根结底,他使自己面对了诸多经典“问题”,面对那些永远都不过时的“问题”。阿西斯不拘泥于类型,他写诗歌、短篇、长篇、戏剧、评论等等,且以一种现代又古典的方式杂糅了诸多弱类型。在宗教、政治、文学、生活等方面,阿西斯的思想是自由的,近乎无政府主义的。阿西斯的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怀疑色彩,并不是存在主义式的,而是后巴洛克式的——于他而言,绝望和希望是一个词。阿西斯是隐藏式的他者,又是神秘化的自我。作为一个隐藏式的他者,他有着洞察事物和走入读者的可能;作为一个神秘化的自我,他召集着他所书写的事物和思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阿西斯的每个段落簇——看得出来,阿西斯的作品是累进式的,是夹杂着空白的——都会让作为读者的我们平静下来,让我们追随他的叙述成为更真实的自我。
2.文学的本质是人的普遍意义
“我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偶尔参加一次舞会,去去剧院,或听演讲,但大部分时间是我独自度过的。我活着,任其事业和光阴流逝;在奢想和失望中时而心绪不宁,时而心灰意懒。我撰写时政文章,从事文学创作,向报刊写文章或诗篇,竟然还得了个善辩和诗人的美名。当我想到已当了议员的罗伯·奈维斯和侯爵夫人维吉丽亚,我自问为什么不能成为比罗伯·奈维斯更好的议员和侯爵。‘我更有价值,比他的价值大得多’,我望着鼻子尖说了这番话。”阿西斯在其经典《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中如是自我剖析。
贵族布拉斯·库巴斯在其死后怀旧忆往,也邀请我们体味他雍容又枯燥的人生。他伪装成斯特恩的巨人,但更偏狭,更执着于高贵又可怜的感情、优越又懊悔的腔调。本书的喜剧效果几乎是一种古典文学变形后所产生的,不过,阿西斯在处理喋喋不休和快速切换的时候,显得更为克制和有所保留,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对象是世情的可笑和人的多变,而不再是巴洛克式的半虚构世界。布拉斯·库巴斯,或者阿西斯总是在节外生枝,总是变了面具,变了情感,变了指向,透过那些自命不凡、脆弱的表演、各一半的快乐和忧郁——“我是人,我的大脑是个舞台,上面演出各种剧目,神圣、严肃、活泼的话剧,高雅的喜刚,形形色色的闹剧、悲剧、滑稽剧。”在这之下,是在爱情和事业上遭遇重重挫折和失败的布拉斯·库巴斯。这个故事既不轻松愉快,也不狡猾肮脏,而是带着笨拙的平衡,有如新生。这位死去的作家在死亡之后开始了他最本真的书写,这个游戏讲的是作家的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阿西斯是失败的,因为他从未真正实现预想的在地性尝试,或者某种现实主义的效果,在这一点上,他比不上巴尔扎克之类的典型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拥有现实主义的所有元素,甚至更欧洲、更古典,但它几乎没有焦点,无法被一个确定的类型所统摄,缺乏一种整体的美感——阿西斯过于隐藏其意图的、过于书面的、独特的反讽加剧了这个结果。从中,我们还能发现他的自恋、他的注意力缺失症、他的对经典的依赖、他的艺术上的强迫症。苏珊·桑塔格所认为的阿西斯的成功正是基于上述的失败,潜在的失败,于是阿西斯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古怪的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巴西现实角度、现代主义文学角度等等——阿西斯总是轻易超越了这个想象所能承载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人士的过度成功几乎总是一种更大的偏执、更存在主义的言说,这也是为什么桑塔格认为贝克特部分失败的原因。
典型的说法是,阿西斯没有提供给我们一种真实的巴西,无论是巴西的自然风光,还是巴西的历史状况,后者最重要的例子是他对巴西的蓄奴问题避而不谈,而巴西是全世界最大的蓄奴国,而它直到1888年才废除奴隶制,是最后一个废奴的国家。就此而言,阿西斯对于现实问题是采取退让态度的。1873年,阿西斯发表《巴西当代文学的创新:民族性本能》一文,提倡民族主义只是文学的一隅,文学的本质是人的普遍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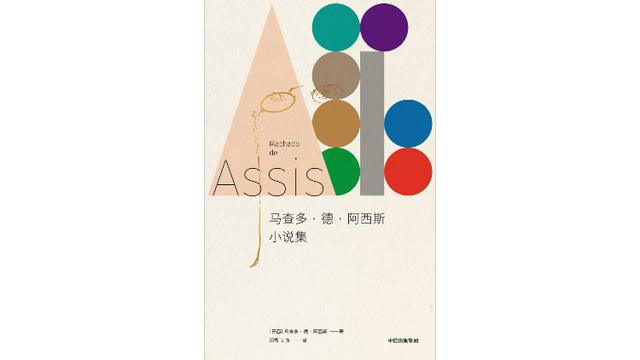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作者:(巴西)马查多·德·阿西斯,译者:闵雪飞,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7月
3.阿西斯代表着巴西真正独立的一代
阿西斯带我们回到了不确定年代的巴西,回到了已然的巴西。在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故事被拉前,他的角色几乎都存在于早于他的历史时期,并且这些人物的感受方式也几乎总是古老的,原始的,乃至于过于精致的。然而,阿西斯仍然带着他的角色狼奔豕突,将他们带到历史的舞台之上,或者让他们征服整个历史。对于最后的获胜,阿西斯是深信不疑的,因为他是布局谋篇的人,更因为他是世界文学的学徒。
《马查多·德·阿西斯小说集》的第一篇《精神病医生》发生在“摇铃宣告”的时期,负责摇铃的人走家串户,收罗所在地的信息,最后他会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将信息公布给所有人。伊塔瓜依当地的医生西芒·巴卡马特相信科学的精神,他的信条是“科学也毫不例外,它是项天天不断探索的事”。他发现了医学里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域,精神病学,它曾经是一座孤岛,现在被医生证明是一座大陆。精神的健康才是医生最值得尊重的事业,西芒·巴卡马特医生如是说:“人的精神是一个巨大的蚌壳,我的目的是从中取出珍珠。”医生将病人大致分为两类,暴躁病人和温顺病人,然后再细分……在后来的治疗中,病人会按照自己所患病的类型接受诊治,诸如诚实病、忠诚病等。西芒·巴卡马特为了收治病人,建造了绿屋,顾名思义,绿色的屋子,是当地最为豪华的宅子,后来还得到了扩建。
绿屋建成之后,西芒·巴卡马特就收治了很多病人,诸如爱修辞学的年轻人、施舍钱财的科斯塔,甚至于他的夫人艾娃丽丝塔。由于医生的“荒谬”的收治行径,人们团结在理发师波菲里奥的周围,进行了一场针对绿屋的叛乱,“玉米粥叛乱”。叛乱影射了巴西历史上一次未成行的叛乱,蒂拉登特斯(Tiradentes)率领下的“米纳斯密谋”(Inconfidência Mineira),只不过前者成功了。但旋即,发生了复辟。西芒·巴卡马特的声望在政权更迭时期达到了高峰,绿屋也借机收治了镇长和议员,但旋即,绿屋里的病人都被释放了。新的治疗方案和立法方案得到了实施。故事的最后,取得了智识和精神双重平衡的西芒·巴卡马特离开了人世,葬礼很有排场。
《精神病医生》的故事是多维度的,你可以说它讲的是精神病的发现,也可以说它讲的是科学至上只会带来巴士底狱般的荒唐,也可以说它讲的是政治的黑暗和翻覆,诸如此类。最重要的是,故事从不止一种发生的方式,它是关于故事的故事学,关于类型的类型学。在资料和素材方面,阿西斯从未逾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但在寓意方面,阿西斯是完全普世的。阿西斯的一个信念是,在社会和人的战役中,胜利的总是社会,正如《精神病医生》所昭示的。社会的胜利没有看上去那么令人不堪。在阿西斯的另一本小说中如是写道:“这或许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没有下决心要改变它,那就只能承受这一切,在这个社会里照常生活。”最顺从的人,像西芒·巴卡马特医生那样,或许才是最疯狂的,他们竟然将日常当作病态。
阿西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保守的怀疑主义,它既有道德的维度,又有美学的维度。在道德维度上,阿西斯是超然的、成熟的。比如,他反写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圣经》中的美与纯洁不过是更大的邪恶而已,而我们所需的是更大的美好,是真正的上帝。再比如他借人物之口对“人性主义”的呼唤,带着双重的意味,“请求助于人性主义,它是容纳精神的伟大胸怀,是永恒的大海,我潜入海底去捞取真理。”在美学的维度上,阿西斯代表着巴西真正独立的一代,他彻彻底底地将那些原本属于西方、属于宗主国的文本改造成了新的文本。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新的现代主义。阿西斯是反歌德的,又是和歌德相对应的。他的怀疑主义还没有抵达虚无主义,出乎启蒙世界也没有多远。
早在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发表《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之前,阿西斯就做出了惊人的食人主义的实践——在西方世界之外寻找更好的天堂。“只有纯粹的精英成功地实现了肉欲的食人,它在自身内部承载着生命的至高意义,避开了弗洛伊德指定的一切疾病——教义问答的疾病。”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如是说。吉尔贝托·德·梅洛·弗雷雷(Gilberto de Mello Freyre)后来在《主与奴》(Casa-Grande & Senzala)为混血人所做的证明正是一个起点。而现在,阿西斯那张有胡须、显赫的、混血的画像出现在纸币、邮票、巴西文学院。
作者|后商
编辑|张进
校对|李世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