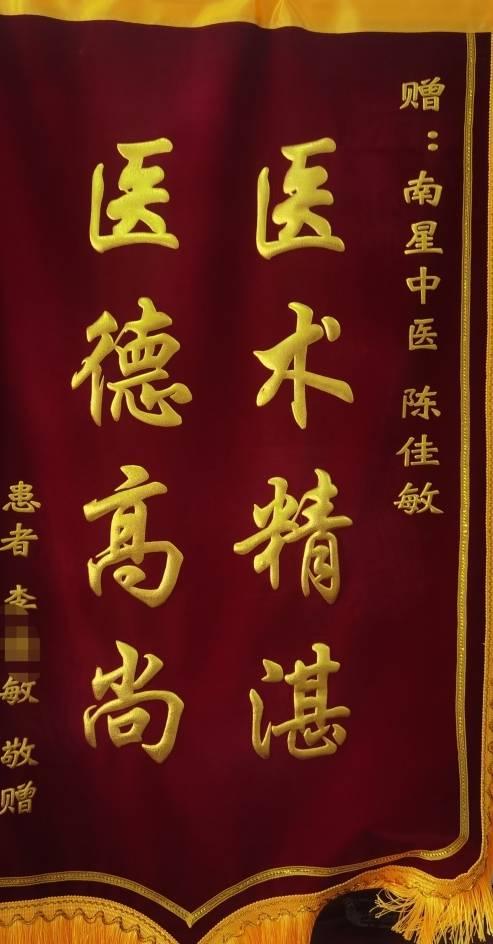作者:页清
2020年的这场大疫,注定要载入史册。2月3日,NATURE杂志在线刊出一篇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表的研究论文,该论文显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nCoV-2019的序列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也就是说,引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
在这篇论文出来之前,就已经很多人将蝙蝠列为第一嫌疑人,并愤怒指责那些贪吃野味的吃货:“大过年的吃什么蝙蝠啊?”事实上,蝙蝠这种相貌奇特,长着双翅的小生灵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特殊角色。
一、中国古人如何看待蝙蝠?
由于蝙蝠的颜值惨淡,常人对它的直观印象都不会太好。它长着老鼠的脑袋、尖利的獠牙,却又背负着一对翅膀,栖息于阴暗的洞窟中,常常发出尖利的叫声,令人不寒而栗。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蝙蝠一直不受待见。
《旧约全书·申命记》记载,耶和华曾告诫摩西等人“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却不允许吃蝙蝠,显然是将蝙蝠视为危险的不洁之物。
由于有的蝙蝠会吸食动物的鲜血并带来疾病,西方人又将它与恐怖的吸血鬼传说相联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蝙蝠在西方文化中形象相当负面,至于超级英雄蝙蝠侠,那都是现代的事情了。

▲电影中的蝙蝠侠形象
与西方不同,蝙蝠在中国文化中却有着光鲜的一面。这是因为在汉语中,蝠与“福”同音,代表着吉祥如意。早在新石器时代,心灵手巧的远古先民就制作出有关蝙蝠的工艺品。到了汉代,蝙蝠图案已经成为常见的纹饰。
到了明清之时,蝙蝠的福气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清代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中说:“虫之属最可厌莫若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文字的读音与字义本身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但蝙蝠确实意外受益于中文的谐音之妙。

▲商代的玉蝙蝠
有学者认为蝙蝠在中国成“仙”,在西方成“鬼”,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其实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古代中国文人对蝙蝠的看法也不全是吉祥如意,也有着负面的评价,只不过这种评价更多是从道德立场出发。
在古人看来,蝙蝠昼伏夜出,终日躲藏在黑暗之中,是胆怯的表现;它兼具鼠类与鸟类的特征,似鼠非鼠,似鸟非鸟,阵营不明,是一个妥妥的“骑墙派”。在重气节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这样的“贪生怕死”、“立场模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少不得用文学创作来编排蝙蝠。
三国时期的大文豪曹植曾写过一篇《蝙蝠赋》,开篇便写道:“吁何邪气,生玆蝙蝠。”将蝙蝠视为邪气所化。曹子建还特别讥讽蝙蝠“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的不伦不类和“不容毛群,斥逐羽族”可悲下场。

▲日本游戏《三国志》中的曹植
白居易在《洞中蝙蝠》一诗中说蝙蝠“远害全身诚得计,一身幽暗又如何”,批判蝙蝠的“消极避祸”。
明代冯梦龙更是在《笑府·蝙蝠骑墙》中嘲讽了蝙蝠的“两面派”行为。在故事里,百鸟之王凤凰过寿,众鸟都前往祝贺,只有蝙蝠不至,说自己是兽非鸟,等万兽之王麒麟过寿时,蝙蝠还是不到场祝寿,说自己是鸟非兽,后来凤凰与麒麟相遇时,慨叹“今世风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实无奈他何”。显然,冯梦龙是相当瞧不起蝙蝠的。
蝙蝠虽然长着翅膀,但终究是哺乳动物,这在今天是常识,古人却很难看得清楚。至于蝙蝠的那些习性,只是生物本能而已,实在没有必要以人类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蝙蝠冷嘲热讽,看似是对蝙蝠不屑,其实只是借物喻人,表露对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之徒的憎恶罢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古人认为蝙蝠有极高的食用价值。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记载:“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食之神仙。”又据葛洪的《抱朴子》载,蝙蝠“此物得而阴干莫服之,令人寿万岁”。
《古今注》等都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但在古代医学与生物学极其不发达的情况下难免有局限性,即便是《本草纲目》这样的不朽医药巨著也远非完美无缺,因此今人无需苛责。
中国古代追求成仙万岁者数不胜数,可真的有人成功吗?对于这样的追求,魏文帝的这两句诗再合适不过:“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读史使人明智,历史为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但愿这样的教训是最后一次。
看来,古人对蝙蝠的评价都是随自己的需求而变,无论是“福”的化身还是“不禽不兽之徒”,都是人类自身的寄托与譬喻而已,与自然界的蝙蝠又有何干呢?
二、蝙蝠成为近代“反面教员”
蝙蝠的形象在古代便比较复杂,直到晚清之际,蝙蝠也没有离开文人们的视野。
1905年的《国粹学报》第5期与第7期分别刊登了两篇奇文,《哀蝙蝠文》与《招蝙蝠文》。
《哀蝙蝠文》的作者不明,但作者描述他亲眼看到在上海高竿掣电之下,“蝙蝠成群投明而舞,磁石所引摄,力不胜,陨坠赴地,无复奋飞”。也就是说蝙蝠因电线杆等现代文明的产物而受到影响,在磁场的误导下精疲力尽,被人类踩死。
看来,作者已经对蝙蝠辨别方位的原理有所了解,并寄予了一些同情。不过,他也替蝙蝠“猥不爱惜,外铄其中,依附末光炙之而热炎炎之势,罔顾其后终陨躯命,何异自戕”感到悲哀,既悯其遇,更憎其愚。
分明是人类的扩张危害到蝙蝠的生存,作者却说是蝙蝠自寻死路,未免有些不厚道,不过他也说明是“余怀有托,文以哀之”,又是一托物言志,自然意不在蝙蝠。

有趣的是,很快又有人写《招蝙蝠文》相呼应,这篇文章词藻更加华丽,也更为晦涩难懂。“繄蝙蝠之赋形兮,实托体于穴虫。去纷烦之土壤兮,乘窸窣之微风。应升阳而夏见兮,怀沉阴以蛰冬”……
想必大家也看出这篇赋的意蕴深刻。两篇文章“意有所寄,不必强同也”,都是文人借物抒怀的佳作,蝙蝠只是作者的寄托罢了,更与寻常百姓关联不大。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传媒的逐步发达,蝙蝠的形象开始深入国民心中,意外成为启蒙国人的重要工具。
前文已经提到,蝙蝠因为“尽似鼠形,谓鸟不似”的不伦不类,被古人视为“骑墙派”,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近代中国,骑墙派自然遭到更猛烈的口诛笔伐。
1902年,《大陆报》转载法国人威诺伦的小说《蝙蝠中立》,通过西方人之口狠批了蝙蝠的首鼠两端。
1918年的《神学志》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喻蝙蝠》的文章,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鸟与兽的战争中,蝙蝠一直保持中立,一会儿说“我有二翼”,一会儿说“我有四足”,最后被鸟类野兽“共逐之”。
这个故事与冯梦龙所写其实大同小异,但作者更明白地阐明了内涵,明言这里的蝙蝠指的就是在南北对立中左右逢源的政客、军人、“调和人”。
中国古代便推崇“忠贞不二”在,民国之后,万象更新,但许多基本的道德准则仍得以保留。在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紧张对峙的时刻,投身政治者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反复无常、立场不坚者必定为双方所嫌恶。
因此,蝙蝠在新时代又成为抨击政治投机心理的重要载体。
1925年,庄淳正作《斥蝙蝠式之中西医》,鼓励国人“与实验主义之中医携手,而不可与蝙蝠式之中医共语”,显然是以蝙蝠比喻批判某些不伦不类、只知西医皮毛而不知精髓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救亡图存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原本左右逢源的蝙蝠更是成为缺乏气节的象征,被用于敲打通敌动摇者。而且,由于大众传媒和教育启蒙的迅速发展,蝙蝠不再是几个文人的抒怀之物。
救亡图存,要从娃娃抓起,国难当头,儿童成为国家的希望。1931年的《小朋友》杂志刊登童话《蝙蝠为什么没有巢》,在故事中,蝙蝠同样利用自己似鼠似鸟的特点,先投靠鹰,后投靠狐,但都因习性太坏被赶走,最终落得无巢可住、倒挂梁上的下场。
此时,东三省正被日军荼毒,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样的童话故事指向鲜明。
1932年,张振亚又在《桃坞》杂志作雄文《讨蝙蝠文》,在扑杀两只蝙蝠后,张振亚还历数蝙蝠之罪,“二蝠汝死固惨,然所以至此者,汝自作自受之因果也,设汝安于分谨乎行,不作首鼠之两端,不冒禽兽之杂种,束身自爱,潜匿避人,则吾曹将纵汝辈走”。
与《讨蝙蝠文》同版的文章还有赞颂爱国将领马占山的《黑马将军传》,在此特殊时期,《桃坞》刊登这篇文章显然意有所指。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危在旦夕的时代,也是国际局势纷繁诡谲的时代,国人同样以蝙蝠来比喻一些国家反复无常、投机侥幸的外交方针,比如1935年《上海党声》的《英国之蝙蝠外交》,以“蝙蝠式”外交讽刺英国对德、意、日侵略集团的妥协退让。
1939年,《新民族》发表短评《想做蝙蝠的日本》,指出日本与德、意结盟不过是蝙蝠式的投机取巧,并非真心帮助德、意对抗苏联,果不其然,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日本非但不曾出兵苏联策应德国,反而冒死将美国拖入战争,狠狠地出卖了一把“盟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御侮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目标,一切通敌、投机者都将被顶上历史的耻辱柱,蝙蝠又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反面教员。
1943年胡生静在《广东儿童》发表童话《没有国籍的蝙蝠》,虚构出狡猾的蝙蝠挑拨鸟、兽、鱼三族的全面战争,却又凭借自己兼具鸟兽特点的外形从中渔利,在长达九千万年的战争中
蝙蝠“凭着它特有的两翅和四脚,到处可以跑可以飞,鸟呀兽呀都会好好的招呼它”,“到处受到很优裕的招待,它希望这个战争要长久打下去”。
最终,鸟、兽、鱼签订协议,都不给蝙蝠国籍,从此蝙蝠成了没有国籍的怪物。
1943年是关键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势在这一年变得相当明了,开罗会议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阵营的关键成员,战争也早已由中日两国的孤立战争演变为两大国际阵营的殊死决战。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着左右逢源、渔翁得利的投机分子将成为全民族、全世界的公敌,等战争结束的那天,也将成为没有国籍的蝙蝠,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声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除了位列同盟国阵营外,还有一个汪伪政府加入轴心国集团,无论二战结局如何,中国都是战胜国。
这种看似机灵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人提出,这个人就是周佛海。1941年6月,周佛海得知德、意两国宣布承认汪伪政府,便在日记里突发奇想:
“目前英、美、俄及日、德、意两战线已分明,谁胜谁败,尚未可知……今南京加入后者,则中国双方均有关系,所谓脚踏两只船,无论胜败谁属,中国不至吃亏。”

▲周佛海
对于周氏的脑洞,学者邓野评价其为标准的汉奸理论。
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中日战争必将演变为国际性的战争,在两大阵营中,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任何投机的余地,与日本血战多年的惨痛经历也不可能让中日有“并肩作战”的可能,否则只能是“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让中国蒙受污名与耻辱罢了,周佛海这样的说辞不过是自作聪明与文过饰非而已。
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在珍珠港事变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对日、德、意三国宣战,并率先提出同盟国阵营成员不得与敌人单独媾和,与周佛海相比,高下立见。外交固然需要权谋机变,但终究不能违背正道。
在民族大义与国际正义面前,想做投机取巧的蝙蝠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蝙蝠仍然扮演着“反面教员”的角色。1946年《新上海》刊登《李香兰化作蝙蝠东京飞》,以蝙蝠比喻凭借日本国籍逃脱汉奸审判的李香兰。1947年《礼拜六》又有《杨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时局展望)》,同样是斥责某些人的投机外交思想。
蝙蝠的“非鸟非兽”纯粹是物种天性,但在民族主义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种原罪,有罪的不是蝙蝠,而是投敌者。
三、蝙蝠的形象逐渐趋于正面
说了这么多,似乎蝙蝠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很糟糕,但其实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国人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蝙蝠。
早在1873年,西方传教士就在《教会新报》以科学的态度向中国人介绍蝙蝠,指出蝙蝠“最喜食者惟蚊,蚊生多之处,蝠亦生多,此又大益人矣”,世间生灵“无一物虚置”。
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理性认识蝙蝠,尤其是蝙蝠捕食蚊虫对人类的裨益。比如1930年的《少年》杂志刊登棠洲的《科学故事:蝙蝠》,向读者介绍蝙蝠虽然长着翅膀,但其实是哺乳动物,且会捕食蚊虫,对人类有益。
同年,《学生杂志》刊载《蝙蝠的捕蚊数》,公布外国科学家堪培尔的统计结果:蝙蝠一昼夜可捕杀蚊子3635只。1940年,周性初也在《科学趣味》上发表《蝙蝠:蚊的敌人》。

▲《蝙蝠的功劳很大》,来源:《儿童知识》1948年第26期。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落后,因此许多有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蝙蝠的仿生学价值。
雷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发明之一,其工作原理与蝙蝠飞行时的声波导航有相似之处,饱受日机轰炸的中国虽然根本不具备制造雷达的技术,但对这种新式防空装备颇感兴趣,也注意到蝙蝠与雷达的关系。
在《中国的空军》、《文摘副刊》、《一四七画报》等杂志中都有专文介绍蝙蝠的导航原理与雷达技术的联系。
1948年,国统区已是风雨飘摇,但上海的《中华少年》还是在科学问答栏目耐心解答了读者郑志中的疑问,即蝙蝠是否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
这篇问答告诉读者,“与其说蝙蝠是科学家发明雷达的前导,还不如说人们想到雷达和蝙蝠的相似”。
不仅国统区的杂志关心这个问题,解放区杂志也是如此。1949年,张子瞻在《新儿童世界》发文《你看见过蝙蝠吗?它是雷达的始祖》,向小读者们介绍雷达与蝙蝠的联系。在这场战争中,国共立场分明,但追求科学与现代化是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中国古人曾认为吃了蝙蝠可以成仙,但在近代医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国人早已注意到蝙蝠会传播疾病。如1932年,冯文华在《医学与药学》译介海外医学新闻《蝙蝠与狂犬病》,警告国人蝙蝠可传播狂犬病。
1939年,《上海医事周刊》刊登《医学文摘:蝙蝠传播瘈咬病》。1940年,《广西农业通讯》发文宣称吸血蝙蝠会在家畜间传播烈性的口足病。
试想,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蝙蝠会传染疾病早已成为常识中的常识,现在还想着吃蝙蝠的人,就是穿越回民国也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到了民国末期,蝙蝠的习性与益害处事实上成为连儿童都需要掌握的常识。这背后反映的其实是国人科学精神和卫生意识的加强。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从点滴之处做起。
简要回顾蝙蝠在中国历史中的形象演变可以发现,这种长相不太讨人喜欢的小动物一直在陪伴着中国人。
不管是首鼠两端的投机者形象,还是吉祥的福星,亦或是民族主义的特殊需求,国人对它爱恨情仇,无非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蝙蝠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试问,到底是蝙蝠危害了人类,还是人类危害了蝙蝠?
长着翅膀不是蝙蝠的错,错的是首鼠两端的投敌者;传播病毒也不是蝙蝠的错,错的是违背自然规律与敷衍卸责的人。人类是最具智慧的生物,也是最容易犯大错的生物,蝙蝠何辜?自然界何辜?
参考资料:
1.《教事近闻:格物探源》,《教会新报》1873年第230期。
2.《小说:警世奇话:蝙蝠中立》,《大陆》1903年第3期。
3.《哀蝙蝠文》,《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5期。
4.《招蝙蝠文》,《国粹学报》1905年第1卷第7期。
5.包容:《喻言:蝙蝠》,《神学志》1918年第4卷第3期。
6.董启明:《蝙蝠》,《小朋友》1923年第64期。
7.莊淳正:《斥蝙蝠式之中西医》,《广济医刊》1925年第2卷第8期。
8.《蝙蝠的捕蚊数》,《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7期。
9.魏丽敏:《蝙蝠为什么没有巢》,《小朋友》1931年第485期。
10.冯文华:《海外医事新闻:蝙蝠与狂犬病》,《医学与药学》1932年第1卷第6期。
12.张振亚:《讨蝙蝠文》,《桃坞》1932年12月。
13.《英国之蝙蝠外交》,《上海党声》,1935年第1卷第35期。
14.《蝙蝠传播瘈咬病》,《上海医事周刊》1939年第5卷第49期。
15.《想做蝙蝠的日本》,《新民族》1939年第4卷第2期。
16.周性初:《蝙蝠:蚊的敌人》,《科学趣味》1940年第3卷第2期。
17.胡生静:《没有国籍的蝙蝠》,《广东儿童》1943年第5卷第2期。
18.《蝙蝠与雷达》,《中国的空军》1945年第88期。
19.《发明雷达的始祖:蝙蝠》,《一四七画报》,1946年第2卷第12期。
20.虚丹:《李香兰化作蝙蝠东京飞》,《新上海》1946年第38期。
21.苏迅:《杨柳外交和蝙蝠外交(时局展望)》,《礼拜六》1947年第94期。
22.王庄:《农业文献摘要:蝙蝠危害家畜》,《广西农业通讯》1947年第6卷。
23.《蝙蝠的功劳很大》,《儿童知识》1948年第26期。
24.《答读者郑志中君》,《中华少年》1948年第5卷第17期。
25.张子瞻:《你看见过蝙蝠吗?它是雷达的始祖》,《新儿童世界》1949年第27期。
26.邓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27.陈涛:《吉祥文化下的蝙蝠图案研究及符号化解读》,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08年。
28.张智艳.:《传统蝙蝠纹样艺术符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工业大学,2009年。
29.焦成根,叶锡铮:《从蝙蝠形象看中西文化精神》,《美术大观》200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