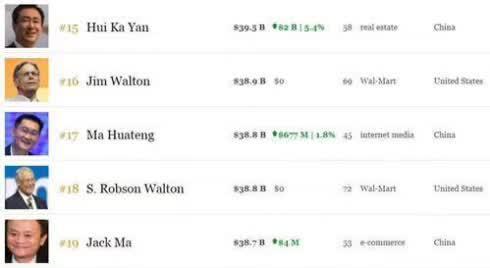作者简介:王曾瑜,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古代开封城边界?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古代开封城边界
作者简介:王曾瑜,1939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在金朝和伪齐的统治下,开封城从公元1130年到1233年金代的开封城的历史。其中包括南宋时开封最后的陷落,开封宋宫的火灾和金朝的重建,金宣宗在蒙古军的威胁下南渡,将开封作为国都,金朝亡国时的开封守卫战,以及金朝统治下的开封城市面貌。本文论述金朝对北宋开封的城市格局没有多大更动,但开封始终没有恢复北宋时的繁盛。北宋与南宋之交,金朝末年的两次兵祸,使开封市民深受苦难,城市也受到很大摧残,但作为城市建筑精华的宫殿,还是大致完好。
关键词:开封;金朝;龙德宫
狗尾续貂,与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的巨著相比,本文名符其实是一条狗尾。但是,笔者在阅读明人的《汴京遗迹志》后,确实产生了续貂之念。开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包括五代的梁、晋、汉、周与北宋五朝,到南宋初最后陷落,计210年,而伪齐作为国都, 金朝作为南京,金海陵王一度打算作为国都,金宣宗南渡后,开封又正式成为国都,直至被蒙古军所破,计104年。金朝统治下百余年的沧桑变故, 即使在编修《汴京遗迹志》的明人李濂眼里,已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网罗的载籍少得可怜。因此,笔者打算依据宋金元的记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补苴工作。
一 宋朝开封陷落前后
金军在天会四年(公元1126),即宋靖康元年冬,其实只是攻破开封的外城。经历战斗的损失,金军所剩“大约不过八万人”〔1〕。 在平原旷野,女真骑兵纵横驰骋,比宋军步兵确有很大优势,然而若下城与开封大约百万军民巷战,则将是胜负难卜的消耗战。故史称宰相何 “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2 〕。他们只是占领外城四壁,不断勒索马匹、兵器、财宝、女子等,最后通过一些宦官、开封府尹徐秉哲等,又将赵氏皇族一网打尽。即使宋钦宗被骗入金营后,“诸城夜有金人下城虏掠者,亦为百姓掩杀甚多”〔3〕。以和议佐攻战,回避巷战,正是表现了金军将帅的聪明。
天会五年,即建炎元年,金朝立伪楚政权后,匆忙在夏季前撤兵。由于南宋首任宰相李纲的极力举荐,宗泽才先后出任开封尹、东京留守等差遣。宗泽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在他镇守开封的一年间,这个饱受劫难的城市才恢复了城防和生机。他在奏中说,“京城四壁、濠河、楼橹与守御器具,其当职官吏协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厉不懈,增筑开浚,起造辑理,浸皆就绪”,并“已修整御街、御廊、护道杈子,平整南薰门一带御路”〔4〕。 特别是在建炎元年冬到二年春,金帅完颜粘罕(宗翰)发动凌厉的攻势,而宗泽坐镇开封城中,从容指挥宋军,在开封四围与金军激烈搏战,开封城却固若金汤,连一个金兵也不能抵达城下。正月元宵前后,开封城内“张灯五日,暂弛夜禁”,“士民游观如平时”〔5〕。 这与一年前宋钦宗及其无能的宰执守城,适成鲜明对照。宗泽力请宋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但宋高宗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前去。
这个68高龄方才统兵的文臣,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终于因心力交瘁,忧愤成疾,与世长辞。宋高宗的小朝廷在发表新留守杜充的任命时,告诫他“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6〕。 这是宋廷对这个爱国者的评价。杜充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他最初是下令决黄河,以阻金军,接着,又不听部将岳飞的苦劝,率领当时最精锐的东京留守司军南逃。但狡猾的杜充既要逃跑,又不敢承担放弃国都的罪责,而将守城的责任推诿给副留守郭仲荀,又“檄直龙图阁、知蔡州程昌为留守判官”。郭仲荀也如法炮制,“遂率余兵赴行在”。程昌到开封后,“食尽”,吏士“乃挑野菜而食”,也逃回蔡州,最后是上官悟在建炎三年八月权京城留守。上官悟屡杀劝降者,应当说还是个克尽己责的留守。〔7〕
天会八年(公元1130),即宋建炎四年二月,在“河南之地尽已陷没”的情况下,“唯京师甸内县犹为国家守,粮食乏绝,四处皆不通,民多饿死”。因部属作乱,上官悟最后被迫出奔而遇害,开封终于在十四日丁亥被金朝占领,“时在京强壮不满万人”〔8〕。 这座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尽管濒临荒绝的惨境,却仍不屈地反抗。据金方记载,当月二十五日戊戌,“汴京乱,三月丁卯, 大迪里复取之”〔9〕。三月丁卯为二十五日,可见这次反抗斗争竟持续了一个月,成为宋朝开封史上最后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扉页。可惜因载籍的缺略,人们已无法知其详情。金将大迪里则应是大姓的渤海人。
二 伪齐建都与金朝重占开封
正好是在开封陷落的当年,金朝扶立了伪齐刘豫政权。最初,伪齐以大名府为都城,阜昌三年(公元1132),即金天会十年,宋绍兴二年,方迁都开封。伪齐在开封前后六年,对这个城市还是作了一些改建。
例如阜昌五年,由殿帅许清臣拆毁了著名的道教景灵宫,此处原为宋太宗晋邸旧址、宋真宗出生地,是宋朝视为最神圣的道宫之一,规模宏大。许清臣“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为二十八段”。阜昌六年,又拆毁了宋徽宗时以秘书省改建的明堂,“得金龙之金四万两,大铜钱三百万”。翌年,刘豫“改明堂基为讲武殿,开上安门(改安上门)为众安门,朱雀门为明昌门,景龙门为照远门”。阜昌八年,又“改保康门为清远门”。然而就在当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完颜兀术(宗弼)等率金军由内城的“梁门(阊阖门)外登城”,派兵守宫城的“宣德门,东华、左、右掖门”,闯入讲武殿,将刘豫押“出梁门,囚于金明池”,金明池已在外城之郊。〔10〕
从某些记载看,在伪齐治下,开封城的荒凉衰败,与昔日全盛时已有天壤之别。估计里城之内,大约还像个城市,而在里城与外城之间,其实已同荒郊一般。金天眷二年(公元1139)至三年,即宋绍兴九、十年间,宋金初次议和,金朝一度将包括开封在内的河南之地,归还宋朝。据宋朝官员王伦、楼炤等所见,在开封宫城之内,大体还保持旧观,但出了宫城北的拱宸门后,“时京城外不复有民舍,自保康门(宫城南偏东)至太学,道才数家,太学廊庑皆败,屋中惟敦化堂榜尚在,军人杂处其上,而牧彘于内堂下。惟国子监以养士,略如学舍。都亭驿栋牌犹是伪齐年号。琼林苑敌尝以为营,至今作小城围之。金明池断栋颓壁,望之萧然也”〔11〕。所以前述金朝废伪齐时,完颜兀术(宗弼)等出入开封,是以内城为准。此外,在外城西金明池以南著名的琼林苑,又另外筑一个小城,作为驻兵之用。这是金朝占领宋朝土地后常见的做法,因为城市太大,其实缺少兵力防守。
宋朝得到开封后,按理说,岳飞军区距离最近,但宋廷绝不愿命令岳飞分兵驻守,只命武将郭仲荀“充东京同留守”,“以张俊兵一千”前往,后又“召仲荀赴行在,仲荀因与刘豫之众五千七百余人南归”〔12〕。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即绍兴十年五月,金朝毁约,完颜兀术(宗弼)率大军突入实际上是不设防的开封,留守孟庚只能拜降,完颜兀术(宗弼)“入城,驻旧龙德宫”,即宋徽宗退位后的旧居。〔13〕此后,岳飞率军大举反攻,“以其军进至朱仙镇,距京师才四十五里”。完颜兀术(宗弼)只能放弃开封,“夜弃而出,北遁百里”〔14〕。金方的记载也承认,岳飞班师后,完颜兀术(宗弼)方“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15〕从此开封就全归金朝统治。
由于金朝国都上京会宁府远离中原,故在中原地区另设行台尚书省。《金史》卷55《百官志》载:“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完颜兀术(宗弼)在死前一直领行台尚书省事。当时汴京也专设官署,如任熊祥任开封少尹、行台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赵元任同签汴京留守事。〔16〕在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公元1150)“罢行台尚书省”前〔17〕,开封是金朝南方的统治中心。
三 金朝中期的开封城
金海陵王是个雄心勃勃的君主,立志要成为中原皇帝。他不仅迁都燕京,还将祖坟也搬到了大房山,“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18〕,简直是犁庭扫穴一般。贞元元年(公元1153),开封府正式定为南京。贞元三年五月,“南京大内火”。这场火灾看来相当大,“烧延殆尽”。金海陵王为此重责有关官员,“留守冯长宁、都转运使左瀛各杖一百,除名”。副留守郭安国“及留守判官大良顺各杖八十,削三官。火起处勾当官、南京兵马都指挥使吴濬杖一百五十,除名。失火位押宿兵吏十三人并斩”〔19〕。金海陵王是个没有民族偏见的人,从这个名单看,大良顺是渤海人,冯长宁原是伪齐官员,南人,郭安国是郭药师的儿子,渤海人,而左瀛又是左企弓的儿子,是辽朝汉儿。
金海陵王重修南京宫殿,按宋方一种记载, 是从正隆元年(公元1156)到四年,负责官员是梁汉臣和孔彦舟,梁汉臣“本宋内侍陷虏,每思报仇”,其实是藉此耗竭金朝国力。〔20〕梁汉臣可能就是梁珫的字,按金方记载,“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使珫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珫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21〕。金方记载也未说孔彦舟主持修建,只说他在“正隆五年,除南京留守”。〔22〕宋方另一种记载则说是“己卯(正隆四年)春三月,遣左相张浩、右参政〔敬〕嗣晖”营建。〔23〕
然而据《金史》卷5《海陵纪》,卷83《张浩传》,卷89 《梁肃传》,卷90《高德基传》,是在正隆三年十一月,“诏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四年,又命渤海人、户部郎中高德基“与御史中丞李筹、刑部侍郎萧中一俱为营造提点”,官员梁肃也“分护役事”,高德基“转同知开封尹”。正隆六年初,金海陵王命令李通对宋使说,南京“营缮将毕功”。不久,金海陵王就迁都南京,又随即攻宋,这应是比较确切的记录。重修南京宫殿,大约用了不到三整年的时间。
这次重修开封宫殿确是耗资巨大,“大发河东、陕西材木,浮河而下,经砥柱之险,筏工多沉溺,有司不敢以闻,乃诬以逃亡,锢其家”〔24〕。“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25〕宋方记载说,金海陵王“起天下军、民、工匠,民夫限五而役三,工匠限三而役两,统计二百万。运天下林木花石,营都于汴。将旧营宫室台榭,虽尺柱亦不存,片瓦亦不用,更而新之。至于丹楹刻桷,雕墙峻宇,壁泥以金,柱石以玉,华丽之极,不可胜计”〔26〕。
北宋包罗大内的宫城原先只有五宋里,但到宋徽宗时,诸如艮岳、延福宫、龙德宫等建筑,已将宫殿区延伸到内城以北。在内城正北的景龙门外,景龙江当时实际上成了内城的北濠,而“景龙江北有龙德宫”〔27〕,成为宋徽宗退位后的住所。此外,宋徽宗的“诸皇子日长大”,“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锡名曰蕃衍宅”〔28〕,看来又与龙德宫相近。宋徽宗在龙德宫与大内宫城之间,还修筑一道夹城。据他后来对李纲说:“本欲内禅后,于夹城中往还,抱子弄孙,不欲令皇帝频出。人主频出,则不威,此本意也。”这道“夹城中通宫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岳、九曲池至龙德宫后,正与金水门相接”。金水门是外城西北水门,正名咸丰水门,景龙江和宫苑池沼都是引自金水河的水源。金军初次攻开封时,“夹城中无一卒守宿,恐有奸细不测之意,故拆去,使与宫禁相绝,备不虞”〔29〕。
在金海陵王时那次将原宋宫“烧延殆尽”的大火灾中,估计限于宫城以内,而不包括艮岳以北的建筑。据宋使范成大记载,他出使经开封城中,“出(内城)旧封丘门”,“金改为〔玄〕武门,门西金水河旧夹城曲江之处,河中卧石礧磈,皆艮岳所遗。过药市桥街,蕃衍宅、龙德宫,撷芳、撷景二园楼观俱存,撷芳中喜春堂犹岿然,所谓八滴水阁者”〔30〕。金军第二次攻开封时,宋人曾凿艮岳造炮石,直到金世宗时,“河中卧石”也未得到清理。金卫绍王时的宋使程卓南归时,由外城西“入顺义门,即俗名固子门(宋称金耀门)也,循龙德宫墙,入五虎门”〔31〕。金末刘祁也说,“南京同乐园,故宋龙德宫,徽宗所修。其间楼观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发,及五六月荷花开,官纵百姓观,虽未尝再增葺,然景物如旧”。后金亡“尽毁”,唯存“熙春一阁”,“盖其阁皆桫木壁饰,上下无土泥,虽欲毁之,不能”〔32〕。金人刘仲尹《龙德宫》诗说:“碧栱朱甍面面开,翠云稠叠锁崔嵬。连昌庭槛浑栽竹,罨画溪山半是梅。”〔33〕金末完颜《书龙德宫八景亭》诗说:“刻桷朱楹堕绀纱,裙腰草色趁阶斜。谁知剥落亭中石,曾听宣和玉树花。”〔34〕龙德宫等无疑没有重建。
龙德宫等固然平时不对外开放,但从刘祁之说看来,金代仍未将其包容在宫禁之中。至于艮岳则无疑已包容在新的宫城之中了。有两处记载都谈到金宫中有“二太湖石”,一说为“敷锡神运万岁峰”和“玉京独秀太平岩”〔35〕,前一峰或说为“敕赐昭庆神运万岁峰”,“乃宋徽宗御书,刻石填金”〔36〕,这就是当年的艮岳,还保持了宋代的原貌。考古勘探也与文献记载一致,证实金朝的宫城北墙,是利用原宋朝内城北墙的中间地段修筑而成。〔37〕可知金代的宫城当大于宋朝的周长五宋里。
但原宋宫城内的建筑,因为“烧延殆尽”,就只能另建。据宋使楼钥说:“前逆亮(金海陵王完颜亮)时,大内以遗火,殆尽。新造一如旧制,而基址并州桥稍〔移〕向东。大约宣德楼下有五门,两傍朵楼尤奇,御廊不知几间,二楼特起。”〔38〕“新造一如旧制”之说,应有所据,虽然金人未让宋使参观南京的新宫。如“正殿曰大庆殿”〔39〕,则与宋殿名称全同。另一记载描写大庆殿说:“殿前有两楼对峙,东曰嘉福,西曰嘉瑞。大庆殿屋十一间,龙墀三级,傍垛殿各三间,峻廊后与两庑相接。殿壁画四龙,各长数丈,乃宣宗渡河后画。中有御屏画小龙,用拱斗斗成一方井,如佛〔宫宝盖〕。正殿盖中有一金龙,以丝网罩之,此正衙也。”此外,如“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仁安殿,龙墀、两廊皆如隆德殿规模,即宋〔集〕英殿也”〔40〕。其他殿阁难以逐一查对。
估计自金海陵王修建至金亡,开封宫殿不可能全无改变。如金世宗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五月,“南京宫殿火”。因为这场火灾,“留守、转运两司官皆抵罪”,南京路转运使程辉“降授磁州刺史”〔41〕。但这次火的延烧面有多大,事后又如何修建,已不知其详。
金朝在开封也有若干新特色的建筑,如据楼钥说,他从金中都南归,“入顺常、〔玄〕武二门。二门之间,过五丈河、菜市桥、夷门山巷口、百王宫,乃炀王球场,亲从第一指挥,旧日御龙直也”〔42〕。这段话不易理解,估计球场就设在原宋皇城司亲从官第一指挥和诸班直之一御龙直的营地。金人承辽俗,十分重视和嗜好打马球,“凡重五日拜天礼毕”,“击球”也是一种重大仪典〔43〕,故金海陵王(炀王)在开封另修马球场。南京并不作为都城,照理无须修太庙,但在“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44〕。
金朝虽然重修宫殿,向北扩大宫城,但对宋朝原有的里城和外城的整个城市格局没有更动,只是将城门改名。按金朝中期的宋使所记,外城正东的“新宋门,即朝阳门也,金改曰宏仁门”,有的记载则称“弘仁门”或“洪仁门”。里城的“〔旧〕宋门,即丽景门,金改为宾曜门”。里城北墙偏东的“旧封丘门,即安远门也,金改为〔玄〕武门”,外城的“新封丘门,旧曰安远(景阳),金改曰顺常”。外城西的旧金耀门,金改名“顺义门”〔45〕。据《金史》卷25《地理志》载:“都城门十四,曰开阳,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远,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广泽,曰顺义,曰迎朔,曰顺常,曰广智。”以上仅有顺义和顺常两门可与宋使记载相合。估计此处所载是金朝后期的情况,据金卫绍王时的《使金录》所载分析,当时宏仁门已经改名安利门,即是上述都城十四门的一门。按北宋时外城城门,连同水门九个,通计二十一门,即使东水门和西水门各有两门,也应有十九门。〔46〕可见金朝的外城门数略有减少。
据《金史》卷25《地理志》说:“宫(皇)城门,南外门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门曰丹凤,其门三。丹凤北曰舟(州)桥,桥少北曰文武楼,遵御路而北,横街也。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其门五,双阙前引。”〔47〕参对《湛渊静语》卷2引《使燕日录》,外城正南为“旧南薰门”,但未说金朝的改名, 内城“丹凤门即旧朱雀门”。
前引《金史》卷25《地理志》的文字,估计是抄自两处,“都城门十四”为一处,后一段所引即抄自杨奂的《汴故宫记》,而元朝史官失于融会贯通。但《使燕日录》却并未记载在南薰门之北另造丰宜门。其北的龙津桥,则是横跨惠民河的桥,“此水系蔡河分流,小舟往来,颇类临安内河,但船少尔”。承天门即是宋代宫城的宣德门。估计承天门也是后来改名,楼钥未提及此门更名,而稍晚的范成大《揽辔录》已提及“侧望端门,旧宣德楼也,金改为承天门”。两书都说其下有“五门”,门前双阙即是楼钥所称的“朵楼”,与《金史》卷25《地理志》可互相印证。
金朝记载开封诸门颇为混乱,有用习惯称呼,有用宋时旧名,有用金朝改名。如《金史》卷17《哀宗纪》和卷113《赤盏合喜传》所载,“上出承天门”,一作“上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御端门肆赦”,端门是承天门的别名。“西水门千户刘寿”,“开郑门,听百姓男子出入”,“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奔”,这又是用习惯称呼。“过南薰门,值被创者,亲傅以药”,这是用宋朝旧名。“以兵护宫女十人,出迎朔门”,“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出宜秋门”,这又是用金朝改名。迎朔门见于上引《金史·地理志》,而宜秋门可能是迎秋门的改名。
北宋末年,外城的楼橹都被金军烧光,后来宗泽重建的情况并不清楚。但按金末的记载,外“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乃“合抱之木”〔48〕。估计是在金海陵王另建宫殿时,将原宋宫等木材又移用于修造外城楼橹。
北宋的内城,到北宋晚期,已多年失修而荒颓。〔49〕金代看来也延续这种状况。金海陵王虽然重建了宫殿,但不可能改变整个开封城的荒凉凋残面貌。金世宗时,据楼钥说,在内“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50〕。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宏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如“羊裘、狼帽”之类。“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炀王亮徙居燕山,始以为南都,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51〕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52〕。在个体生产的农业社会,城市的发达主要依赖于农业人口能否提供充足的余粮。在黄河以南,成了中原最荒凉的地区,“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53〕,金章宗初,还是“河南地广人稀”〔54〕。当时金朝以中都大兴府为国都,其经济水平本来就不如北宋,这与北宋时以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支撑开封的繁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在金朝的统治下,开封民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范成大说:“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男子髡顶,月辄三四髡,不然亦闷痒。余发作锥髻于顶上,包以罗巾,号曰蹋鸱,可支数月或几年。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55〕原来北宋是以中原洛阳语为标准语,类似今北京语,然而据楼钥说,接待宋使的“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开封汉人在服饰方面的辫发左衽,以及礼仪、语音等方面的改变,不能不使宋使“伤叹”〔56〕。
开封作为金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自然设立了众多的官署。最初是完颜兀术辖下的都元帅府和行台尚书省,金海陵王废除这两个机构后,由于宰执张浩和敬嗣晖掌管营造宫殿,一度在南京仍另设尚书省。〔57〕金朝南方三大军区之一的河南统军司即设于南京。〔58〕金海陵王发兵攻宋时,太子完颜阿鲁补(光英)“居守,以陁满讹里也为太子少师、兼河南路统军使,以卫护之”〔59〕。在战时,开封当然是军事指挥中心,金世宗大定初,命令仆散忠义“以丞相总戎事,居南京,节制诸将”,旋兼都元帅。〔60〕金章宗末年,宋金再战,最初命仆散揆“为河南宣抚使,籍诸道兵以备宋”,“至汴”,后又命完颜老(宗浩)为都元帅,“驰至汴”,“行省于南京”〔61〕。如尚书省、行尚书省、宣抚司、都元帅府之类,虽然地位重要,却是非常设机构。
从史籍上看,开封作为南京的常设机构可例举如下:
一、河南统军司:其官员有统军使、副统军、都监、判官、知事、知法等。〔62〕
二、南京留守司:据《金史》卷57《百官志》,其长官有“留守一员,正三品,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同知留守事一员,正四品,带同知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副留守一员,从四品,带本府少尹、兼本路兵马副都总管。留守判官一员,从五品,都总管判官一员,从五品,掌纪纲总府众务,分判兵案之事”。此外还有推官、司狱等官。金朝以武立国,南京留守还掌管南京路,包括三府、十九州的军事。南京留守有时可兼河南统军使,如金世宗时,徒单习显(克宁)“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统军使”。金世宗说:“统军使未尝以留守兼之,此朕意也。”〔63〕南京留守司还掌管河防,金世宗时,同知南京留守事纥石烈邈、高苏,南京副留守石抹辉者等都负责黄河堤防。〔64〕
三、南京路转运司:据《金史》卷57《百官志》,其官员包括转运使、同知、副使、都勾判官、户籍判官、支度(度支)判官、盐铁判官、都孔目官、知法等。《金史》说:“惟中都路置都转运司,余置转运司。”然而前述金海陵王时的左瀛就任都转运使,金世宗时,“阿勒根彦忠为南京都转运使,不闲吏事”,又命刘枢“为南京路转运使事”,“以佐之”〔65〕。在都转运使之下又设转运使事为副职。看来上引《金史》之说应是金世宗以后的定制。金章宗时,张亨“迁南京路转运使”〔66〕,卢庸“除南京转运副使”〔67〕。户籍、度支、盐铁三判官,实际上应是沿用宋辽的旧制,如武都“迁南京路度支判官”〔68〕,雷渊任“南京转运司户籍判官”〔69〕,估计《金史·百官志》中的“支度判官”,只怕是将“度支”两字颠倒了。转运司是管理本路财务的机构。
四、南京路提刑司、按察司、安抚司等:金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初置提刑司”,承安三年(公元1198),命令“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四年,又“改提刑司为按察使司”,泰和八年(公元1208),又令“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70〕。南京路提刑司本来不在开封,明昌四年(公元1193),“南京路提刑司自许州迁治南京”〔71〕。据《金史》卷57《百官志》,此类机构的官员包括使、副使、签安抚司事、签按察司事、判官、知事兼安抚司事、知法等。如李完“授南京路按察使”,纳兰胡鲁刺“改南京路按察副使”〔72〕。
除以上的重要机构外,据《金史·百官志》,尚有提举南京路榷货事,南京交钞库使和副使,南京流泉务使和副使,南京店宅务管勾,南京诸仓使、副使和监支纳官,草场使、副使和监支纳官,南京提控规运柴炭场使和副使,南京军器库使和副使,作院使和副使,南京提举京城所的提举、同提举、管勾、受给官和壕寨官,南京皇城使和副使,南京街道司管勾等官。此外,如纥石烈德在金章宗时中进士后,“调南京教授”〔73〕。看来当地又办了学校。其中流泉务就是质典库,后世称当铺。金朝一般使用北宋“旧钱”,为防止铜钱南流,南京交钞库可能最初名“交钞所”,专印纸币。“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在大河以南,包括开封城,却只能行用交钞。〔74〕
金朝中期的南京开封府城与北宋相比,其人烟已今非昔比。但光凭官方的统计数,却又截然相反。北宋开封府十六县在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户数为261,117,而金海陵王天德四年(公元1152), 面积有所减少的开封十四县,户数为235,890, 到金章宗“泰和末”(公元1207),户数为1,746,210。 张政烺先生在《金史》标点本第618页注〔五〕中已指出, 最后的数字竟占当时金朝天下总户数的四分之一,不太可能。〔75〕上述记载反映古代统计数的不可信。揆情度理,从金世宗到金章宗的对宋和平时期,南京路,包括开封城内的人口应有所上升,但金章宗泰和末的对宋战争,又必然招致户口数的下降。
四 金朝后期的开封城
金章宗泰和末的宋金战争表面上是金胜宋败,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在金朝元气大亏之余,蒙古在北方崛起,金军屡次大败。新即位的金宣宗在贞祐②二年(公元1214)决策逃往南京,到天兴元年(公元1232),金哀宗出逃,蒙古军于翌年进入南京城,开封作为金朝国都,为时不到20年。
当金朝面对蒙古的强劲攻势时,政治决策和军事回旋的余地,其实已比北宋皇朝的晚年小得多。在是否南迁的问题上,金廷内是有争议的,如徒单镒说:“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76〕但力劝迁都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如完颜弼“劝迁都南京,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77〕。贞祐②二年四月,刚与蒙古讲和,“尚书省奏巡幸南京,诏从之”,七月,“车驾至南京”〔78〕。决策和行动都相当果断。
金宣宗虽然仓促南渡,正值“南京行宫宝镇阁灾”,故仍须“修南京宫阙”〔79〕。在金朝后期,开封的宫殿仍有所修缮和改建,其布局与中期相比,显然有所改变。今存有宋邹之的《使燕日录》〔80〕和杨奂的《汴故宫记》〔81〕两份文献,都介绍开封的金宫。前一份记录金朝灭亡当年时的情况,后一份写于“己亥春三月”,即公元1239年,距离金亡才六年。其中又以前一记载更详。例如太庙,当时“庙社诸祀并委中都”,“时谒之礼尽废”。就将金海陵王原来所建的太庙“修之,以袝诸帝神主”〔82〕。金哀宗时,将“试进士”的明俊殿,改名寿圣宫(圣寿宫?),让两个太后居住,但“廊庑阶庭一切仍旧”〔83〕。又如按《使燕日录》所载,大致在位于原宋艮岳附近,有“球场,有阅武殿”,球场已由宫外搬迁宫内。又如隆徽宫为“金人皇后宫”,其中有琼芳殿、玉清殿等,“此皆金主〔珣〕(金宣宗)所造,规模制度,岂敢望旧宫室万一”。
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金朝后期的开封城内“繁盛益增”,〔84〕但这种繁盛却是战乱期间的特殊情形。历史记载说,当蒙古军于天兴元年(公元1232)“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85〕,另一说是“内外死者以百万计”〔86〕,这应是逃难入城所致。《金史》卷17《哀宗纪》说,当年夏蒙古军暂时撤退后,“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最后开封城陷落,按蒙古方面统计,“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87〕。以上三个数字相加,合计约三百五十万人,其数字颇为可疑。金朝龟缩河南一隅,其农业只怕很难为开封城提供百万人以上的余粮。金朝末年守开封城,“时自朝士外,城中人皆为兵,号防城丁壮。下令,有一男子家居,处死”〔88〕。然而搜罗到的“丁壮六万”,配合军队守外城,即使不是“丁壮”的全数,当亦相差不大。〔89〕依此推算,包括临时逃难入城者,大约也只有几十万人。金朝晚年,“京城三十六坊”〔90〕,也依然沿用北宋的制度,以坊作为基层单位,而坊的数目却比北宋锐减,可能与平时的人口多少有关。
在仓猝南迁的情况下,大批的官员随着中央机构拥入开封城。元好问说:“汴京官府寺舍者,百年以来,无复其旧。车驾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为之。”〔91〕这无疑给市民带来很大的骚扰。
兴定五年(公元1221)十一月,“京师相国寺火”〔92〕。据《使燕日录》载:“寺门成劫灰,止存佛殿一区,高广异常,朱碧间错,吴、蜀精蓝所未有。后一阁参云,凡三级,榜曰资善之阁,上有铜罗汉五百尊。其寺旧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广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禅院一,东偏宝梵、宝严、宝觉律院三,慧休禅院一,寺通闤阓,往时每月八次开寺,听商贾贸易。”这是火灾后十三年的情况,当时显然不可能有财力和物力予以修复。但据《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说,相国寺等的“塑像皆大金时所作,绝妙”。
在金朝后期,开封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整修子城。《归潜志》卷7说:“兴定初,术虎高琪为相,建议南京城方八十里,极大难守, 于内再筑子城,周方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议守子城,或云一失外城,则子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筑,土脉甚坚,北兵攻之,旬余不能拔,而新筑子城竟无用也。”参对《金史》,此说并不完全确切。
最初,在贞祐②四年(公元1216)十二月,术虎高琪最早提出“修南京里城”,金宣宗说:“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朕亦何能独安此乎!”〔93〕术虎高琪的建议被否定后,翌年,即兴定元年(公元1217)七月,完颜赛不又上章说:“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极高深,今外城虽坚,然周六十余里,仓猝有警,难于拒守。窃见城中有子城故基,宜于农隙筑而新之,为国家久长之利。”金宣宗“从之”〔94〕。据《金史》卷108 《侯挚传》说:“(兴定)三年七月,设汴京东、西、南三路行三司,诏挚居中总其事焉。十月,以里城毕工,迁官一阶。”此处所谓“里城”,应就是指开封内城。当时侯挚任三司使〔95〕,也应参与了开封内城最后阶段的修建事务。在修筑内城时,原来的宋国子监、“当城所经,弗便也,坏而徙之东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96〕。
上述开封外城周长“八十里”、“六十余里”,内城“周方四十里”之说无疑都是夸大其词。据《宋史》卷85《地理志》载,“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新城周回五十里百六十五步”,这与现代考古勘探大致相合。〔97〕金朝开封外城仍沿用北宋的外城,未予更动,但由于金朝的宫城已占用内城的部分北墙,新修的里城北墙是否往北拓展,就难以断定,但也不可能达到“周方四十里”。
五 金朝亡国时的开封之战
天兴元年初的三峰山之战,金军主力被歼,其亡国的命运已不可免。然而出人意料者,是在当年的开封守卫战中,金军却仍然抵挡了蒙古军的猛攻。当时元太宗窝阔台和其弟拖雷“住夏于官山”,“留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汴”〔98〕,速不台当然是著名的宿将。
当年三月,蒙古军兵临城下,金哀宗命曹王完颜讹可出质〔99〕,但蒙古军依然攻城。金廷商议如何守城时,“朝臣有言,里城决不可守,外城决不可弃”。因为如果蒙古军“先得外城,粮尽救绝,走一人不出。里城或不测可用。于是决计守外城,时在城诸军不满四万,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经多方搜罗,“得四万人,益以丁壮六万,分置四城。每面别选一千,名飞虎军,以专救应,然亦不能军矣”〔100〕。此处又说开封城周长一百二十里,自然是错讹的。 据刘祁说:“北兵树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时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颜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盏合喜主之。东北隅稍缓,丞相完颜赛不主之。独东南隅未尝攻。”〔101 〕上引记载大体介绍了金方的防御兵力和部署。蒙古军的进攻方位主要是开封城西南,而一百多年前金军攻破开封时,却专攻东南。按《元史》记载,“塔察儿复与金兵战于南薰门”,郭侃“从速不台攻汴西门”〔102〕。 他们应是攻开封南城和西城的蒙古将领。但蒙古军的兵力和部署缺乏具体记载。
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炮有至十三梢者,余炮称是。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枝,更递下上,昼夜不息,不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103〕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 据“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为保护楼橹,金军“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网索旃褥固护之。其悬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蒙古军又“以火炮击之,随即延爇,不可扑救”,这是使用火药兵器的记录。蒙古军最初“立攻具,沿壕列木栅,以薪草填壕”。他们“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在这场残酷的攻防战中,主要还是无辜平民的牺牲。蒙古军后来又在“壕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楼橹,壕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铺,铺置百许人守之”。为了攻城,蒙古军“又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龛,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104〕。由此看来, 他们的攻城兵器和战术,与百余年前金军攻开封城时相比,没有多大差别。
金军的守城兵器有箭矢、炮石之类,“龙德宫造炮石,取宋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完颜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楼橹垂就辄摧,传令取竹为护帘”〔105〕。北宋末宋徽宗居住的龙德宫至此近乎全部拆毁, “其楼亭材大者,则为楼橹用,其湖石皆凿为炮矣”,如前所述,所剩下的唯有无法拆毁的熙春阁。〔106〕守城的金军在火药兵器方面有所发明, 震天雷和飞火枪是威力较大的火器。金兵用“铁罐盛药”的震天雷烧蒙古军的牛皮洞,“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又飞火枪注药,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军“惟畏此二物”。完颜白撒“命筑门外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以防大兵夺门”,结果却妨碍了金军“乘夜斫营”。于是“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径渡”,“杀伤甚众”〔107〕。
开封的守城人力显然相当紧张,所有的平民男子都充“防城丁壮”,“家居”者“处死”,连“太学诸生亦选为兵,诸生诉于官,请另作一军,号太学丁壮”, 后来“朝议”讨论, 将太学生“发为炮夫”〔108〕。在金哀宗出宫慰劳将士时, 太学生杨奂哀求说:“臣等皆太学生,令执炮夫之役,恐非国家百年以来待士之意。”于是金哀宗“免其役”〔109〕。完颜白撒十分恼火,又“分令诸生监送军士饮食, 视医药,书炮夫姓名”。“又夜举灯球为令,使军士自暗门出劫战,令诸生执役,灯灭者死。诸生甚苦之。”〔110〕
虽然金军守城,十分艰难,但蒙古方面也承认,“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111〕,“京城之役,守者屡出接战,我军不能前”〔112〕。速不台不得不在四月上旬罢攻。“城上人望见北兵焚炮车,众皆以相贺。俄闻北兵不退,四面驻兵逻之,由是知祸未艾也。”〔113〕
金蒙虽然暂时和议,但金朝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蒙古军已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分州县,开封处于粮尽援绝的困境。当年夏,开封大疫五十天,大量人口死亡。七月,蒙古使者唐庆一行到开封,说:“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金哀宗只能“托疾,卧御榻上”,唐庆“不为礼”,“仍有不逊言”。“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馆,诏贳其罪,和议遂绝。”八月,武仙与完颜思烈两军奉命增援,却被蒙古军击败。在粮食奇缺的形势下,金哀宗仍两次下令“括粟”,第二次规定“自亲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粮,计口留之,人三斗,余入官,隐匿者处死”。有两个寡妇,“实豆六斗,内有蓬子约三升”,“竟死杖下”。参知政事完颜合周说:“人云花又不损,蜜又得成,予谓花不损,何由成蜜。且京师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结果“所括不能三万斛”,而“死者相枕,贫富束手待毙而已”〔114 〕。
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金哀宗只能于十二月率军逃出开封。天兴二年正月,开封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杀留守开封城的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捏阿不,投降速不台。城南的青城,当年是宋钦宗投降和被俘之地,如今金朝的皇族、后妃等也被押往此地,大多被杀。当时开封城内景况比北宋亡国时更惨,“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开封投降后,市民们“得出近郊采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陈冈上有野麦甚丰, (崔)立请百姓往收之”。但蒙古军入城后,仍然“大掠”〔115〕。速不台提出屠城,被耶律楚材劝阻,最后“速不台下令纵其民北渡以就食”〔116〕。大量开封人口留在城内,已不能生存。 张柔入城后,“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家,卫送北归”〔117〕。
由于最后不战而降,开封城内虽然“触目皆瓦砾废区”,却完整地保存了金宫,而北宋的遗迹主要只剩下了龙德宫的熙春阁。据《使燕日录》载,翌年六月夏季,宋使们“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状”,并亲自“出城迎”。宋使们所见,金宫“殿宇皆群小杂居,粪壤堆积,庭下草深数尺,大内诸殿亦然”。北宋时的“琼林苑、金明池,苑余墙垣,池存废沼”。龙德宫原“有殿二,有馆四,有亭二十有四”,“止存熙春一杰阁,高百余尺,巍然插空,非人间所有”。在丹凤门内外,“此京城阛阓軿阗之最,今荒墟矣”,不免起旧京黍离之叹。元人王恽有诗文咏金朝故宫和熙春阁说:“掖庭依约粉垣丹,行入荒宫重黯然。华表忽惊人世换,昆明重见劫灰寒。”“封丘门外故宫傍,天阁空余内苑荒。瀛海梦空三岛没,帝城烟惨五云苍。”他赞叹熙春阁为“神营鬼构”的建筑。〔118〕此外, 《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也记录了劫后开封所存的雄伟建筑和古迹。
据《元史》卷59《地理志》,在壬子年(公元1252),即开封失陷后的第20年,汴梁路下辖郑、许、陈、钧、睢五州之地,仅有户30,018,人口184,367,户数比宋金时代少得可怜。由此可见, 开封的极盛期是在北宋,而在金元之际,总的说来,是走着下坡路,而非复旧时之盛。
注释:
〔1〕《宋史》卷375,《邓肃传》。
〔2〕《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70。
〔3〕《会编》卷77。
〔4〕《会编》卷113,《历代名臣奏议》卷85。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12, 建炎二年正月壬辰;《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14,《宗忠简公传》。
〔6〕《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甲辰。
〔7〕《要录》卷24,建炎三年六月乙亥;卷25, 建炎三年七月庚子;卷26,建炎三年八月乙丑;卷27, 建炎三年闰八月; 《会编》卷133,卷136,卷137;《宋史》卷475,《刘豫传》。
〔8〕《会编》卷137;《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丁亥。
〔9〕《金史》卷3,《太宗纪》。
〔10〕《会编》卷181;《要录》卷91,绍兴五年七月;卷99, 绍兴六年春。
〔11〕《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己酉朔。
〔12〕《会编》卷194;《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丑,丁巳;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己亥。
〔13〕《会编》卷200;《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丙戌。
〔14〕《鄂国金稡佗编》卷8。
〔15〕《金史》卷77,《宗弼传》。
〔16〕《金史》卷90,《赵元传》;卷105,《任熊祥传》。
〔17〕《金史》卷5,《海陵纪》。
〔18〕《金史》卷5,《海陵纪》。
〔19〕《金史》卷5,《海陵纪》;卷82,《郭安国传》。
〔20〕《会编》卷243, 《炀王江上录》说:“以梁汉臣充修汴京大内正使,孔彦舟为副使。”此当是宋人的口吻,金人应称南京。
〔21〕《金史》卷131,《梁珫传》。
〔22〕《金史》卷79,《孔彦舟传》。
〔23〕《会编》卷242,《正隆事迹记》。
〔24〕《金史》卷82,《郑建充传》。
〔25〕《金史》卷5,《海陵纪》。
〔26〕《会编》卷242,《正隆事迹记》。
〔27〕《宋史》卷85,《地理志》。
〔28〕《铁围山丛谈》卷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睦亲宅》。
〔29〕《梁溪全集》卷83,《奉迎录》。
〔30〕《揽辔录》。
〔31〕《使金录》。
〔32〕《归潜志》卷7。《金史》卷56、卷58,《百官志》载, 设有“同乐园管勾”官。
〔33〕《中州丙集》卷3,《龙德宫》。
〔34〕《中州戊集》卷5,《书龙德宫八景亭》。
〔35〕《元文类》卷27;《说郛》卷68,杨奂《汴故宫记》;《金史》卷25,《地理志》。
〔36〕《湛渊静语》卷2引《使燕日录》作“敕赐卿云万态奇峰”。今据《大金国志校证》卷33,但此书作“独秀太平岩”,又漏落“玉京”两字。据宋《东都事略》卷106 《朱勔传》和《吹剑三录》引祖秀《华阳宫记》,《挥麈录馀话》卷2, 艮岳有三块大石赐名,除玉京独秀太平岩外,另有神运昭功敷庆万寿峰和庆(或作卿)云万态奇峰,其名与正文所引有异。
〔37〕丘刚:《北宋东京内城遗址的勘察》。
〔38〕《北行日录》上。
〔39〕《元文类》卷27;《说郛》卷68,杨奂《汴故宫记》;《金史》卷25,《地理志》。
〔40〕《湛渊静语》卷2引《使燕日录》, 《大金国志校证》卷33。
〔41〕《金史》卷7,《世宗纪》;卷95,《程辉传》。
〔42〕《北行日录》下。
〔43〕《金史》卷35,《礼志》。
〔44〕《金史》卷39,《乐志》。
〔45〕《揽辔录》,《北行日录》上,《北辕录》,《使金录》。
〔46〕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3页,61—63页。
〔47〕以《元文类》卷27、《说郛》卷68杨奂《汴故宫记》参校。
〔48〕《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49〕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47页。
〔50〕《北行日录》上。
〔51〕《揽辔录》;《石湖居士诗集》卷12,《宜春苑》、《相国寺》、《市街》。
〔52〕《北辕录》。
〔53〕《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1,《梁公墓铭》。
〔54〕《金史》卷47,《食货志》。
〔55〕《揽辔录》。关于宋使记录,参见陈学霖《宋史论集》的《范成大〈揽辔录〉传本探索》和《楼钥使金所见之华北城镇》。此段即据陈学霖所引《永乐大典》卷11951补裰。
〔56〕《北行日录》上。
〔57〕《金史》卷90,《高德基传》。
〔58〕《金史》卷25,《地理志》。
〔59〕《金史》卷82,《光英传》。
〔60〕《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
〔61〕《金史》卷12,《章宗纪》;卷93,《仆散揆传》,《宗浩传》。
〔62〕《金史》卷57,《百官志》;卷86,《独吉义传》。
〔63〕《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64〕《金史》卷27,《河渠志》。
〔65〕《金史》卷105,《刘枢传》。
〔66〕《金史》卷97,《张亨传》。
〔67〕《金史》卷92,《卢庸传》。
〔68〕《金史》卷128,《武都传》。
〔69〕《金史》卷110,《雷渊传》。
〔70〕《金史》卷9、卷11、卷12《章宗纪》;卷57, 《百官志》。
〔71〕《金史》卷10,《章宗纪》;卷96,《李愈传》。
〔72〕《金史》卷97,《李完传》;卷103,《纳兰胡鲁刺传》。
〔73〕《金史》卷128,《纥石烈德传》。
〔74〕《揽辔录》。
〔75〕《宋史》卷85,《地理志》;《金史》卷25,《地理志》。
〔76〕《金史》卷99,《徒单镒传》。
〔77〕《金史》卷102,《完颜弼传》。参见卷101,《仆散端传》、《耿端义传》。
〔78〕《金史》卷14,《宣宗纪》。
〔79〕《金史》卷14,《宣宗纪》;卷100,《张炜传》。
〔80〕见《湛渊静语》卷2。《大金国志校证》卷33, 《汴京制度》作邹伸之。
〔81〕见《元文卷》卷27,《说郛》卷68。
〔82〕《金史》卷30,《礼志》;卷39,《乐志》。
〔83〕《汝南遗事》卷4,《元文类》卷27和《说郛》卷68 《汴故宫记》所载相同,而《湛渊静语》卷2《使燕日录》作“圣寿宫”。
〔84〕《归潜志》卷7。
〔85〕《金史》卷115,《崔立传》。
〔86〕《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87〕《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元文类》卷57 《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作“户一百四十七万”,其数字就更加惊人,当有几百万人。
〔88〕《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89〕《金史》卷113,《白撒传》。
〔90〕《金史》卷114,《斜卯爱实传》。
〔91〕《遗山先生文集》卷33,《警巡院廨署记》。
〔92〕《金史》卷23,《五行志》。
〔93〕《金史》卷14,《宣宗纪》;卷106,《术虎高琪传》。
〔94〕《金史》卷113,《完颜赛不传》。
〔95〕行三司掌管经济事务,参见《金史》卷100《李复亨传》。
〔96〕《牧庵集》卷5,《汴梁庙学记》。
〔97〕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第44—53页;丘刚:《北宋东京内城遗址的勘察》。
〔98〕《元史》卷2,《太宗纪》;卷115,《睿宗传》;卷121, 《速不台传》。
〔99〕《金史》卷93,《守纯传》。
〔100〕《金史》卷113,《白撒传》。
〔101〕《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02〕《元史》卷119,《塔察儿传》;卷149,《郭侃传》。
〔103〕《遗山先生文集》卷6《梁园春》五首注:“龙德宫有玉溪馆。”疑是。
〔104〕《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105〕《金史》卷113,《白撒传》、《赤盏合喜传》。
〔106〕《归潜志》卷7。
〔107〕《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08〕《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09〕《金史》卷113,《赤盏合喜传》。
〔110〕《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11〕《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元文类》卷5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112〕《遗山先生文集》卷26,《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113〕《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14〕《金史》卷17、卷18《哀宗纪》;卷114,《斜卯爱实传》、《合周传》;《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
〔115〕《归潜志》卷7、卷11,《录大梁事》。
〔116〕《元史》卷121,《速不台传》;《元史》卷146, 《耶律楚材传》;《元文类》卷5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117〕《元史》卷147,《张柔传》。
〔118〕《秋涧先生大全集》卷14,《登熙春阁》、《哀故宫》; 卷38,《熙春阁遗制记》。
《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第1期,第86~95页
以上转载自网络,侵·联·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