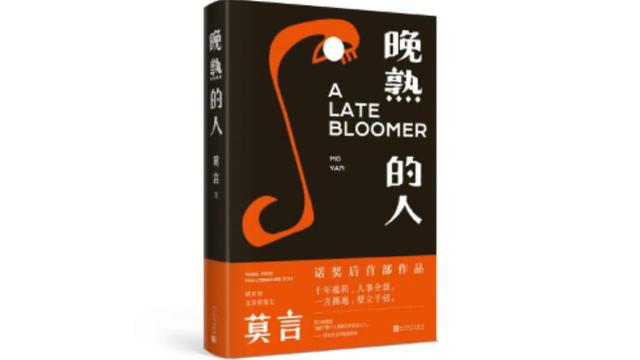我听刘颖老师的作品不是很多,印象最深的就是2010年相声大赛上他和搭档合说的《一对一》。这段作品贴近现实,道出了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因此现场表演气氛热烈,最终夺得一等奖。
电话里约访刘颖老师,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比较严肃,没有客套,不说废话,干脆利落。采访当天在铁路文工团见到刘老师,他先领我们看了看二七剧场,那时候临近春节,剧场内正举行一场对团里老同志们的慰问演出。
进排练场地开始采访之前,刘颖老师专门回了一趟办公室,取出一条红围脖搭在脖子上,人显得更精神了。
采访过程中刘老师提到师父李金斗老师眼睛特别大,其实他的眼睛也不小,尤其当他非常认真地阐发自己对相声的理解的时候。能看出他平时勤于思考,对相声圈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坚持,尤其对于相声规矩,他甚至怀有特别的执念。
由于亲历过曲艺团老先生们的教诲,他对于规矩二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甚至希望讲规矩的相声能像京剧一样成为知音艺术,而对只追求包袱儿不讲规矩的表演不屑一顾。
在刘颖老师之后我还采访过高晓攀。他和刘老师关系非常好,但对于刘老师的执念他还是不太理解,认为刘颖老师坚守的是死板的“学徒相声”。刘老师对晓攀说,没办法,我是大师哥。
说到当年曾合作十年的老搭档于谦,刘颖老师不吝赞赏之词。他认为于老师是他们那一批演员当中天分最好的,他能有后来的成就自己丝毫不奇怪。就在采访刘老师那几天,我还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张八十年代北京市曲艺团几位演员外出旅游的合影,那上面有年轻的刘颖、于谦、李伟建、武斌,李金斗和陈涌泉老师也显得很年轻。

前排左起依次为刘颖、李伟建、武宾,后排左起依次为于谦、李金斗、李建华、陈涌泉、刘洪沂
采访结束与刘颖老师合影,我们身后是一组铁皮柜子,其中一只铭牌上,还贴着刘老师当年的老搭档于谦的名字。在于谦和郭德纲走红之前,当时的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侯耀文,曾把这两位新秀调进团里,力图打造一支国内实力最强的相声队伍。
刘颖访谈录
刘颖:1969年生,北京人。11岁考入北京市曲艺团团带班,同年拜李金斗为师学习相声,在校期间得到王世臣、王长友、高凤山、罗荣寿等人的指导。1985年进入北京市曲艺团任相声演员,与于谦合作演出。1992年赴日本留学,1999年回国。2003年起,参加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2008年加入中国铁路文工团,与张浩楠结为搭档。2010年,两人合说《一对一》获得第五届CCTV相声大赛职业组一等奖。代表作品包括,《一对一》、《教你模仿》、《又来打灯谜》、《出谋划策》、《时尚评书》等。

刘颖接受采访中。杨明拍摄
“曲艺最应该注重两个字,规矩”
问:我看您13岁就拜了李金斗老师?
刘颖:11岁。没关系,这只是个数字问题。
问:那时是把他当做老师来学习,还是真正拜师了?
刘颖:就是拜师。
问:但当时金斗老师还非常年轻啊。
刘颖:缘分,缘分。我拜他的时候他还没说《武松打虎》呢。我做过几年隐蔽的徒弟,因为我师父对我有一个要求。我们考北京曲艺团的时候,对相声不是很了解,就是喜欢文艺,表现欲比较强。考曲艺团一试、二试过了以后集中一个星期培训,每个人都选择老师,那时对相声有了解的人选择的就是有名的老师,让我选的时候正好赶上我师父推着自行车下班,我就问负责人,这个老师是说相声的吗?他说是啊,我说那我就跟他学。现在想起来就是缘分。当时我是觉得我师父长得很突出。那负责人就叫住我师父,师父说我教不了,我还学呢。他推车就要走,我一把就把车后座拉住了,我说老师我必须跟您学,我师父就答应了。他给我培训一个星期,说了一个小段儿,叫《一分为二》,说的是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我也就考进来了。除了我师父,启蒙老师那就太多了。

青年时代的李金斗、王文友表演相声
问:那时候老先生都在。
刘颖:对,王世臣老师、王长友老师、高凤山老师、罗荣寿老师,这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
问:想想有点儿不可思议,拜金斗老师为师,就因为眼缘。
刘颖:我认为相声界的师徒都存在一种缘分,跟名气大小不直接相关。“投明师访高友”,这个“明师”是明白的“明”,不是名气的“名”。跟我师父学的那一个星期,他教会我一些东西,我也愿意跟他学,我认为这是我的运气、我的造化。至于说金斗老师是哪年有的名,这和我跟他学能耐关系不大,很多老前辈、老艺术家们没有《武松打虎》这样的代表作,但他的能力都是很强的,在相声舞台上不能以谁腕儿大、谁名气大论英雄。
问:在你们心目中有和普通观众不一样的衡量标准。
刘颖:对。我是一个专业的相声人员,所谓专业并不是说我在一个专业的文艺院团,专业是你拿它当职业,还有一种说法是专业就必须有责任感,相声对于我来说是伟大的。相声这种语言艺术,它具有的能量,我从中汲取能量,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支撑。
问:你们当时考的这个班正式名字叫……
刘颖:北京曲艺团团带班,我们挂靠在北京戏曲学校,我们学文化课和形体课是戏校的老师教,学相声、曲艺概论,学台词和声乐是北京曲艺团的老师教。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再后面就没有了。
问:这跟谦祥老师、增瑞老师他们那会儿的曲艺班一样吗?
刘颖:一样,谦祥叔和增瑞叔他们长我们两代。北京市曲艺团团带班严格来说应该是五代,不严格说是三代。第一代的演员有莫岐老师、马歧老师,第二代就是我师父和谦祥老师他们这一代,第三代人有张志强老师、种玉杰老师,第四代有刘廷凯、崔伟丽、李红军,我们就是第五代。我们第五代演员也有淘汰和补充,先来的有我、于谦、李伟建,后来补充进来还有武斌等演员。

1960年北京曲艺团学员班合影。前排为王长友、谭伯儒,后排左起依次为李金斗、李增瑞、王文友、王谦祥
问:后来就没有第六代了。
刘颖:没有了。我认为曲艺人才培养有这种团带班是最好的,师资力量强。我老跟别人说,我们是21个老前辈给打大的。
问:到你们那会儿还打吗?
刘颖:打、打、打。相声教育比较严苛,比如我师父教我就非常苛刻,我小时候有没有心里不舒服?有。但现在我理解,这种教育方式是科学的。一说“打”字,你的脑子里立马出现非常恶劣的那种画面,那就不对了,老先生的打是点到为止,有点儿像佛教里说的棒喝,在哪个节骨眼儿打你一下,叫你在这里集中精神,你就记住了。这东西带给你一生,我们叫做瓷实。
问:起码对于学习相声来说是好的。
刘颖:我学习《黄鹤楼》的时候,罗荣寿老师拿烟袋锅子打我脑袋上好几个包,那时我觉得招老师生气是很大的耻辱。罗老师拿着烟袋锅子手直哆嗦,现在想想,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论辈分他也长我那么多代,他凭什么哆嗦?我有什么行为把他气成那样?说明什么,他太爱相声了,他希望我们能成为相声的接班人。我现在快到他们那个年龄了,我只有感恩,感念他们这些老先生。

相声名家罗荣寿
问:您刚才说打你们的都是老先生,金斗老师不敢打你们是吗?
刘颖:我师父还用打吗,他那大眼珠子一瞪,还用打吗?
问:当时被打这些事儿,跟家里说吗?
刘颖:不跟家里说。我认为那就是我的错,我能把我的错误满处去说吗?
问:8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注重所谓文凭教育了,当时你们想报考学相声,家里理解吗?
刘颖:理解呀。
问:就是喜欢。
刘颖:不是,困难呀。实话实说,我母亲身体不好,30岁就卧病在床,家里就靠着我父亲,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就想给家里省省心、省省力,自己走出去。
问:从那些老先生身上,能看到什么?比如注重基本功?注重规矩?
刘颖:我认为注重的就是两个字,规矩。现在说规矩都说到了道德层面,我认为这都不足以说得丰满。学艺有学艺的规矩,表现有表现的规矩,做人有做人的规矩,传承有传承的规矩。曲艺界最应该注重的两个字就是规矩。我师父告诉我,侯先生给我们京派相声设定了八个字,清雅、规矩、细腻、流畅。一个相声演员的规矩,从你开始要创作哪段相声,说哪段相声,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表现什么,这里就有规矩。不是我想怎么说怎么说,不是哪个包袱儿好我就要搁进去。选择什么服装,服装熨烫得很标准,这是一种规矩。走上舞台,你的节奏、你的频率是一种规矩,如何从垫话儿、瓢把儿到正活到底,这是一种规矩,如何与观众交流、与捧哏交流,这也是一种规矩,下来之后如何一遍拆洗一遍新,也是规矩。每个细节都有规矩,这就能区分出专业的和业余的。规矩就要讲究不要将就。老师要求我们更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有规矩。台上那十几分钟不是玩儿,需要跟运动员一样紧张起来。很多相声表演看似轻松随意,从一开始我们叫爬坡儿,老先生说我们得跟台风潇洒的京剧艺术家学习。比如马连良先生,看着轻松随意,其实拿鞋已经把舞台踩出坑,内劲很大。如果相声就信马由缰地说,我们就不叫艺术,就叫祸从口出了,你有多大的文化支撑和基本功支撑?你看马三立先生站台上看着那么絮叨,其实不是,我听我老祖王长友先生讲过,他和马三立先生是莫逆之交,他和刘奎珍先生两个人上家里给马三立先生念活,所谓念活就是说,这个段子是我们创作的,但我们俩说不精彩,我们把这个节目给你。然后马先生还会在他们面前表演这段儿,有时候你看着马先生说一句台词好像想不起来下句了,其实那是他的表演风格。很多人现在想模仿这个,你像吗?我的相声追求就是四个字,舌治心耕。这是相声的祖师爷朱绍文先生留下来的。您了解相声很多,朱绍文的艺名是什么?
问:穷不怕嘛。
刘颖:您说的这三个字是对的,但是又说错了,说出来穷后面应该有个停顿,然后才是不怕。我认为说相声的应该有一颗不怕穷的心,这才能把相声说好。我师父经常跟我说,买一尺,露八分。老先生也跟我们说过,好相声是什么样的,让你听完之后,一无所获,满载而归。相声是有哲学意味的。
问:老先生们传下来的这些,您平时思考的这些,跟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能理解吗?
刘颖:相声是散发个人魅力的艺术,但也不能说谁说的就完全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师胜杰先生告诉我说,不能做“三一”的相声演员,一张脸,台上台下都是那个模样;一字调,说话没有音调变化;一道汤,表演什么节目都一个滋味。
“论天分,于谦在我们这批演员中排第一”
问:咱们再往回倒一点儿,你们在学员班学了几年?
刘颖:最开始说是三年,后来追加了两年,一共五年。
问:在学习的时候,就算曲艺团的人吗?
刘颖:算曲艺团的学员。每年考试两次,还要进行淘汰,有业务分数不高的,有生活行为不符的,还有找到另外机会另谋高就的,各种情况都有。
问:当时您有稳定搭档吗?
刘颖:于谦。我和于谦搭档了十年,从1982年到1992年。我们俩是进学员班考试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一直是搭档。

青年于谦
问:一直是您逗哏他捧哏吗?
刘颖:对。
问:你们合作十多年,互相有个评价吗?
刘颖:我对于谦的评价啊,于谦能有今天的成就,根本就不奇怪,他从小就很优秀,老先生们和同学们都能看出来,于谦的捧哏很像赵世忠先生。
问:赵先生是捧哏大家。
刘颖:而且于谦的艺术素养也是受到家庭影响。
问: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吧?
刘颖:知识分子。于谦从小受教育,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小时候他写字最好。你们现在听于谦唱歌、唱京剧、唱曲艺,从小在我们那一批孩子中,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特别好学,学得也快,而且有天分,学完之后到他身上还就特瓷实,但我们就得不停地练,不练的话就忘了。天分方面,他在我们这一批演员中应该排第一。
问:你们还是有缘分,中间分开那么多年,到后来他的关系又到了您所在的铁路文工团。
刘颖:对对对。但他是先进来的,我后进来。
问:1992年您去日本学习管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相声不景气吗?
刘颖:有,有。
问:当时的相声不景气到什么程度?
刘颖:我们很多同学都去报考电影学院表演系、导演系,都去学副科,既然大家都有其他追求,我就彻底别干了。
问:我听说是当时曲艺团给的工资很低,而且演出方面……
刘颖:关键是演出机会很少。
问:演出市场还没有兴盛,电视晚会又轮不到你们这些小字辈,是吗?
刘颖:对。那时候我不是跟于谦一起拍《编辑部的故事》吗?电视剧风潮刚刚要来,拍完《编辑部的故事》我就走了,我那会儿哪儿懂判断未来呀。而且那个年龄段正是我们情窦初开的时候,知识文化欠缺,很难准确判断未来。如果在学员班的时候多看看书,多听老先生话,多学一些哪怕我们不演的节目,独立判断的能力都会增强。说一句笑话,就是后悔,只能让今后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儿,明白一点儿。

刘颖、于谦参演《编辑部的故事》
问:其实可以理解,你们走上社会早,到九十年代初你们其实也才20几岁。
刘颖:22岁。
问:当时金斗老师什么态度?
刘颖:不让走。就因为师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扛了七年,要不半年我就跑回来了。师父跟我说,爷们儿,咱们干这个的,有句老话叫做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你说是出去上学去,谁养你啊?你不得自己养自己勤工俭学吗?你受得了吗?听我的,别去。但那时候自己年轻,没听师父的话。
问:但您当时看不清在国内那种状态的未来。
刘颖:对,就是实践机会太少了,一年都演不了几场。那时是北京曲艺团力量最雄厚的时候,轮不上我们登台。我们进曲艺团的时候,每到演出我师父和谦祥叔他们这两对儿轮换着开场,等我们毕业的时候我师父就已经奔“底”去了。我跟你说说那时候我们一台晚会的阵容。梁厚民老师开场你信吗?二场,殷培田、刘晨老师的《老年人》,三场谦祥叔,四场我师父和陈涌泉老先生,五场史文惠、李世明,六场刘司昌老先生,七场我师爷赵先生他们,底是笑林。旁边还有很多人在排着上不了场,像王文友、陈志峰、李红军。
问:所以你们就看不到希望。
刘颖:对,演出机会太少了。
问:金斗老师只能提醒您到日本会有多难,但当时你们那种状态的出路,他也说不好。
刘颖:说不好。
“我给你恢复,你就行”
问:到日本后有个细节,洗盘子的时候……
刘颖:对,真背《菜单子》。我英语一窍不通,但日语没有问题。学过相声再学外语其实很难,日本人总说我说的日语很奇怪,但是都能听懂。刷碗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个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同时弯下腰去刷,人家能两三个小时不直腰,但我老得直腰,我就老被店长说。我学艺出身有尊严,我就得扛着,那得分散注意力,我就开始背《菜单子》,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日本人老问,你念叨什么呢?我说我背五十音图呢。
问:五十音图是什么?
刘颖:就是日本的音标。
问:您是1992年去日本,1999年回来的。怎么想到回来的?
刘颖:我是被母亲骗回来的。她觉得我老这样下去不行,就骗我说她生病了,让我回来看看她,我回来以后她就把护照扣住了。
问:您当时30岁。
刘颖:对。我首先知道自己当时说不了相声了,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一周不练同行知道,一个月不练大家就知道了,我将近十年没有上过舞台。那时候到哪儿都不敢承认自己是相声演员。
问:回来见金斗老师了吗?
刘颖:见啦,他给我轰出来了。我刚回来头发是灰的,还打着耳环,我提前打过电话他知道是我,一开门我师父还是来了一句,您是?我说师父是我,他说出去,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都归置好了才能进来。第二天赶紧理发,把零碎儿都摘了才进师父家门。师父说,这就对了,咱是中国人。他让我先歇歇,接下来再看干什么。
问:他也并不是说干相声这行儿。
刘颖:他在观察,他也看我丢没丢基本功,虽然我们都带着童子功,但他怕我丢了。我又没跟他说我每天都在练《菜单子》。
问:侯先生十年文革没登过台,他再上台都有点儿含糊。大师都如此。
刘颖:我们叫“顶”。
问:那您先做了几年其他行业的工作,顺利吗?
刘颖:很顺利,毕竟我学了管理,另外我有一个强大的武器。
问:能说。
刘颖:语言。不叫能说,语言。我有个极端的话,语言是第一生产力。
问:需要几句话把事儿说明白,让人明白你的意图。
刘颖:对。我们从小学过语言艺术,与人交流的时候我能发挥出来,比如偷换概念、找谐音,最终的目的是底。比如做营销,与人沟通直接到哽嗓咽喉。所以我当时发展得还是如鱼得水。
问:直到2003年,金斗老师他们组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刘颖:对,我师父和宋德全老师筹建俱乐部,我那时候老跟他们见面。我师父说,俱乐部要平稳健康发展,需要老中青三代演员,他说他当时就算老了,年轻人也有,中年力量不足。他就跟我说,你跟了我那么长时间,启蒙老师教了你那么多,你要是不表现就有点儿可惜了。我当时说,杨少华老先生说过一句话,凡是学过相声的人,血液里就有一种菌,叫笑菌,今生磨灭不了。我说我真心体会到这句话,相声是一座高山,我已经到了山脚下,现在只能仰慕它。我师父说,我要给你恢复,就行。他说如果他不行,还有另一个人行,谁?你的另一个启蒙老师,陈涌泉老先生。我说师父,容我考虑三天,然后我真的在家斗争了三天。

李金斗、陈涌泉表演相声
问:那说明一方面您对于相声之路不太确定,另一方面也说明您自己当时的事业发展还可以。
刘颖:对。到最后还是造化,也就是缘分。但我相声恢复得还是很痛苦,又回到学徒的阶段,挨骂,斥责,那时候我都30多了。第一次跟我师父恢复上台,我大量出汗,下来都湿透了。后来在我师父和陈涌泉老先生的帮助下,我恢复了两年。

刘颖和李金斗等人合影
问:那两年就是金斗老师捧哏,他给托着?
刘颖:对,恢复之后我为什么要找新搭档呢?因为我觉得我师父不容易,他是一家之主,业务如日中天,他也有很多事务要忙,抽空给我排练,我于心不忍。后来我还跟陈涌泉老师对活,但老先生毕竟年岁大了,有时候出去演出,带着陈老师出门我对人家陈家是一个责任。恢复之后我就需要速度了,在后台很多小孩儿当中我就发现了浩楠。
“创作一段上乘的相声,需要前辈帮你考量”
问:您和浩楠老师是2005年开始搭档的。
刘颖:2004年我先找的康珣,找张浩楠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走创作路线。
问:能介绍一下康珣老师的情况吗?
刘颖:康珣老师的父亲叫康松广。

康松广、靳佩良表演相声
问:康老师我们前两天刚聊过。
刘颖:康松广老师是我们老祖(王长友)最小的徒弟,而康珣老师多年来在中央电视台做专业撰稿,小品、相声都写过。比如李伟建表演的《咨询热线》,我说的《一对一》,还有春晚上的一些小品,他都参与过。他也是我们团的。我跟康珣老师说,我有很多想法,毕竟我出去过,经历过很多,对很多传统相声有自己的理解,后来我们俩合作写过《教你模仿》、改编《打灯谜》叫《又来打灯谜》,还有《出谋划策》、《时尚评书》、《说唱双截棍》、《减肥一家人》,还改编过《夸住宅》叫《安家置业》,最后那段的说各种钟表的贯口,里面很多品牌现在观众不知道,我就把它改成现在的国际品牌,一口气说下来。

相声编剧康珣
问:那在表演方面搭档就是浩楠老师,他是建华老师徒弟对吧?
刘颖:对。
问:当时金斗老师和建华老师开始合作了吗?
刘颖:早就合作了,俱乐部之前就开始合作。
问:您2008年进入铁路文工团,大部分观众认识你们俩,是通过2010年的第五届相声大赛,你们就合说了那段《一对一》。现场的效果非常好,你们后来又在2011年的央视元宵晚会上说过。这个段子应该下了很大功夫,题材上也贴近很多家庭的实际,这个点子最早怎么出来的?
刘颖:我找康珣去谈创作,进他们家小区,见小区里到处都是家教小广告,我跟他说,这广告给你们小区都快贴花了,这个咱们是不是值得说说?他说我这两天正在琢磨这个,所以我们俩是一拍即合。原来我们这个活就叫《我要当家教》,谁给我们改成《一对一》的呢?康松广老先生。
问:他也特别擅长创作。
刘颖:那时候有个品牌专门就做一对一培训,这样最挣钱。这个节目也是一遍拆洗一遍新,从《我要当家教》,到《我是黑家教》,再到《一对一》,主题从讽刺家教到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错误的,后面这个主题这是我们总团团长刘志江提醒我的,这仅仅是一句广告词,不是人生哲理。后来姜昆先生、师胜杰先生,我师父就更不用说了,石富宽先生、赵炎先生、袁德旺先生……
问:央视的导演。
刘颖:对,诸多大家,还有李增瑞先生、常贵田先生,都给我排练过这个作品。我的体会是,真要创作出一段上乘的相声,就要找前辈大家们帮你考量,光靠我们几个没有办法把节目打造成最后这样。
问:如果他们的意见相左,怎么办?
刘颖:这种情况太多了,那我就来说服,比如我说,这样一改您的风格能表现出来,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东西还要表现,那就是浪费时间。
问:既要博采众长,也要有自己的判断。
刘颖:比如我师父跟我说要做到几个地方,我跟我师父说我做不到以他的风格,以名人的状态可以那样表演。就说里面的垫话儿,我的垫话儿比较长,他认为可以去掉,我说我跟您不一样,您一上去大家就愿意听您说话,我上去就先要吸引眼球,哪怕有着表演时长的要求。

2019年,刘颖、浩楠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参加这种大赛,作品是有时间要求的是吧?
刘颖:有啊,13分钟啊,我已经超了,超了4分钟。相声需要语言的叠加和组织罗列,才能形成最后的结局,一句话让你乐那是笑话那不是相声。
问:像苏文茂先生的《扔靴子》,如果没有前面两番儿,只说最后一番儿那观众乐不出来。
刘颖:我接受的教育是,老先生说如果给你的全是包袱儿,你以后就不会说相声了,当你遇到没有包袱儿的相声,肯定就不行了。再一个,你怎么知道没有包袱儿的语言就真的没有包袱儿呢?
问:起码它有吸引力。
刘颖:我们听刘宝瑞先生很多作品,没有那么多包袱儿,但他留下很多惊世之作。相声演员应该把握铺包袱儿、翻包袱儿、抖包袱儿的技巧和功能,另外没有包袱儿的语言也要说得非常有味道。
问:说到《一对一》,它的内容与当时的现实非常贴近,如何看待相声作品和现实的距离问题?现在有些作品不关心现实。
刘颖:《一对一》就是一个时效性节目,它能不能留得更久一点,可以,但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它是为大赛量身定做,这一点不能回避。小园子有小园子的相声,大剧场有大剧场的相声,分得很细,比赛节目讲究技巧性,说学逗唱都体现出来,《一对一》这些都有,唯独没有倒口。
“我要坚守我心中的相声,哪怕只剩我一个人”
问:在相声创作方面,您提出过相声产业化这样的话,认为演员收入和创作者收入不匹配,这个问题现在有解了吗?是不是现在相声演员本身的创作能力提高了?
刘颖:我不管它解不解,我自己先要解。相声走到今天,外行人都说相声有低谷,谁的问题?相声人自己的问题。一个相声演员想再演好小品,演好电影,把这些都做好,不太可能,能把相声本身做好就谈何容易?相声文本创作是文学创作中最难的,这也不是刘颖说的,这是老舍说的。相声还要依靠专业创作队伍,相声演员与他们碰撞出火花,我们演员对文字的感知还比较差,更缺乏理论基础。就像侯宝林先生旁边有个王决老,侯先生说过很多话,“捧得严,兜得紧,铺得稳,抖得准”,还有“宁不够,莫过头,恰到好,余地留”,如果王决老不给他总结呢?
问:高度和深度就不够了。
刘颖:当然。人家专业搞曲艺戏剧研究,我们相声队伍需要这样的人。
问:侯先生是表演大师和相声大师,但从理论上……
刘颖:作为艺人你站在台上可以立碑,树碑可以,立传不行,必须两拨儿人一起打磨。这么多年相声创作人员流失了多少?我没有那么大野心拯救这个现状,但凡是跟我合作的人,就跟康珣一样,我给你创作费,我以后演你的节目,无论到哪儿,我一定给你酬劳的10%。这样作者会很用心给你写,他会认为写完之后我跟你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写完就再也跟我没关系了。老先生们说,我有一口肉吃,他就必须有一口肉吃,我有一口汤喝,他就必须有一口汤喝。

2019年,刘颖、浩楠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在您目力范围内,像您和康珣老师这样做的人多不多?
刘颖:我没这么呼吁过,另外我这么做已经招致很多人的反感。
问:为什么?
刘颖:我不知道,大家价值观不一样吧。理解我,不理解我,甚至讨厌我,这都允许,当然我也允许很多人喜欢我。
问:不过也有人说,现在的相声演员需要具备创作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自己写,还有找专业合作者写,这怎么把握?
刘颖:演员自己写,这可以,但我主张从专业创作人员那里借鉴,一个专业演员创作能力再强,迟早也会陷入黔驴技穷的境地。
问:掏空了。
刘颖:当然啊,演员应该是富有表现力的,如果没有人帮你盯着,很有可能走入唯我独尊的死角,对于你自己可能没事儿,该挣钱挣钱,但对艺术没有帮助。

刘颖、李金斗表演相声
问:如今相声的娱乐化越来越强,尤其民营小剧场更迎合了年轻观众的娱乐需求和口味,怎么看这种变化?
刘颖:相声是有功能的,有教育功能,有娱乐功能,娱乐功能只是其中一部分,你无限地发展这一部分没有错,你在这个技巧上很娴熟,但是相声组成的其他技巧,你并不娴熟。这就回到师胜杰先生说的那个,你就是“三一”的相声演员,相声应该一人千面,而不能千人一面,一旦你只说这种包袱儿密集的娱乐相声,你就不能说大相声,带有人物的,带有场景的,带有故事叙述的,你就表现不了了,只能小段儿去凑。我现在看到我的长辈有的也在舞台上这样表演,我很痛心。这是别人的错误吗?不是。相声界相互看待一定要包容,不能说我存在就是对的,别人存在就是不对,年轻人这样说就是不对,你呼吁他能改吗?谁的问题,他老师的问题。什么叫师徒关系?学生有问题一定是老师的罪过。我认可我师父教给我方法,我就要一直走下去,我也饿,我也让家里生活水平提高,但人得讲几个东西,第一是造化,我可以有能耐,但我没有造化怎么办?那我就得面对现实,找准自己的定位。还有人有造化没能耐……
问:他就火了。
刘颖:火,和能不能理解相声,能不能传承好相声,无关。观众喜欢你,那是事实,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你这种表演方式,老先生说,给他三年,他能扛下来吗?相声基本功如果不打下的话,到37岁到45岁你还能站在台上说相声吗?要么你改主持,要么你就改别的了,侯大师上台都慌,他是泰斗啊。苏文茂先生跟我说过,相声是花朵,相声演员是蜜蜂,采蜜不伤花。现在的人已经都不是蜜蜂都是马蜂了,把花全给扒拉碎了。我可以奉献我的生命,我不可以奉献相声的生命,老先生曾经说过,当你每天到家看到全家老小吃得很好,当你穿得很体面受人尊敬的时候,你应该仰望天空说一句话,感谢祖师爷赏饭。坚守自己的选择,舌治心耕。
问:您对相声的未来乐观还是悲观?相声的形式会不会有变化?
刘颖: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也是乐观的。我认为相声未来会出现两个队伍,一个队伍就是我这样的。
问:坚守的。
刘颖:冠冕堂皇地说叫坚守,有人认为我们就是顽固不化。
问:就是比较老派的。
刘颖:对,就是传统,我很传统,我必须像京剧人坚守京剧一样坚守相声。另一个相声队伍已经把相声更改了,比如变成类似脱口秀的形式,更为放松的一种形式。人家没有错,因为他们没有经受过我经历过的严格教育和培训,我就是要坚守我心里的相声,哪怕只剩我一个人坚守我也快乐。一定要分清楚相声是相声,包袱儿是包袱儿,包袱儿在相声里面,相声不能在包袱儿里面,现在大家拿包袱儿太当生命了,这不行。

2019年,刘颖、浩楠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但有些观众现在就认这个,你们让我乐就行,我不管你们相声程式化的传统是什么样儿。
刘颖:对,观众没有错,有些观众需要减压,但是他们也需要经过一个阶段,当你年龄到了有些东西你就笑不出来,你势必要听一些厚重的东西。你让我这岁数的到台上说各种时尚包袱儿,台下年轻观众不都觉得奇怪吗?一个相声演员想让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都喜欢,不可能,但老先生穿上大褂站到台上只要台风端正,就受人尊重,这就是相声的魅力。那些年轻人如果将来想触碰我们这边的领域,他也走不进来,因为他没有基础,我也不抨击他们,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组成了相声。
问:您觉得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不会成长?
刘颖:今天几号?咱们俩打一个赌,十年以后你去采访他们,他们就会被另一批比他年轻的一代或者两代人干掉了。我研究的是相声的厚度,我承载着相声另一个功能——传承,他们使用的是相声的进攻。
问:有一种说法,京剧和相声不同在于哪里,京剧越来越成为一种知音艺术,是年岁稍长的人才会喜欢,它更讲规矩。您坚守的这一支队伍的相声,将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京剧这种少数人的知音艺术?
刘颖:还真别大言不惭,相声成不了京剧,很多从业者对相声没有京剧人对京剧那么爱,当然我很希望相声成为京剧,如果成为不了,我们这个队伍将来被时代淘汰。人家那拨儿人上来把相声更改了,把这两个字改成别的字,那我也只能面对,我愿意抱着这四大本儿,哪怕就像程疯子一样我疯掉了,我也很美。因为我此生追求过,我自认为我追求得没错,相声的规矩两个字对我一生是莫大的支撑,我是很幸福的,我活在我的相声里边,我不会活在别人评价我的相声里面。
问:但这种固守传统当中并不拒绝创新对吗?
刘颖:不拒绝啊,比如我把《打灯谜》改掉,增加一个逻辑,但不破坏它的节奏和技巧,还得是三翻四抖,还得是“吃了吐”,它还得是相声。

刘颖接受采访中。杨明拍摄
注:除特别标注外,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