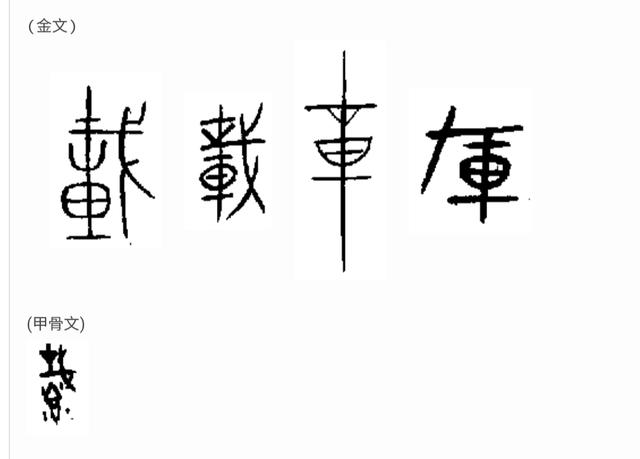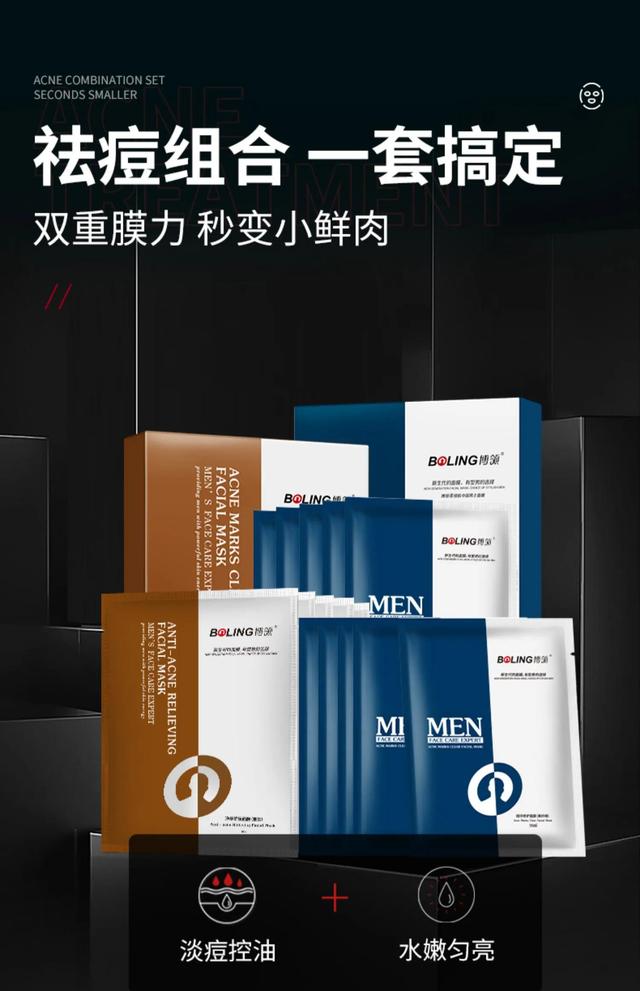提到秋声,总会不由地让人想起欧阳修的《秋声赋》。老先生笔下的秋声,是肃杀、低沉和悲凉的。而我青年时代,在农村所听到的秋声,却是丰富、热烈、高昂而又温暖的,至今难以忘情。
秋的声音,是一首动听的交响乐。你听,那呼呼的风声,就是这交响乐里不可或缺的一组音符。从七月到八月,爽风变凉风,虽然都是呼呼响,但是很象汉语拼音的声调一样,是“阴平”变成“阳平”。慢慢地,它吹红了高粱,山坡上,路两边,便多了一队队、一群群的“醉汉”;吹红了大枣、酸枣,一树树的红玛瑙映照着碧空;吹红了柿子,漫山遍野的柿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它吹黄了谷子,一块块地里头竖满了沉甸甸的金钩;吹黄了玉米杆,每个杆上都站着一个或两个粗壮的穿白衣服的“哨兵”。它吹落了豆叶,豆枝上挂满了褐色的鞭炮;它吹绿了菜地,各样蔬菜长势喜人;它吹白了棉田,大块大块的田地,成了一片银海雪原。
你听,秋虫已经登场。蝉儿们不再喊“热啊”、“热啊”,腔调变成了“知了”、“知了”,它说秋天已然来临。最不知疲倦的是蟋蟀和蝼蛄们。蟋蟀极像现在走穴的歌唱家,一会儿在草丛里,一会儿在窗户外,一会儿“出我床下”,“唧唧”有声。蝼蛄倒像是现在守穴的歌唱家,呆在一个地方扯着嗓子唱着一个音。特别是月明之夜,它叫得更欢。你从它的穴边走过,它会警觉地噤声,待你走远了,它仍旧老调重鸣。有一种叫油蛉的,它的叫声和名字一样好听。你好奇地循声而去,有幸看到它的两个翅膀在不停地振动,发出银铃一样的声音。还有好多人家去大众煤矿推煤,回来路过城郊的柳树行村南,从庄稼地里逮上一只正在吱吱叫的蝈蝈,回家立马用高粱箭扎个笼子,挂在院中搭衣裳的铁丝绳上。它喜欢吃南瓜片,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不知疲倦地“吱”、“吱”、“吱”叫,东家叫,西家应,增添了秋天里的红火气氛。

黄鹂、布谷、麻乍乍、迟笨儿,这些歌唱家都不知道去哪里唱了,当主角的成了啄木鸟。它不辞辛苦,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上,不断传来“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有时还会一连大叫三声。乡亲们说:“啄木鸟,叫三声,不是下雨就刮风”,原来“树医生”对天气还很精通。最吸引人的是大雁,霜降以前,它们成群结队,向南迁徙。蓝天白云,衬托着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叫声渐远,雁阵幻化成美好的画意诗情。每当听到“咹”、“咹”、“咹”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乡亲们就会说“雁过带霜。”三个生产队会不约而同地给社员们放工,催促大家赶快去捊红薯叶,那可是遭饥荒后的半年粮啊!不然寒风一刮,一夜之间,红薯叶会变成一片黑色,很难再被食用。
然而,秋声中的主调还是劳动中发出的声音。
到收庄稼时,我们这半山区,许多地都是在高处的沟里,庄稼得用小车往场里推。一个小队,一出就是十几辆小胶车。推车的都是青壮年,爱热闹,他们都喜欢用柳木做成裹脚(车闸),既耐磨又响声大。开始下坡,身子往后一趔,“吱吱哇哇”一片响声,再配上几句梆子腔,跑几回都不累人。有的地进不去车,青壮年妇女们就用扁担挑,担子担。女人们总是乐观的,担子压在肩上,不耽误说笑,银铃一般的笑声,会传得满沟满岭。
你看,那边来了一队小学生,像蜂出巢,鸟出笼,活蹦乱跳,叽叽喳喳,一会儿又是一阵嘹亮的歌声,他们在本队民办老师的带领下,来拾地上丢落的庄稼和帮忙腾玉米地,别看他们稚气未脱,干起活来,个个都象小大人。
每到凌晨,你会被犁地的各种响声惊醒。“东方红”拖拉机嗓门大,“轰隆隆”响个不停,手扶拖拉机嗓门小,“突突突”地不住声。套牛犁的扶犁手多是少壮派,他们最得意的是甩鞭子,谁也不甘落后。队与队之间,犁手与犁手之间,争着比谁甩得响。为了争响,听说有的用家中最好的麻搓成鞭花,犁半天地,能甩完一条鞭花。坡高沟深,响声此起彼伏,山鸣谷应,比过年放的大雷炮还动听。除了争个响,还有个作用是鞭策鞭策偷懒的牛,催它们快些走,把地犁到犁深。
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各家送饭的会相约来到地头,双手拢成喇叭状,“开饭啦!”“开饭啦!”,喊声此起彼停,唤醒那些忘我耕耘的人们。
上午十一点来钟,卸了套,牛铃声“叮当”、“叮当”响成一团。小牛犊都戴着小铃子,它们无拘无束,随意撒欢,一会跑到前头,母牛一叫,又赶快跑回后头,吃几口奶,“叮叮当当”的铃声,仿佛顽皮孩子的笑声。
到了晚上,要加班,不是撕玉米,就是錘玉米。“千支亮”一点,场上一片光明,男女老少齐上阵。撕玉米活儿轻,人们话匣子自然打开,一边干活,一边家长里短地说一阵,天南地北地侃一通,忘记了白天的劳累。乱一阵,笑一阵,一会儿就撕一大堆。錘玉米时,“扑通扑通”的声音大,也出力,说话声就少了。到了錘成“半片子”,需要清清籽,翻一翻时,话又回到了人们的嘴上。一片人能成一台戏,好象谁也怕把谁当哑巴卖了。有了打玉米机以后,“哗哗哗”的响声,代替了繁重的劳动,机器转一小时,能顶百把人干两个晚上。不知谁念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立即引起人们热烈地共鸣。
我们村子在低处,为了好借风力,三个队的场都在高处。每个场大小不一,最小的有半亩大,一个小队就有十几个场。打场时,石磙“吱吱扭扭”的叫声,配上吆喝牲口的声音,飘荡在山村的上空。扬场的时候,金黄的籽粒“沙沙沙”地落在裹着头巾、披着布单的扫场人的头上、身上,一会籽粒就扫成了小山丘。有经验的扬场手会从木锨的承重上,落籽的声音里,估算出当年某种粮食的“千粒重”来。有了扬场机后,“哗哗哗”的籽粒落成一条黄色的瀑布,获得解放的场上工作人员,会发出惊叹的笑声。
秋天里,晚上要有人站岗,在场房里,草庵中,站岗人会谈论今年的年景,有点文化的人会仿古论今。夜里起来巡查几次之后,遇到那天淅淅沥历地下起秋雨,站岗的人都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一来,连日的劳累终于有了歇息的机会,二来,下了雨,地里有了墒,“麦收八、十、三场雨”(麦子要丰收必须在八月、十月、来年的三月下三场透雨),现在第一场雨要下透了,明年小麦丰收就有了三成保证,咋能不让人高兴?
地犁好了,耙平了,畦搭整齐了,就该播种了。交响乐到了高潮。那几天,除了牲口拉,所有的播种耧都要用上。 耩地,拉耧都是出力活,那几天中午家家不是吃饼就是捞面,乡亲们叫它“盖耧饼”、“扯耧面”。田野里,“推推”、“逮逮”,这是扶耧手对用牲口拉耧的帮耧手的指令;“夹紧胳膊”、“眼观六路”,这是老扶耧手对新扶耧手的教导声;最热闹的是人工拉耧,耩地的那几组,尽管个个满头大汗,还是笑声不断。真是人欢马叫,大家都在为播种希望费心。不过两天,那些作徒弟的新耧手会悄悄地抽空到自己播种过的麦田里,小心翼翼地刨刨,瞧瞧播得匀不匀,断陇不断陇。尽管都符合要求,还是忧心忡忡。熬到七天头上,看到成陇成行的麦苗齐刷刷地出来。“我会了!”“我会了!”就好像范进中了举一样,走到那喊到那,家里人也感到喜得不行。
轮到刨红薯,摘柿子,同样是闹哄哄的,尽管忙,但是热闹,因为这是收获的时辰。
秋收、秋耕、秋种这三部大曲演奏完了,到了九月,呼呼的风声变成了“上声”和“去声”,它吹得麦田碧绿接远陌,吹得霜叶比二月花还红。吹得菜地变了样,萝卜露出胖胖的身体,白菜穿上了新衣十几层……
离开农村,脱离农村劳动,已经三十多年,但是那时节美好动人的秋声,至今还经常回响在我的耳际,出现在我的睡梦中。我要把我的“秋声赋”献给那个火红的年代,献给那个时代忘我劳动的人们。
2019年9月16日

【作者简介】:王来宝,祖籍桂林镇,大专文化,从小喜爱文学,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退休后开始写作,处女作《又到六月六》在红旗渠报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