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的“发明之学”与傅斯年的“发现之法”
文 | 冯胜利
“
本文原载于《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2辑,正文之前有该刊编者按语如下:
此文以黄侃与傅斯年间两种代表性的学术理念为楔点,提出一个世纪来学术范式的转型并反思其对学术研究的根本性影响,其意不止于黄、傅二家的不同,亦不止于东西方学术于方法、理念上的差异,而在对整个学术理念、范式和标准的根源上的反省。发之深,明之广,直溯钱学森的“世纪之问”。
当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所剩几何?学术的最高追求当是什么?中国传统学术的精华有哪些?目前学术风气若有弊病其根何在?孰为学生素质培养之最要紧因素?……凡于此有所思考而有志变革者,读此篇,当有启发。故特予推荐,以期引起广泛注意。
”
提要:本文首先介绍黄季刚先生的发明之学,提出:发明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在乾嘉时代的理必原理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华学术之精华;而发现之学则是在西学东渐中,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用来取代传统旧学(包括发明之学)的现代学术的新方法。文章进而指出:发明之学的理论背景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乾嘉理必),发现之学的学理背景是实验主义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胡适和傅斯年在发现之学的学术风尚和路线上,有着开时代的推创之功;而与此同时(或稍前及后继)的章黄之学,则对乾嘉理必的继承与发展有着自觉的、跨时代的科学贡献。文章在重温“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的同时,提出“中国学术回归理性”的主张与呼唤!
关键词:乾嘉理必;材料主义;理性主义;发明之学;发现之法;学术范式
一、乾嘉学者之理必说
乾嘉理必(道理上的必然)可以戴震“《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为标志:
《尚书·尧典》:“光被四表。”
戴震曰:“《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与王内翰凤喈书》)
段玉裁乃皖派理必之中坚。兹姑举《说文解字•米部》“粒,糂也”一例,以见其概。《段注》曰:
按,此当作“米粒也”。“米粒”是常语,故训释之例如此。与“䆃”篆下云“䆃米也”正同。《玉篇》《广韵》粒下皆云“米粒”可证。浅人不得其解,乃妄改之,以与糂下“一曰粒也”相合,不知粒乃糂之别义,正谓米粒。如妄改之文,则粒为“以米和羹”矣,而一曰粒也何解乎。今俗语谓米一颗曰一粒。《孟子》:“乐岁粒米狼戾。”赵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皋陶谟》:“烝民乃粒。”《周颂》:“立我烝民。”郑笺:“立,当作粒。”《诗》《书》之“粒”皆《王制》所谓“粒食”;始食艰食、鲜食,至此乃粒食也。…… 按,此篆不与糂篆相属,亦可证其解断不作糂也。[1]

许慎《说文解字》
“米粒”之“粒”今本《说文》作“糂也”,段注谓“此当作米粒也”—— 径改许书且强调说“断不作糂”。其何以如此自信裁断,乃“断”字之后的理证原理。其“论证程序”可归为如下十一步[2]:
1. 指出错误:“当作‘米粒也’。”
2. 发现《说文》的训释原则,亦即“训释之例”:“按,此当作‘米粒也’。‘米粒’是常语,故训释之例如此。”
3. 内证,亦即《说文解字》本书内的“训释之例”的证明:“与‘䆃’篆下云‘䆃米也’正同。”首先,段氏给上面“训释之例”找到同类的现象:“䆃”训“䆃米”和“粒”训“米粒”一样,都是用“常语”解释被训释词的例子。以此给开篇的结论“粒,糂也”“当作‘粒,米粒也’”的“当作”建立证据。
4. 旁证:“《玉篇》《广韵》粒下皆云‘米粒’可证”。这是进一步从旁立证:《玉篇》《广韵》的解释和《说文》一样,应当是取自《说文》同样的“常语”的训诂。由此可证原本《说文》当作“粒,米粒也”。
5. 误源的推测:“浅人不得其解,乃妄改之,以与糂下‘一曰粒也’相合。”这里是揭示致误的客观原因:因为《说文》 “糂”下有“一曰粒也”的训诂,不学无术的人就把《说文》“粒”下的“米粒也”之训,改成了“糂也”,以便和“糂”下的“一曰”相合。
6.用归谬法驳斥妄改所导致的荒谬结论:“不知粒乃糂之别义,正谓米粒。如妄改之文,则粒为‘以米和羹’矣,而‘一曰粒也’何解乎。”
这里必须把《说文》原文的“糂”和妄改的“粒”对勘,才能知其谬误所在:
因为:“糂,以米和羹。”
如果:“粒,糂也。”
那么:“粒,以米和羹也。”
荒谬:“糂,以米和羹也。一曰:以米和羹也”。
结论:“粒”不可能是“以米和羹”,所以“粒,糂也”必误无疑。
7.再引俗语以为证:“今俗语谓米一颗曰一粒。”
8.复引古籍用例以为证:“《孟子》:‘乐岁粒米狼戾。’赵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
9.延伸理证与《诗》《书》“粒”字之用例 —— 既是预测,也是反证:《皋陶谟》:“烝民乃粒。”《周颂》:“立我烝民。”郑笺:“立,当作粒。”段玉裁指出:“《诗》《书》之‘粒’皆《王制》所谓‘粒食’;始食艰食、鲜食,至此乃粒食也。”
10.最后殿以《说文》例字之证:“此篆不与‘糂’篆相属。”可见“粒”、“糂”非同类、同义之字,由此可证二字词义之不同;
11.结论的必然性:“可其解断不作糂也。”

段玉裁
段氏最后的结论非常自信和决断:“其解断不作糂也。”这个“断不”的“断”就是太炎评赞乾嘉皖派“理必”学术特点的“任裁断”的“断”。乾嘉理必,师生珠联,段王璧合。王氏念孙之理必,多在《广雅疏证》,其最典型者如卷一上“捊,取也”条:
凡“与”之义近于“散”,“取”之义近于“聚”;“聚、取”声又相近,故“聚”谓之“收”,亦谓之“敛”,亦谓之“集”,亦谓之“府”;“取”谓之“府”,亦谓之“集”,亦谓之“敛”,亦谓之“收”。“取”谓之“捊”,犹“聚”谓之“裒”也;“取”谓之“掇”,犹“聚”谓之“缀”也;“取”谓之“捃”,犹“聚”谓之“群”也。[3]
其中论证之必,可归为王氏所独创之生成模拟逻辑:
X和Y都具有属性p、q、r,
如果p、q、r具有衍生关系,
且X和Y具衍生关系,
则X和Y的属性系列可以被预测和验证为真。
这里推证步数殊为繁复,暂从略。有意者可参拙作《论王念孙的生成类比法》[4]。
二、乾嘉学者之发明说
2.1乾嘉学者论发明
乾嘉学术的路数是理必,乾嘉学术的目标则是发明。什么是发明?发明是乾嘉学术范式的基本原则、方式与目标。兹粗胪数端,以见其详:
纪昀评戴震曰:
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戴震全书》)[5]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曰:
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6]

王念孙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有云:
吾友段氏若膺,于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剖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7]
江沅在评价《说文解字注》时也用“发明”二字以为说:
先生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已矣。…形以经之,声以纬之,凡引古以证者,于本义、于余义、于引申、于假借,于形、于声,各指所之,罔不就理。… 县(悬)是书以为的,则许氏著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说文解字注•后序》)[8]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则以“发明意恉”揭橥其学:
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廿八篇紬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论《毛诗》“终风且暴”、《礼记》“此若义也”诸条,发明意恉,涣若冰释,益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9]
尽管上引诸条中的“发明”所指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含义都是“发之使明”。解释现象背后的原理,这就是“发明”的真义之所在,这就是乾嘉学术的真谛之所在。
2.2传统学术的旨要在发明
发明不是一个简单的褒词(也不是英文to invent 或invention之意),它是传统学术的最高境界。《马氏文通•序》有言曰:
刘氏《文心雕龙》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顾振本知一之故,刘氏亦未有发明。[10]
言下之意,自己的研究则多有发明。太炎先生论及季刚的十九纽时,说:“此亦一发明。”[11]本师颖明陆宗达先生评述皖派,其所强调及注重者亦用“发明”:
…以戴震为代表的“订误”派,这一派以纠正旧注、创立新说为主。目的是:发展语言文字科学,批判旧注、发明新义,从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使训诂学进一步提高。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等人都属于后一派…(陆宗达《训诂浅谈》)[12]

章太炎先生
如何才堪称“发展语言文字科学”?根据本师之说,不仅要“批判旧注”,更重要的是“发明新义”。什么叫“发明新义”?就是要“提出自己的新理论”。事实上,吴宓1919年12月14日记载和陈寅恪的谈话,就用“发明”这一术语来阐释陈寅恪惊世骇俗之“新理论”。他说:
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中国之中世…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吴宓《吴宓日记》)[13]
我们看到,凡秉承乾嘉传统之学者,无不以“发明(或发覆)”标举学旨,而章黄更进一步,提出“真发明”的概念。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云:
清代算学,以梅文鼎为首。…自梅氏之后,几何学渐渐通行,此本西法,不过将中国旧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为第一也。…真有发明者,当推李锐之四元说,李氏仅讲测天,不讲步历,所以高人一等。[14]
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云:
来书谓近治《说文》,桂氏(馥)征引极博,而鲜发明,此可谓知言者。[15]
本西法者,虽能“推明(旧法)”但也不算“发明”;守国学者,虽称淹博(古籍)但也不算“发明”,—— “发明”之义,亦大矣哉!
三、黄侃之发明论

黄侃先生
把“发明”作为一个学术原则正式提出来的第一人,是黄季刚(侃)先生。这可以从吉川幸次郎介绍季刚先生的发明之说清楚地看出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之《黄侃给予我的感动》云: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
以这句话来看(即“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
“中国之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但实际上要达到一个结论,其中运用逻辑,或归纳或演绎……演绎是非常有难度的,必须对全体有通观的把握。绝不是谁都有能力这样做的,于是,就认识到中国学问,确实是需要功底的。[16]
“发明”被季刚先生理解、揭举或发展为一个富有“学术范式”概念的代名词。他划时代地指出:当时正在进行着从发明到发现的学术范式的转型—— 亦即从“主尚道理的揭示”到“推重材料的发现”的转型。吉川幸次郎《与潘景郑书》云:
幸次郎于此公(指季刚先生——引者)私淑有年,昔江南之游,税驾金陵,亦职欲奉手此公故也。通名抠谒,即见延接,不遗猥贱,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17]
为了真正理解季刚先生的学术转型说,我们有必要重申什么是发明的准确定义。首先,“发明”的字面意思是“发之使明”,它和“发覆”(即“使覆盖隐藏的道理彰显出来”之义)一样,在学术范式的理念上,是一致的。严格地说,学理概念上的发明指的是:揭示“前之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18]的规律或秘密,才是发明,它和发现不同,发现是找出本已存在而前人没有见到的材料或事物(不同于“前人没有提出的道理”)。
五四以来“发明替而发现兴”的学术转型,至今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和警觉。但学术转变的趋势和原因,早就有人意识到了。王国维总结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时说: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道咸以降,治学已“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19]。而五四以来,政治风俗变革更甚,于是“发见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这就是学术转型的社会原因。
发明这一术语、这一思路、这一学理,今人久违已近乎一个世纪,即使本文提出这个问题,也未必能够引起广泛注意,或反而遭到声讨之声也说不定。即便如此,如王念孙所云:“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原因很简单,没有发明,学术无以自立。理既如此,近代中国的学术为什么会抛弃这个“缺之不可”的学术范式呢?下面的讨论可以提供思考这个原因的一个新视点。
四、傅斯年之“一分材料一分货”

傅斯年先生
4.1傅斯年的再造时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
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说是中国学艺的再兴时代。[20]
(按:傅氏所谓的“再兴”是什么?略而言之或可归之为“学说上的外来主义 材料学上的经验主义”。我想,这或许就是傅斯年“再兴”时代的核心所在,今观斯年先生之史学,可以知其情[21]也。)
4.2史学=材料学
1928年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他说: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22]
顾颉刚更直截了当,开宗明义地说: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创刊词》,《宝树园文存》卷一)
对后代以至于今天仍有深重影响的傅斯年的“研究工作旨趣”,把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指定为: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这里不仅建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材料之学,而且提出“推论是危险的事”的警告,甚至加上了一个“不诚信”的道德评判一一这是重伦理的国人最在乎的事情。推论当然要演绎,而傅斯年“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背后,最基本的学术原理是归纳(包含综合逻辑)。这无疑就是中国近代学术重归纳、弃演绎的源头之一。
4.3材料与学问
据顾颉刚回忆,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刊物把北大文学院的国粹派骂倒”。胡适与黄侃斗法的高潮是傅斯年的反水。据悉,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后,傅斯年便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刮目相看,与黄侃等章太炎门生逐渐疏远,转而投到了胡适门下。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冯友兰等20多名学生办了一份《新潮》杂志,响应新文化运动。傅斯年原来是黄侃的爱徒,对于他的这个转变,陈独秀有些不敢相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陈独秀一开始还怀疑傅斯年是黄侃他们派来的“奸细”。
几十年过去,材料学派如何评价?这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钱穆有言值得反思,他在《〈新亚学报〉发刊辞》中说:
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此乃以考据代学问,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其所求为自己之知识者,在求知别人之罅缝漏洞而止。然此绝非由于虚心而内不足而始有意从事于学问之正轨。[23]
钱穆的话似乎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更没有改变风气;今天罗志田从另一个角度继续这一话语:
在乾嘉汉学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24]
我在《王念孙“生成类比逻辑”中的必然属性及当代意义》里也曾指出:
事实上,根据我们对乾嘉理必思想的发覆以及本文对王念孙“生成类比推理逻辑”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乾嘉发明之学的学理思想没有充分揭橥于世以前,对清代或近三百年的学术不可能从根本上做出科学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学术史,若非隔靴搔痒,也属不能客观。[25]
更有令人深思的异响,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一位学术领袖未经深入研究的言论可以对几代学人的历史记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26]
这里我们不想做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只提出问题,供今人以及后来学者的比较(见下文)和思考。
五、乾嘉奇葩(俞敏语)——黄侃科学发明举隅
与材料的发现形成对比的,是章黄的发明之学[27]。这里仅粗胪数端,以见一斑。
5.1发明“古无上声”
季刚先生的古无上声说完成了远古汉语没有声调的空前假设。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推理步骤看出来。
第一,季刚先生《音略》说:“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唯有平入而已。”[28]古无声调说还需要一个上古音系的基本事实的对勘,才能奏效。这就是岑麒祥先生说“入声非声说”。入声本是音节韵尾的语音特点(-p,-t,-k),属于音段成分,不是超音段现象。据此,我们有:段 黄 岑 = 古无声调的结论。亦即:

为什么呢?如果传统的四个声调的中没有去声和上声,而所谓入声又不是声调,那么远古汉语就只有一个平声。单独一个声调无法形成“声调对立”;没有声调对立则不成声调系统;没有声调系统则远古汉语就是一个无声调的语言。不难看出,古无上声是上述推理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没有这个核心环节,不仅段玉裁的“古无去声”不能独立作为“无调”的充分条件,就是再加上岑麒祥的“入声非声”,也对远古声调系统的有无起不到必然性的决定作用。因为上声和平声,仍然可以构成一个两调系统的语言。然而,有了“古无上声”,即使没有岑氏的“入声非声”,古无声调[29]的推理也能俨然而立,因为入声(-p,-t,-k)原本就不是超音段的成分,而单独一个平声不可能构成语言的声调系统。没有对立、没有区别性的特征的语言现象,不能构成该语言的系统。
当然,上面的推理在“材料主义”的思维系统里恐怕不足为信,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推理是危险的”——傅斯年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主张远古汉语没有声调的学者里面,基本都主从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的声调来源说的,而不知或忘记这个结论本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季刚先生“古无上声”的发明中推演出来[30]。我们是相信早期中国学者的发明和推演呢?还是仅据西方学者后来的材料和结论呢?这当然不仅是个数典忘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术理路的问题。事实上,章黄以来,中国(包括西方)学者几乎没有人从上古汉语语言本身的内部事实上,发明“古无声调”的理证[31]——这是不是材料主义的后果呢(因为“上古没有声调的结论”是归纳不出来的)?值得深思![32]
5.2发明语体二分之必然:“文与言判,非苟而已”;预测“我手写我口”(白话文)必不单行
季刚先生“文与言辨,非苟而已”的发明,预测了“我手写我口”(白话文)必不通行于任何语言的必然。今天汉语正式体的创新和发展,证明了此说泰山不移。先看季刚先生的理论:
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且夫人为之事类,皆爻(效)法于他,罕能自创。嫛倪效语,庄岳教言,陶染所成,若出天性。而文章既有定体,美恶复有公评。举世名篇,嗟不盈掬。拟之作式,必是前代之文。模放既久,与之同化,句度声辞,宛有定规。所以诗歌虽广,常用者不逾四五七言;形体猥多,恒见者大都止三五千字。
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此又无足怪矣。尝闻化声之道,从地从时。从地则殊境不相通,从时则易代如异国。故越歌《山木》,待楚译而始通,秦语素青,俟郑言而方晓。况以近事,昆腔宾白,非吴侬则厌其钩辀;元代王言,在今人必迷其句读。是则文兼常语,适使胡,不若一秉古先,反得齐同之律。综上所说,文与言判:一由修饰,二由迁移,三由摹放,四由齐同。非苟而已也。[33]
注意:季刚先生的论证里面,“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是原因,“方圆异德”是属性,“雅俗殊形”是结果。根据这一结果,季刚先生揭示出或发明了人类语言语体的一大规律:“文与言判,非苟而已”——意思是:书面语(文)和口语(言),或者正式语体(书面/文)和日常口语(言)的区别和不同(判),不是偶然或随意的结果。显然这一发明回答了为什么五四运动“我手写我口”不能贯彻到底(用口语写正式文件或学术著作)的原因所在。当然,当年的胡适是要把“手口一致”贯彻到底的。据悉:胡适曾让学生做文言辞聘说明,然后择出一则字数最少、意思最全者,如下:“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适曰:“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34]一时传为佳话(白话胜于文言的)。今天看来,这五字虽短,但语体轻率而不严肃。今天的正式辞聘书,很少(或根本没)有径言“干不了,谢谢”这五个字的。何以然哉?“文与言判辨,非苟而已”的规律作用,斯其故也。
5.3古音28部19纽:语言学互补分布法的发明与使用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恐怕没有比季刚先生28部19纽的遭遇更富有学术史的意义了。仅此一例,就值得学术史家大书而特书,以见近代学值翻覆、学理变化之沧桑。为清楚起见,兹简介背景如下。
1928年,林语堂在《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中对古本韵与古本纽说冠以“循环式论证”。
章太炎以“精清从心邪”本是“照穿床审禅”之副音(见《新方言》卷十一),遂毅然将二种声母合并,而以“精清”等归入“照穿”等,这已经来得武断。更奇怪的,是黄侃的古音十九纽说的循环式论证。黄氏何以知道古音仅有十九纽呢?因为在所谓“古本韵”的三十二韵中只有这十九纽。如果你再问何以知道这三十二韵是“古本韵”呢?那末清楚的回答便是:因为这三十二韵中只有“古本纽”的十九纽。这种以乙证甲,又以甲证乙的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实则黄氏所引三十二韵中不见黏颚声母并不足奇,也算不了什么证据,因为黏颚的声母自不能见于非黏颚的韵母,绝对不能因为声母之有无,而断定韵母之是否“古本韵”,更不能乞贷这个古本韵来证明此韵母中的声母为“古本纽”。[35]
1935年,王力在《中国音韵学》(1956原版重印更名为《汉语音韵学》)里说:
我们不反对拿《广韵》的系统去推测古音系统…但是,我们不能赞成黄氏拿《广韵》的反切法去做推测古音的工具,因为反切法是后起的东西,与古音不会发生关系。黄氏以“古本纽”证“古本韵”,又以“古本韵”证“古本纽”,在论理学上犯了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的毛病。[36]
胡文辉(2010)的总结道:
林语堂指黄氏的古音十九纽说为“循环式论证”…;张世禄承林说,亦称黄说为“循环式的乞贷论证”;王力更将“古本韵”学说批评得体无完肤。此外,李方桂谓黄氏未做过任何古音构拟的工作,而且“没有出过什么有影响的书”;周法高也说:“…黄季刚先生的二十八部(晚年又分为三十部),把阴阳入分立,是相当有道理的,在中国音韵学史是有地位的;但是他的一四等为古本音的学说就不合语言学原理。”[37]
这种声音之下,并非没有反悟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黄淬伯曾与徐复先生谈到此事:
往年于季刚先生古音之学未曾深究,反信林语堂“乞贷论证”之妄说,受其瞽惑。及寻绎《音略》诸文,乃知先生声与韵“相挟而变”之说,倜然与唯物辩证之恉相会,岂不伟欤?[38]
黄典诚更推崇季刚先生之古音学,谓:
古音之学,以季刚先生之说为最谛,其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与闽南方言无不淹若合符,妙达神恉,唯先生有焉![39]
事实上,林语堂晚年在《八十自叙》中也认宗黄季刚先生:
分别古韵分部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由于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的瑞典的学者高本汉,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40]
最令人关注的是何大安先生在《声韵学中的传统、当代与现代》中,独具慧眼,发明季刚学说之底蕴,说:
这个论证程序的关键是“相挟而变”。就我所知,在黄侃之前,从没有人提过声母韵母“相挟而变”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推广到什么地步,例如上述步骤是不是一定能够成立之类,容可再作考究。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有很丰富的意蕴,值得深思。首先,它不但预设了静态的声韵配合(结构),而且预先了声韵母的互动(生成)。其次,相挟而变这个概念自然会要求我们对声韵的结合形态作动态的、历时的观察,因而就汇出了一种在他之前的古韵学家──即使是审音派的古韵学家──所不曾想象过的方法。由相挟而变推知古本韵,这不是“归纳”,而是因演绎所作的“预测”;预测的结果与前人的结论相合,这是“证明”。[41]
最近,李葆嘉(2016)也撰文指出:
黄侃不缺乏“音类”与“音值”区分的观念。所谓“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不可用“西洋构拟音值”(争议太多,甚至有人认为是“示意图”“鬼画符”,只有相对参考性)来理解,只是一个与“今变音”对待的术语。黄侃认为古本韵大抵在一四等,因此二十八部韵目取一四等字以寓其古读。至于具体音读,尚需另加考订。[42]
李说洋洋洒洒二万余言,引证广博但却未及何大安之说而一语破的(不是归纳而是因演绎)。李文论证虽可信,但仍需补充如下数点而后安:
1.古本音是相挟而变的系统中的“古本音”。因此“古本音”是相对“今变音”的系统“支柱”。
2.古本音不是构拟,构拟是根据对系统的理解给单个音位和音位变体拟定的读音。
3.拟音永远不是古代的真实读音(没有录音,无法得知2000年前的真实读音),唯其如此才称此法为“拟”——它是理论的推测,不是原声如何的论断(因此有人用“读不出来”作为诋毁的武器,不仅有失公允,实在是打错了目标)。就此而言,无论黄氏的“古本音”还是高本汉等的“拟音”,都不是上古的实际读音。
4.古本音和今变音的关系是古代语音系统的真实关系(以及后来变化结果的真实关系)。
5.古本音和今变音是贯通“古音系和今音系”的动脉(如童年、成年、老年的脊柱)
6.拟音的最高境界,亦当如是。
有了上面这种理解,李葆嘉上面论述中有关“音类”、“音值”、“寓其古读”、“具体音读”等说法和概念,才便于理解和成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是用“互补分布法”推演出来的,这一点至今鲜为人道:
大抵古声于等韵只具一、四等,从而《广韵》韵部与一、四等相应者,必为古本韵﹔不在一、四等者,必为后来变韵。[43]
古声十九类,必为一、四等。中虽间有二、三等,而十九声外,碻无一、四等。《广韵》中于等韵全韵皆为一、四等者,即为古今同有之韵;于等韵为二、三等者,必非古音。何以故?以其中有古所无之声母。[44]
其中的道理可以分析为:
甲、互补分布
十九类 均为一、四等;
十九外 均为二、三等。
乙、例外与例内
a 十九类也有二、三等;
b 十九外绝无一、四等。
按:若无“十九声外确无一、四等”的发现,上之互补分布则无法成立。因有(乙b),则互补分布可以成立,如下所示:
十九类 均为一、四等
十九外 均不为一、四等
而且可以证明“十九声”和“一/四等韵”之间的古今之对应关系。据此可进而推出:十九外和非一、四等韵的必然的变异关系——十七纽和二、三等韵为必然的变异,否则无法解释17纽不在三四等韵的事实。更重要者,在互补分布之上,季刚先生复以旁证凿实之:
古声无舌上、轻唇,钱大昕所证明;无半舌日(按,当作:“半齿日”)、及舌上娘,本师章氏所证明﹔定为十九,侃之说也。(《音略‧略例》)[45]
古声数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钱竹汀知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吾师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侃得陈氏之书,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数纽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音略‧古声》)[46]
28部19纽的构建是近代语言学科学发明的典范,其中科学方法的发明和使用,我认为至少有如下诸项:
1.互补分布现象的发现与互补分布法的创发(这后一点更具科学方法发明的意义);
2.古音成果旁证,凿实互补分布的创见;
3.声韵相挟的演绎,预测古韵类别(因为声韵相挟,故可以声测韵而得28部);
4.互补咬合法定案。(咬合法Interlocking Method)[47]
互补分布是西方结构主义的科学法宝,这一点人人皆知。然而,人所不知的是与西方没有(哪怕间接)对话的章黄学术,居然也在自身学术体系中创用互补分布之法,并成功地发明了上古音系(28部19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科学思想的巨大威力。
以上三点,(1)古无上声的无调推演、(2)文与言判的语体规律、(3)声韵相挟的互补分布,即使在今天,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语言规律或科学发现。而这些规律的发现、理念的发明,从本质上说,是精神的产物、思想的结晶;单凭资料主义,是无法创造和企及的。
六、结语
卞孝萱等在胡适的《治学方法•前言》中说: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胡适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而其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在20世纪的新旧交替之际,他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治学理论和治学方法。通过认真的探索,他(胡适)确信有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广泛、最适用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实验主义”,其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不盲从已有的定论,不迷信圣贤和权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用十分精炼的语言把这种治学思想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50]
据此,在20世界的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治学理论和方法的精髓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这一精髓的精髓就是崇尚怀疑精神。后来的疑古风潮很大程度上即从此而来。什么是疑古?用胡适自己的话说:“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研究国故的方法》)于是就把这十个字领进了笛卡尔“怀疑一切”(skepticism)边缘,其结果,“可疑”之风遍天下。而“疑古”自身,根据“宁可疑而错”的潜在逻辑,也成为了可疑对象。于是整个民族学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意识悖论”的道路之上。当然,悖论在哲学上是研究深入的起点,然而如果整个民族、国家,百年来拿着一个深含哲学悖论的命题作为整体学术的原则和指导,其影响结果如何,可想而知。当时的疑古派不能说不是以这样的原则和态度为其理论后盾而出现的、而发展的。
大胆假设推动着疑古,而小心求证则驱使学人发现新的材料。这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 小心、尽心、全心地“四处找材料”的学理动源。材料主义的百年传统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建立起来的。近代影响中国学术思想最强烈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另一个是傅斯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 “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无疑,这与乾嘉皖派诸老、章黄的学理路数(范式),迥然有别。

章黄学派代表人物——章太炎先生与黄侃先生
什么是章黄的学术理路呢?本文认为:章黄之学的核心方法是“综实见理,以必验实”(综览现实对象,发见所以之理;运用理必之法,期验所证事实)。这从上文所示之章黄发明之学则可得而见,今更有明证:
夫为学者…有所自得,古先正之所覭髳,贤圣之所发愤忘食。员舆之上,诸老先生所不能理,往释其惑,若端拜而议,是之谓学。(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51]
今世顽固者之诋泰西,亦陋见也。(黄侃《黄侃论学杂著·汉唐玄学论》)[52]
学术如学艺,技有上下,境有高低。古往今来,学者纷纭如烟;而其所得、所能、所释、所议、所见者,则不均一。太炎先生将其分为五类:
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章太炎《章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 [53]
这里所标举学术至高之境者为“发前修所未见”。黄季刚先生的28部19纽正是“发前修所未见”的学术典范。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的方法和结论持有不同的看法。综而言之,有的批评他的研究过程是主观的演绎,而不是客观的归纳;还有的说他是从原则出发,先有结论,然后用材料去证明他的结论。具言之,他先从等韵中寻找 “变纽” 所在的等列,而这些“变纽” 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已经证明了的。继而,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这个假设(演绎!)在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古韵分部结论(二十三部。收喉入声独立则二十八部)中得到验证,从而反过来又证明这些古本韵里所没有的声母都是“变纽”。议者认为这是循环论证。毫无疑问,“循环论证”“就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结论”(参林语堂1928、王力1982、胡文辉2010等)显然,这样的看法与上面我们分析的28部19纽的构建是“近代语言学科学发明的典范”的结论正相反。比较:
1.黄侃先从等韵中寻找“变纽”所在的等列 = 互补分布现象的发现与互补分布法的创发(他发现“变纽”都出现在二三等,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
2.“变纽”绝大多数是钱大昕、章炳麟已经证明了的 = 古音成果旁证,凿实互补分布的创见;
3.于是以为一四等韵都是古本韵;反过来又企图证明这些古本韵里所没有的声母都是“变纽”= 声韵相挟的演绎,预测古韵类别;
4.这样循环论证 = 科学的咬合法(interlocking method)
5.引出了很不合理的结论 = 逻辑的合理性与现实的正确性(按,李方桂和俞敏的上古音构拟系统,都与黄侃的19纽冥合无间,证明黄氏结论的正确性)。
这里与本文观点最不同的是:一般认为季刚先生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主观的演绎而不是客观的归纳。”显然,这就潜在地把归纳视为正确的方法而把演绎归入错误的手段。这正是经验主义和材料主义在方法论的选择上的必然与极至。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乾嘉(东方)诸老以及地球另一端(西方)的伽利略、罗素、乔姆斯基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演绎作为学术的最高取径。我们知道(至少现在),演绎没有不是主观的(不是今天主观主义意义上的“主观”)。科学是思想,科学原理的获取和推演,都离不开演绎。因此,科学的发明也无不是主观的(同上)。主观是理性的,它和非科学、非逻辑的“主观主义(=臆说)”不是一回事。相对演绎而言,归纳是经验的。五四以来我们的学术主尚的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这没有错,但因此而排斥演绎性的发明之路,就无法启导后学自创理论了。五四以后中国语言学只善归纳,不尚发明的现实,也就不仅不难理解,甚至是必然结果。[55]故此,重温“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的旧训,不能不激励我们发出“中国学术回归理性”的呼声。
注释
[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经韵楼藏版,总第331—332页。
[2]冯胜利:《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中文学术前沿》第9辑,2015年,第99—117页。
[3][清]王念孙著,钟宇讯整理:《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4]冯胜利:《论王念孙的生成模拟法》,《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77—88页。
[5]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七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77页。
[6][清]王念孙著;钟宇讯整理:《广雅疏证》,总第2页。
[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总第1页。
[8][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总第788页。
[9][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总第2页。
[10]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11]章太炎《菿汉微言》曰“黄侃云:歌部音本为母音,观《广韵》歌戈音切,可以证知古纽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彻、澄、娘、照、穿、床、审、禅、喻、日诸纽,歌戈部中皆无之,即知古无是音矣。此亦一发明。”
[12]陆宗达:《训诂浅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64年,第11页。
[13]吴宓撰,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1924》,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03页。
[14]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载章太炎撰,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15]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载章太炎撰,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40页。
[16]吉川幸次郎:《黄侃给予我的感动》,载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17]吉川幸次郎著:《与潘景郑书》,载程千帆著,唐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1—92页。
[18]李庆福尝引述顾炎武语:“著书必前之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 李庆福记:《蕲春黄先生雅言札记》,《制言半月刊》第41期(1937),第4页。
[19]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载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3,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27页。
[20]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1卷4号,第702页。后载林文光编:《傅斯年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21]情,实也。
[2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后载林文光编:《傅斯年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 第64页。
[23]钱穆:《发刊辞》,载《新亚学报》第一期,1955年8月。
[24]罗志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论》,载章太炎撰,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5]冯胜利:《论王念孙“生成模拟逻辑”中的必然属性及当代意义》,载《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1(总第 辑),第1—26页。
[26]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27]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自然属发明之作。兹事甚大,容另文专述。
[28]黄侃:《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2页。
[29]这里的“古”指“远古”。
[30]这也是国人重材料(奥德里古尔的越南语声调的材料)而轻推理(季刚先生结论的逻辑必然)的结果之一吧。
[31]注意:这里说的“理证” 不是“ 例证” 。“ 没有人发明理必推理之法证明‘ 古无声调’” ,而古无声调的“ 例证” 则不乏其例,譬如郑张尚芳先生有关远古上声为“ 小称缀” 是也。
[32]笔者曾以“甲骨文无句末语气词”之事实,以及两周汉语“吾平我上”及“疑词平,断词上”等相关事实,推证“殷商汉语无声调”的必然。附说于此,以求正方家。
[33]黄侃:《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34]王凯:《胡适与黄侃的新旧之争》,《法治周末》网站,http://www.legalweekly.cn/article_show.jsp?f_article_id=12937。
[35]林语堂:《语言学论丛》,《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46页。
[36]王力:《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2页。
[37]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8]收入徐复:《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前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39]收入徐复:《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前言》,第4页。又,黄典诚在《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中重申:“我是相信上古只有十九纽的。因为我自己的母语闽南方言,号称为‘十五音’系统(只声母而言),若补上被清音化了的四个全浊声母,恰好就是十九纽:p p‘ (b) m, t t‘ (d) n l, k k‘ (g ) ŋ h, ts ts‘ (dz) s, ø。而在福建北部建瓯的石陂,十九纽是不多也不少的。”见《黄典诚语言学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40]刘志学主编:《林语堂自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41]何大安:《声韵学中的传统、当代与现代》,载中华民国声韵学学会:《声韵论丛》第十一辑,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
[42]李葆嘉:《对非议或误解黄侃古音学的澄清(上) 》,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6年第1期。
[43]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399-400页。
[44]黄侃述,黄焯编:《文字音韵训诂笔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
[45]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62页。
[46]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69页。
[46]参冯胜利(2015)《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中文学术前沿》Vol.9:99—117.其咬合法取自巴赫(1964),原文是:It may appear as if our reasoning iscircular in a vicious sense. We use various rules to argue for aspects of thetheory and then turn around and use the theory to argue for the correctness ofthe rules. But this impression is based on an incorrect view of the process ofscientific reasoning. Reasoning in an empirical science does not proceed in alinear fashion, (as I shall stress here). It proceeds on all frontssimultaneously. We are not constructing a pyramid but rather a keystone arch, in which all the pieces must be held up at once.”(Emmon Bach 1964:143)
[47]蒋绍愚:《从〈左传〉中的‘P(V/A) 之’看先秦汉语的述宾关系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八辑,2014年,第1—18页;黄正德:“Syntacticanalyticity: The other end of the parameter.”Lecture notes,2005 LAS Linguistic Institute, Harvard University andMIT.;冯胜利:《轻动词移位和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语言科学》2005年第一期;徐丹. Typological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6.
[48]“汉语形式语法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韵律语法。将韵律看作一种制约语法结构规则的形式,是近20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参李宇明主编:《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99页。
[49]赵元任著,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第221页。
[50]Berlin在《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一文中说,一个学科的真正价值取决于它所创造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他所发现的基本事实The academic value of a subject seems to me to depend largely on theratio of ideas to facts in it.(Berlin 1975:292)。这种“理论重于事实”的学术价值观和我们的材料主义的思想正相反。
[51]胡适:《治学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52]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第102页。
[53]黄侃:《黄侃论学杂著》,第485页。
[54]章太炎:《章太炎文录初编》,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55]王力:《黄侃古音学述评》,载王力著《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85—386页。
[56] 1981年前后(本人读研究生时),北京老一辈语言学家吕叔湘、王力等提出的“求实”口号,也应当看作五四以来经验主义理路下的必然产物。

励耘语言学刊书影
文章原载于《励耘语言学刊》2018年第2辑,页1-21

冯胜利教授
先后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陆宗达先生,为章黄学派传人。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中文部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韵律语法、语体语法、历时句法学、韵律文体学、乾嘉科学思想史。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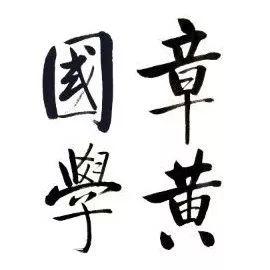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辑:冯可然
专栏画家:黄亭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