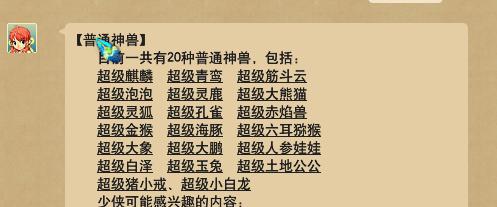“大自然从不拉直线。”
说这话的时候,武汉大学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张箭飞正坐在樱花树下品茗。时有粉色的花瓣飘落,短暂停留在她的围巾上、发梢上。
原话出自建筑界的传奇———安东尼奥·高迪之口。他说,大自然不存在直线,直线属于人类,而曲线才属于上帝。
高迪说这话,是希望建筑设计能够回归自然,只有源于自然,才能和自然融为一体,一如他笔下绘出的那些童话般的“城堡”;张箭飞说这话,则锐利了许多,剑指当下正在兴起的形状方正、种类雷同、由外来植物主导的花海、花田、花带。
张箭飞是国内较早从事风景研究、风景与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主持引进了一系列国外风景研究的经典之作,包括《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风景与记忆》《风景与权力》等。这个曾经冷僻的研究领域,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美丽乡村的打造等,而日益受到关注。
「装饰帝国的“权力与荣耀”」

曾经的植物猎人
上书房:武汉大学是赏樱胜地,但有一种植物,似乎更具湖北、具体来说是宜昌特色,那就是俗称樱草的鄂报春花。
张箭飞:是的。报春花是个大家族,多达550个原种,其中五分之四、400多个报春花原种,产于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多见于滇、藏、川、陕、鄂诸省山地,植物学界公认中国喜马拉雅山地区是报春花属多样性和分布的起源地及中心。中国有“报春之国”之称,与“山茶之国”“银杏之国”等名号一起,标记了我国在园艺植物史上无可比拟的地位。
若单就报春花的种类而言,宜昌远不及四川、云南和西藏的丰富。然而,它特有的藏报春、鄂报春、宜昌报春、巴蜀报春、卵叶报春等,是杂交品种最重要的亲本,繁育出了英国人偏爱的粉红、淡紫、深蓝色系的报春花。虽然在近半个世纪里,英国陆续从后三个地区引种近百种报春花,但多数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更适合藏于植物园,而难以推广。有“植物猎人”之称的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亨利·威尔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四次来中国,在他见到宜昌的植物后,反复强调宜昌的重要性及其与欧美报春花的关系。他说,宜昌“有很多著名的开花美丽灌木”,是“许多园林钟爱者寻找花卉原产地的选择”,报春花属是它最有代表性的13种植物之一。

武汉大学成赏樱胜地
因花形、花色宛如樱花,樱草在日本也风靡不衰。自江户时代始,每逢樱花季,全国各地都会举办樱草展览会,吸引众多游客造访。樱草时尚带动园艺品种改良和大量出口。到20世纪下半叶,欧美的植物园和公园里随处可见日本樱草芳踪,以致著名园艺家柳宗民宣称:“日本各地都有野生樱草,不少人便误以为它是日本特有的品种,其实樱草在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都有分布,并非日本独有。”威尔逊也证明这种植物“实际原产中国,在日本只是栽培”,确言之,原产中国宜昌。
上书房:但与英伦相比,日本的赏樱(草)热情似乎有所逊色?
张箭飞:英人对于报春花的挚爱历久弥新。自16世纪以来,报春花一直高居花卉审美榜单,不仅构成许多英式结纹园(knot garden)的重要元素,而且屡屡再现于诗歌和绘画之中。莎士比亚、罗伯特·赫里克、华兹华斯、约翰·克莱尔、丁尼生等人都反复歌咏或描写报春花———“苍白樱草”“早开樱草”“五月甜蜜”“金色花朵盛开”。他们用报春花象征“优雅”“怅惘”“冥思”“豆蔻芳华”,甚至是自然神性。
实际上,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400年间,某一时段、某一特定植物,主要是外来观赏植物及变种,总会在英国风行一时,如土耳其郁金香、埃及睡莲、澳洲鹤望兰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因英国本土植物种类相对贫乏,更因海外扩张激发出的追猎异域植物的热情。在维多利亚时期,园艺的时代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是热带兰热还是绿绒蒿热,总是与帝国扩张节奏同频共振;从南美腹地到世界之巅,英国的探险家、博物学家追随本国商船或军舰,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搜罗全球奇珍植物,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土。
小小一株樱草,既是文学艺术家吟咏、描绘的对象,又装饰了帝国的“权力与荣耀”。
「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

看世界
上书房:这些年来,您从外国文学研究转向风景与文学的研究、风景的研究。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风景研究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您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风景研究吗?
张箭飞:在聊风景研究之前,我们先来说说何为风景。
一说到“风景”,很多人脑海中会自动播放一幅幅画面,与旅游广告、电影取景地、风光视频,甚至朋友圈打卡的网红景点连接起来。的确,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风景与美景、风光、景色、景致,甚至风土同义,是“供观赏的自然风光或景物”。英语中的风景一词landscape,有时译做景观。这个词源自16世纪荷兰画派使用的德语landscipe或landscaef,原意是指眼睛一下能抓取(目力所及)的一片土地或者景色。尽管此后观念史层面的“风景”意义在不断地扩容和嬗变,但它的视觉(visible)属性一直被保留着。你想想,我们在旅途中拍照时,是不是总会下意识地启动图画模式,将眼前所见“框定”“修正”“保存”为一幅画?如果人走进了风景中,还会做出某种造型来模仿某个场景,比如迎风张开双臂,或策马缓行……将我们自己的姿态与既存的画面重叠起来,这种潜意识的美学认同,当然首先风景必须具有如画性(picturesque)和可看性,决定了我们的风景感知和审美取向。在这一点上,中外皆同———“风景即我们所见之地貌(topographies)和我们游历之地带(terrains)”。
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我看,故景在”。中西词典里都有特别丰富的表达“观看”的词语,比如“审视”“俯瞰”“眺望”等。这些关于观看的动词建立了人与世界的“视觉关系”,决定着风景的美学特征:被“仰望”的风景,往往崇高甚至恐怖,如危崖悬瀑;从某个制高点俯瞰的缓坡田畴,具有牧歌情调……文学作品和游记写作里有大量的风景叙事,不同的观看方式改变着目击景象,激发不同的审美情感。
上书房: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观看风景的工具也在变化,它是不是像观看的方式一样,也会影响人类观看的感受?
张箭飞:是的,自16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改进观看的技术,从透镜成像到遥感卫星摄影,尤其是遥感技术,更是刷新了我们感知风景的方式。遥感影像能够随意“缩放、定位和操控跨越全世界地形”,使观看者获得近乎上帝一样的视角和视域。在唐诗宋词中,古人欣赏的山大都是一座山峰、一道山岭,或者是若干山峰的组合。山系概念的提出是近现代的事。因为过去山系的概念还无法进入人们欣赏的范围,一是概念没有建构起来,二是缺乏技术手段。而今天的我们,可以用虚拟现实的技术去构建一个在虚拟空间中的大尺度景观,比如山系。经过遥感技术“扩瞳”之后,我们的视域可以“覆盖”整个地球,“察觉”到全球范围内细腻的景色变化。还有很多延时摄影大片,正体现了技术手段与风景感知的高关联度。

风景入画
上书房:“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人与景是怎样的“看见”关系?
张箭飞:在风景研究话语体系里,景中人(insider)和景外人(outsider)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一种观点认为,风景中的人感知不到自己正置身于景外人凝视的风光之中。这涉及景中人和景外人的风景感知问题,不同派别的人文地理学家表述不一:风景是我们正在观看的景象(scene),抑或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world)?风景是环绕我们四周,抑或是呈现我们眼前?我们是观察风景还是栖居于风景?……而我想补充说明的是,风景的视觉要素固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唯一。随着风景研究的进展,风景的味觉、听觉、嗅觉等也渐成学者关注的现象。风景本身具有的多重属性,如可视性、可听性、可嗅性等,决定了风景研究必定和必须是跨学科的。
「合围“风景”这一议题」

万亩花田正在成为乡村旅游的某种标配
上书房:从历史、文化或艺术的角度看风景,是否就更复杂了?
张箭飞:是的,这正是风景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研究的第二重意思。我们必须调动文学、心理学、社会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资源来合围“风景”这一个议题,如“地方感”“恋地”“空间记忆”,等等。英国文化地理学教授戴维·马特莱斯曾说:“景观已经成为多门学科试图加以理解的主题……而景观研究有助于超越过去所界定的学科主题。”诸如风景文学、植物美学、文化旅游等当下备受关注的研究任务,每个单项都需要跨学科协力合作。
说到这里,我可以回头来聊聊什么是风景研究了。这些年来,我在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中主持风景研究经典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我结合这套丛书中的几本书来澄清风景研究的疆域。
一本是美国人类学博士温迪·J·达比所著的《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这本书被视为风景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作品,作者考察了自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内,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书中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书中论及的峰区或湖区的难题,其实也在困扰着当代中国。
还有一本是《风景与记忆》。这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了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身为英国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的作者西蒙·沙玛,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再说一本《风景与权力》。这本书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的出版曾改变了风景研究的方向。书中收录了米切尔、萨义德、陶希格等多位学者的文章,包含艺术、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历史与现实等许多层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精华成果。这些文章重点考察风景流通的方式:风景如何成为交换媒介、视觉占有的地点、身份形成的焦点等。每篇文章视角独到又相互关联,并彼此深化,反映出人类风景体验的复杂内涵。
由上可见,风景研究研究的不仅是我们可见的,更有我们不可见的,那就是隐藏于风景之中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历史。多重视角的研究可以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使隐藏在关于风景及风景意象的知识和体验之后的社会性基础显现出来,这种社会性基础就是历史上各种排斥与包容的观点。风景提供了一个切入这些问题的途径,触发诸多思考。
「阅读“风景”,正如阅读书本」

认识脚下的土地
上书房:您是如何从英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向风景文学研究的?
张箭飞:2004年,我和北大钱理群先生有过一次电话长谈。钱先生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他的“认识脚下的土地”的构想和一些研究细节,并希望我能发挥外语特长,引介一些理论文献。为先生的热情所感染,我满口答应,不曾料想正是这次谈话,把我这个偏安文学批评一隅的文体研究者,引至了一个更大的学术领域。
国际学术界对“认识脚下的土地”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风景学(landscape studies)、地方研究(place studies)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三方面。它们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乃至研究方法都源自人文地理学,又融入派系纷繁的文化研究之中,因而具有一切新兴学科的跨越性和模糊性。换言之,它们的疆界随着新的关注、方法或问题的介入而在不断移动。
探索的过程中,我的兴趣逐渐锁定在与人文地理学瓜葛甚深、近乎同构的风景学上,试图以此为基点展开纵深搜索。之所以如此锁定,是因为在把“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个比较感性的表达切换到理论层面时,我注意到美国学者皮尔斯·刘易斯在其《阅读风景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所有的人类风景,不管如何平常的风景,都有着文化意涵,因此,沃茨认为我们‘可以阅读风景,正如我们能够阅读书本’。我们人类的风景是我们无意为之,却可触知、可看见的自传,反映出我们的趣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渴望乃至我们的恐惧。”
我的一个假设是:既然由风景(landscape)一词汇聚和裂变出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如土地、地方、区域、空间、记忆、权力、栖居、家园、身份、国族等,已经成为当代各种社会理论的建构基础或参照框架,它也应该能够成为一个理论棱镜,透过它可以观察同一个对象在作为一个地方、一处风景、一种表述对象时的不同含义。
风景研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意义,那就是当下十分应该研究明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互动关系,这对今天很多急于要把自己打造成旅游大省的各地政府是件十分紧迫的事,不搞明白这层关系,千城千村一面的现象可能无法避免。风景研究经典专著之一《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分析的就是18世纪下半期英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互动,讲如画美学(the Picturesque)如何改变人们的风景感知和审美趣味,使英国西北部凯尔特边区戏剧性地成为游客趋之若鹜的绝美之境,浪漫主义的精神圣地。“画境游”(picturesque tour)得以流行,剧院、绘画、明信片、杂志、广告等媒介的作用居功至伟,它们熏陶了,或者说是规训了游客的品位,引导他们拿眼前之景比照他们熟悉的17世纪荷兰和意大利风景画作品,从而抬升了峰区、湖区、苏格兰高地的文化价值。作者Malcolm Andrews曾应邀来武大与我合作讲授《风景与文学》,他的《风景与西方艺术》也在2014年译成中文,对国内艺术史领域的学者启发很大。贵报曾在2018年采访过他———那次他应上海博物馆之邀,为“泰特英国风景画珍藏展”做系列演讲。作为他的译者和演讲者之一,我们与北大丁宁教授一起做了几期线上课程,讨论中英风景艺术的差异,目的之一就是引导听众重新发现本土风景。一如18世纪末期,拿破仑战争切断了英国贵族视为传统的欧洲大陆壮游路线,倒逼他们开始探索本国的“穷乡僻壤”,进而滋养出浪漫主义的审美趣味。
当下,回溯英国风景美学与旅游的历史很有意义。我认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数年,一方面会严重打击国际旅游业,削弱中国游客海外壮游的消费欲望,但在另一方面,中国拥有的壮丽山河,其气象万千的风景优势可能会越来越有市场空间。市场空间将孕育出怎样的美学趣味和文化认同,正是我目前所关注的。
上书房:如何破除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城、镇、村风景雷同的困境,打造“地方诱惑”?
张箭飞:一个地方的“地方诱惑”,或者说“风景诱惑”,应该是综合魅力,不仅指最易被我们眼睛,或者说眼睛的替代物,比如光学镜头,抓取聚合的“可视性画面”,也指需要调动嗅觉、听觉、味觉、触觉、想象等感知的现实。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魅力糅杂在一起,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和旅行者“到此一游”。无论是普通游客还是文学家、艺术家,都需要特别敏锐的感受力才能捕捉、品味、辨识一个地方的氛围。而“地方诱惑”的生成机制和媒介,往往可从“看不见”的民间音乐、诗歌、传说中找到线索。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有个说法,我经常引用:“看不见的风景决定了看得见的风景”。
中国民间文学里有多少风景传说啊,特别是那些耳熟能详、传唱弥远的民歌,很多就是恋地恋乡的风景歌谣。比如《这里是新疆》———“我要来唱一唱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最美丽的地方。连绵的雪山优美的草场,草场下面是城市和村庄……”。我相信很多内地游客就是因为《达坂城的姑娘》《新疆是个好地方》《白麦子》这类民歌而对新疆产生“如画性”想象。而我,作为一个学者,除了“听出”和“看见”歌之不足则舞之蹈之的心灵风景,更会注意到民歌与地方感(sense of place)之间的互相塑造。
参与贵州省旅游规划项目时,我特意整理了一些“黄果树瀑布的传说”材料,发现了很有趣的叙事要素,涉及地名、地貌、民族、阶级、性别、超自然力量、价值观等议题。传说之一来自汉族,叙事重点放在“黄果树”的神奇果实上,它能够召唤出藏于瀑布深潭中的金银财宝;传说之二收集于安顺布依第三土语区,讲述了一对情侣怎么用特制的网把牛头怪鱼网在深潭里;传说之三的情节最为经典,讲一对相爱的布依族情侣遭受土司迫害,在神仙的帮助下,逃进龙宫,过上了幸福生活。很多地方的地标性建筑或景点,比如武汉古琴台、桂林芦笛岩、新疆喀纳斯湖等,都有自己的传说,这些传说通常解释了名胜风物的起源,保存着当地人的风景想象和叙事,反映出他们的信仰或者环境态度,而这些正是文化旅游赖以生存、得以持续的部分。
上书房:人们常说“诗与远方”,诗是否一定在远方?

诗不必在远方
张箭飞:这句流行语很容易导致一个理解上的误区。近20多年来,国内游倾向于越远越好的壮游路线。在这种审美趣味的推动下,西藏、云南、新疆成为目的地,出境游也是越远越奇特越好。这一现象也非今天的中国独有。历史上的英国,早于我们几百年就经历过这种“诗与远方”的壮游阶段。
壮游(ground tour)最初是精英阶级的地理探险和风景发现之旅,之后成为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一种文化模仿,最终必然地转向了日常风景的发现和大众旅游。今天许多乡村旅游的“卖点”就是普通农民的生活场景和建筑。人们固然神往大自然神力和伟大人力创造的那些“宏大景观”,但也会从平常朴实的乡村生活细节中获得怀旧情绪的满足,这是近年乡村旅游大热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节日庆典到庭院美学,文化交融也是塑造日常风景的一种力量,并且在大地上留下印记,这些印记聚合成珍贵的风景资源,有些可见,有些不可见。作为风景研究者,不管是从美学批评出发,还是从民间文学角度进入,都能发掘并诠释一个地方的“地方诱惑”。
萧驰先生的新著《诗和它的山河》,就是这一研究路数的范例。萧著从中国山水诗歌的审美历史出发,回应和修正了西方风景学念兹在兹的问题意识:何谓风景?我再回答一次———风景就是张力,是远与近,内与外,看得见和看不见之间的张力。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顾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