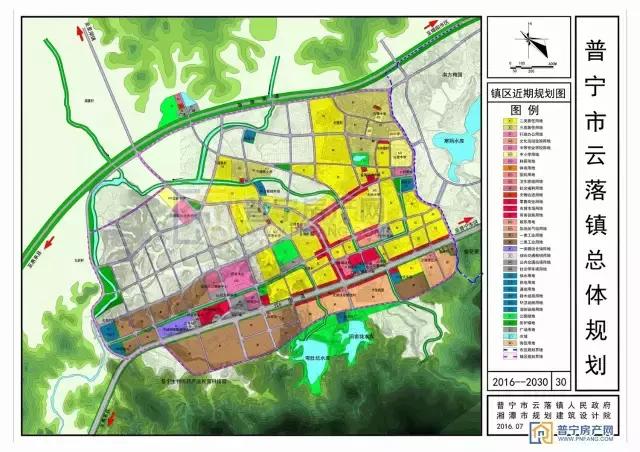记得少年时背诵课文《陈涉世》:"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朗朗上口当背诵到"掇耕之陇上”时卡壳了,我背诵着"怅然曰:苟富贵,无相忘”感觉语气总是不大自然,不符合陈胜这个草莽英雄的本色,我又背诵为“长太息曰:苟富贵,无相忘”更不对了,这又显然是一个落魄的文弱书生的口气想到最后我实在想不起来,翻开书看到:“怅恨久之”四个字读课文时不甚觉得,经我错误的背诵后,高下立见,只“怅恨久之”四字,眼前的陈胜这个草莽英雄,瞬间有血有肉了 后来看了《报任安书》,我才明白,非如此人写不出如此书,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读史记的感想及启示?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读史记的感想及启示
记得少年时背诵课文《陈涉世》:"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朗朗上口。当背诵到"掇耕之陇上”时。卡壳了,我背诵着"怅然曰:苟富贵,无相忘”感觉语气总是不大自然,不符合陈胜这个草莽英雄的本色,我又背诵为“长太息曰:苟富贵,无相忘”更不对了,这又显然是一个落魄的文弱书生的口气。想到最后我实在想不起来,翻开书看到:“怅恨久之”四个字。读课文时不甚觉得,经我错误的背诵后,高下立见,只“怅恨久之”四字,眼前的陈胜这个草莽英雄,瞬间有血有肉了 。后来看了《报任安书》,我才明白,非如此人写不出如此书。
作者遭遇宫刑,沦为鄙视链的最低端。这样一个“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司马迁,他所写出的《史记》,他所写的每一个沦为下贱而又心有不甘的普通人,怎能不神形俱现呢。读《史记》前要先把《报任安书》细读十遍以上,而且要无数次地反复读。
回到课文《陈涉世家》,一句“怅恨久之。”隐含了主人公的遭际,也向我们揭示了主人公后来的动向~揭竿而起。由此,点燃了推反秦王朝暴政的第一把火。
他在《报任安书》书中说“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样的文采,如果不为我等后人所见,怎能不是一件恨事呢。我随便摘出一段来,《留侯世家》有这样一个情节: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後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诵习之。
怪不得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老父的怪异,张良的惊异,读来真令人捧腹,而张良对老父的举止前后用了“良愕然”“良殊大惊”而“父以足受,笑而去” 等等,通篇细细玩味,真的令人一咏而三击节也。而这样一段具有小说家笔墨的描写,我们仔细揣摩,竟然没有一句闲文。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一点椎秦博浪沙的豪气与锐气,只看到一个谦躬的少年人的韧性与忍耐,这样的一个张良,在后来能够辅佐刘邦开出一派大汉盛世,而又能功成之后在充满殘酷的斗争中全身而退,不是没有理由的。
《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要交叉阅读方可体悟到作者的苦心,也可见出作者的良史之笔。在作者笔下,刘邦虽有无赖相,项羽虽为残忍人,但笔墨之间对二人都是作为不世出的大英雄来描写的,我们有时竟会看出二人很多的相似之处,如与秦皇帝的偶遇。刘邦: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项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在项羽穷途末路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在刘邦功成名就时又是这样描写的: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一个是末路穷途英雄泪,一个是功业已就前路茫茫的英雄泪。而这两首即兴吟唱又压倒古今多少无病呻吟之作。有这样两个人生于秦末乱世之中,真算得上始皇赢政的对头了。
再看看二人对死的态度。刘邦: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项羽:
於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面对死亡,在还有一线生机时,刘项二人则决绝地选择了赴死,非大英雄不会有此决断。我们看惯了一些在死亡面前哭天抢地紧紧地抓住不放,或者磨尽最后的一丝活力。在这种“生又何欢,死又何忧。”的态度面前是不是感到震惊。而且又不可思议,连杜牧都替项羽惋惜了,发出:“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慨叹。
面对权势,大众都选择逆来顺受,或者膜拜,刘,项二人选择取代他。面对死亡,大众选择软磨硬泡到最后一刻,刘,项二人选择毅然接受。这正是庸人与英雄的区别。超出俗人的举动,超出俗人的思维。这也是司马迁出众之处。他的《报任安书》是写给任安即将面临处决的前一刻。金圣叹在评语中写道“看他一片心事,更无明处,而欲明向将死之友。”他又在书信书反复对任安慨叹自己的身世: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一个趣舍异路,素无交情的人,只是因了他对这个人的一厢情愿的好感,便在满朝冠带都作失语状态的情况下,冒死替他发言,从而导致自己遭遇了比死亡都可怕的宫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傻得冒了顶了。鲁迅先生说过一段话: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司马迁正是这少有之中的一个。他对他的将死之友任安说“此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圣叹插言道:“骂尽天下俗人”
读《史记》,我们要做一个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