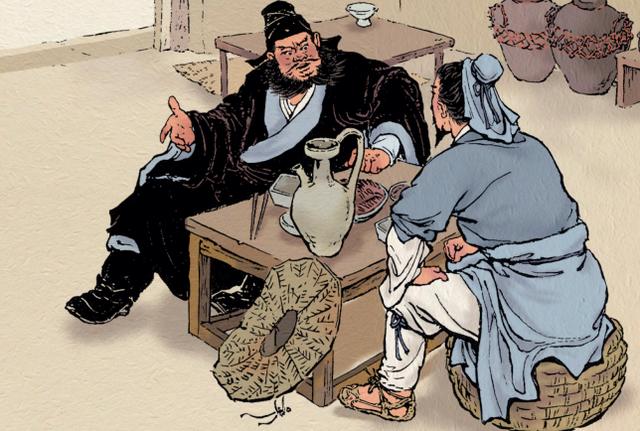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引言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市民通俗化的审美需求为戏剧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戏曲中频繁出现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戏剧作品数量大幅度增加,戏剧理论水平也大大提升,促进了戏剧文学的全面发展。
一、文学渐趋世俗化,“本色论”应运而生明中叶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和思想价值观的变化,并逐渐体现在文化作品上,呈现出明显的商品化趋势。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的冲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人们的社会生活也逐渐突破了物质消费方面的限制,逐渐转向世俗化,典雅的诗歌文化也逐渐被庸俗的散曲所冲击,士大夫文学逐渐被市民文学所取代。通俗的小说、戏曲蓬勃发展起来,而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唐诗、宋词逐渐趋于没落。

李贽曾言:“无时不文, 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皆古今文字,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到了通俗的市民文化背后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文化市场。市民文化的蓬勃发展代表了雅俗文化的转化,小说、戏剧等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阶层思想的解放,一扫传统理学压迫下的社会阴霾,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推动了社会进步。
生活在思想解放时期的徐渭,敏锐地察觉到了文化发展遇到了一个开拓创新的机遇,政治环境的变化为其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也看到了产生于民间的戏曲本身所带有的强大活力,意识到民间文化才是戏曲文化发展的根基,从而确立戏剧语言文学的“本色论”,这也成为其戏曲理论思想的理论基础。
二、心学家格物致知,“本色论”破旧立新继程朱理学的不断没落之后,阳明心学逐渐显露头角,成为当时社会发展催生的必然产物,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阳明心学在王守仁时期逐渐完备,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迎合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各领域掀起理论革新的高潮,超越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成为具有主导性的统治思想。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更加肯定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存在的意义。其主张“致良知”,更加关注人的内心,强调一切道德伦理都源于内心的外化,而不是一味依赖外在的规范约束,打破了强加在人身上的社会礼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
王阳明打破传统,对理学进行了重新的解读和定义,强调道德自由,其勇于反抗传统的精神,激励人们突破思想的禁锢,给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指引了方向,为其提供了思想创作的环境。

明中叶以后,王学成为最为重要的学术流派,加快了明代末期思想解放的步伐,推动启蒙思潮的发展。心学对徐渭“本色论”戏剧美学思想的影响体现出很强的启发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王阳明对“本色"一词的吸纳和改造: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据《明史·儒林外史》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矮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离合“相禅而无穷”。以“中庸”为道的准则,重视“观”对,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

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体现在“心即理”“致良知” 和“知行合一”三个方面,肯定了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从心学的角度来说,王阳明为其代表人物,提出心学的主旨在于“致良知”,也是从王阳明开始,心学的学术脉络逐渐清晰而独立,奠定了心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从“本色”的角度来说,其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阳明心学,与王阳明个人的吸纳和改造有着直接关系。
正德年间王阳明在一次讲学过程中曾言:“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亳实?佛氏说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亳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
可见“本色”的内在含义由此开始从事物外在的客观颜色,转为心之内在主体,是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等思想的转化,蕴含着心学内在的哲学思想。因此王阳明为“本色”一词赋予了哲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本色论”的形成和发展。

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畿也从心学的另一个角度阐释“本色”并延伸“本色”之意,他在讲学的过程中也曾经提及过老师对于“本色”的言论,曾经写道:“良知原是不学不虑, 原是平常,原是无声臭,原是不为不欲,才涉安排放散等病,皆非本色,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之外无学矣。”
他主要从“良知”的角度解释“本色”,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所谓本色文字,尽去陈言,不落些子格数,万选青钱,上等举业也。”由此可知王能认为文学在创作时要运用朴素的文字,保持创作之初的质朴本色,去除华而不实的绮语,由于当时王畿在文学创作领域有一定的地位,因此其主张也影响到了一部分戏剧文学创作者,尤其是影响到了文学批评领域。

王畿创造性地将“本色”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和创作领域,影响了徐渭“本色论”对于戏剧创作中语言本色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徐渭认为戏剧语言应保持质朴,少用华而不实的骈语,多用本色语,继而体现出徐渭创造性地将王畿的文学创作理论应用于戏剧文学创作领域。
除王畿的批判继承以外,王时槐对于“本色论”也颇有研究。王时槐是王阳明再传弟子刘文敏的学生,主要研究修养。他曾言“后儒误以情识为心体,于情识上安排布置,欲求其安定纯净而竞不能也。假使能之,亦不过守一意见,执一光景,强作主张,以为有所得矣,而终非此心本色,到底不能廓彻疑情,而朗然大醒也。”他从心之本体的角度应用了“本色”这一概念, 认为心的本色是至善,而不是情识。

王时槐对“本色论”提出的影响在于心之本体的角度,使得戏剧创作更加关注内心情感的抒发,认为戏剧创作应该张扬真我,做到以真情动人。
可见,明代心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并丰富了“本色”一词的含义,将其从一个解释客观事物本身色彩的名词,转化为解释心学中“良知”等概念的代名词,并逐渐推动其进入文学批评和文戏剧学创作领域。

而在“本色论”主张中可以体现出其吸收了心学的有关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戏剧理论,例如其认为本色应该张扬真我,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本色”代表一种特立独行、狂放不羁的个性:“本色”从戏剧审美的角度解释了戏剧创作中的雅与俗;“本色”代表戏剧创作要体现“真情”等等。这都体现出心学对徐渭“本色论”提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其戏剧美学思想构建的主要哲学内涵。为明代中后期和以后的戏剧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促进了戏剧理论研究的发展。
三、“本色论”蓬勃发展,丰富化戏剧理论晚明时期戏剧文学理论发展相对自觉和成熟,特别是剧论者们对于“本色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嘉靖末年徐渭对于“本色论”的研究开始,他的理论起点较高且具有哲学意味,再到沈璨继承并发展徐渭语言“本色”这一角度提出的通俗“本色论”,再到王骥德以模情为基础提出的雅俗共赏“本色论”,吕天成、徐复祚等人也相继提出了不同角度的戏曲理论。“本色论”自此渐趋美学层面,具有了相对完整的戏曲理论体系。

在“本色论”戏剧理论影响之下,明朝后期形成了以王骥德、吕天成、孟称舜等作家为首的“越中派”戏剧作家群。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戏曲作品,而且提出了很多经典的戏曲理论,为戏曲理论的构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例如王骥德所创作的《曲律》中提及:“于文辞一家得一人,曰宣城梅禹金。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余则修绮而非垛则陈,尚质而非腐则俚矣。若未见者,则未敢限其工拙也。”
王骥德在《曲律》中对于“本色论”的主张可以归纳为“自然忌生造”五个字,在戏剧语言方面批判《香囊记》,主张戏剧文词的通俗性,以便符合戏曲舞台的艺术规律,继承了徐渭有关于戏剧语言“本色论”的相关戏剧美学理论,虽然《曲律》在如今看来仍有局限性,但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吕天成的《曲品》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其不仅收录了很多传奇名家的作品,而且就戏剧创作的语言、题材、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尤其提出“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第一次区分了“本色” 与“当行”的理论内涵。对于“本色”的内涵,他认为“本色”不是对于生活中口语的随意摹仿,而是对于日常语言的提炼和加工,才能够使得戏剧语言更富有生活情趣。
四、传播“本色”思想,戏剧由雅到俗“本色论”戏剧美学思想对戏剧外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使“案头之曲”向“场上之曲”转化,提高了戏曲剧本舞台化的可能性,另外他还主张戏曲剧本创作重视观众,以观众的喜好和接受能力作为创作重点。
该理论不仅涉及到戏剧的美学风貌以及戏剧的语言风格,还涉及到戏剧的舞台表现。戏剧分为两种,一种是“案头之曲”,一种是“场上:之曲”。“案头之曲”就是指戏曲搬演之前的案头创作,而“场上之曲”则是指一种以剧本为基础的,包括曲白歌舞为一体,能够登上舞台进行表演的综合表演艺术。因而场上之曲的语言是否“本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更是为了表达戏剧内容,直接关乎到呈现戏剧表演的舞台效果。

如俄罗斯文学家所提倡的艺术审美关系:“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
而这一审美关系也应以“本色论”为前身。“本色语”并不单纯指俗语、口语化的戏曲语言,而是指适宜舞台搬演的戏曲语言,也就是说剧本语言应与剧本题材紧密相连。剧中的人物随着剧情的发展,从心中流露出最真挚的语言,因此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更加有利于情节发展,更加生活化。
因此在“本色论”的影响下,戏剧文学语言悄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历了一个“由雅到俗”的阶段,不仅适合舞台演出,而且有利于戏剧演员真情的流露,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戏剧作品的传播,加强了戏曲的流动性。也因此催生了一批优秀的、符合舞台搬演的戏剧作品,例如流传至今的《牡丹享》《西厢记》 等,都脱离了“案头之曲”的束缚,真正成为了长存于舞台之上的“场上之曲”。

不仅是戏剧语言要符合舞台搬演,戏剧情节对于舞台演出来说也尤为重要。戏剧舞台是一个时空兼备的特殊舞台,因此情节对于戏剧内容的呈现来说十分关键。所谓“本色"的戏剧情节,指的就是能够引起剧中人物命运转变的关键,也是能够引起观众情绪变化的关键,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的心,使之或悲或喜、或悲愤或平静。这就要求情节设置要符合整剧的表演要求,而且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更要拿捏好情节变化的分寸。
“本色论”主张真情,而真情的流露需要“本色”情节的支撑,才能够使得演员表演自然,内容打动人心,因此在此后的作品中,例如《琵琶记》等,都十分注重情节的安排,深入的刻画了赵五娘的内心世界,催的观众频频落泪,这都体现出“本色”的情节使得一部戏的情感更加真挚。
结语“本色论”戏剧美学思想是我国戏剧理论研究史上的点睛之笔,其构建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戏剧理论的发展趋势。而“本色论”戏剧美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基础,还在当时启发了新的文艺思潮,更是促进了戏曲的传承与繁荣。
参考文献《曲律》
《徐渭集》
《王阳明全集》
《中国戏曲史》
《明史·儒林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