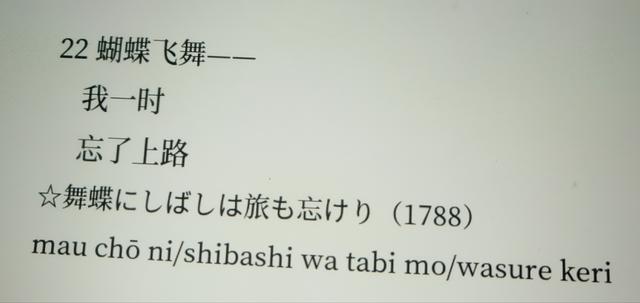文 \ 萨冈
“海风”——不是风,是火车——穿过乡野。坐在火车上,靠着机舱舷窗一样密闭的车窗,三十五岁的贾洛德女士又一次对自己说,要是能住在塞纳河沿岸这些或朴素或奢华的小屋里,那有多好。这么想不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她都过着辗转漂泊的生活;而所有漂泊的人生都梦想着平静、童年、杜鹃花,正如所有平静的人生都幻想伏特加、乐队和醉生梦死。
贾洛德女士长年在感情生活和花边新闻上“风生水起”。这天,欣赏着塞纳河的慵懒风姿,她戏谑地准备着在见到她的情人、里昂拍卖师夏尔·杜修时要说的话:“亲爱的夏尔,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美妙而独特的情感经历。但是,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彼此并不般配……”这时,夏尔,亲爱的夏尔就会红着脸,语无伦次;而她,会在皇家大饭店的吧台边,高傲地伸出一只手——让他只能躬身亲吻它——然后转身消失,留下眼波、残香、柔板和回忆……可怜的夏尔,亲爱的夏尔,留着小胡子的老实人夏尔……他是个漂亮的男人,而且,还很有男人味。可是,怎么说呢,一个里昂拍卖师!他自己应该也清楚,他们之间不会长久。她,雷蒂娅·贾洛德,出生在英国西约克,先后嫁过演员、大官、农场主和董事长,她没理由最后跟一个拍卖师度过余生!……她立刻摇了摇头,又马上收住了。她受不了这种下意识的小动作,那些孤单的女人——还有那些孤单的男人们——在生活中,在大街上,在任何地方,暗自强化内心决定的时候,就会做这些小动作。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小动作,比如撇嘴、皱眉、握拳头,这些小动作属于那些寂寞的人,无论他们的心理状况或者社会地位如何。她拿出粉盒,往脸上补粉,再一次挡住了那个年轻男人的目光。他跟她之间隔着两张桌子,火车从巴黎的里昂车站开动后,他的目光就一直在使她确信,她始终是那个美丽、温柔、可望而不可即的雷蒂娅·贾洛德。她最近刚与罗尔·贾洛德离婚,但仍与此人往来热络。
想想也的确有趣,所有深爱过她的男人,全都以拥有她为荣耀,并且都爱吃醋,但也从不怨恨她最后抛弃了他们;后来都还是好朋友。她以此为傲,但或许,在内心深处,这些男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因为再也不用与她分担这种漫无止境的不确定性了……就如亚瑟·欧康纳利,她最富有的一个情人所说的,“谁都没法离开雷蒂娅,除非她主动离开你!”这男人,很富有,但也很诗意。说起她,他说:“雷蒂娅,她是永远的木樨草、温柔与童年。”这三个词总是刺伤在她之后进入亚瑟生活中的其他女人。
菜单上花样繁多。她单手漫不经心地翻阅着,忽然看到一种吓人的食物,竟然在同一份汤羹里,混杂了疑似芥末酱芹菜、老龙利鱼和改良版烤肉之类的东西,然后是苹果苏芙喱、切片奶酪和香草圆球冰激凌。真奇怪,火车的菜单上似乎全都是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搭配。想到哪天也许还会看到去头龙利鱼或诸如此类滑稽的东西,她突然笑了起来,然后向正对面那位老太太投去询问的一瞥。她明显是当地人,一个里昂女人,面色温和,一点点拘谨,非常老实。雷蒂娅把菜单递给她,那太太立刻摇摇头,微笑着把菜单推还给她,她那万分客气的样子让雷蒂娅意识到,尽管过了这么许多年,她看上去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女人。“您先来,”那位太太说,“您先来……”“不不,我……一起看吧。”雷蒂娅怯生生地回应道(她听出自己有口音,在这种状况下,更加重了……)。“啊不。您觉得白葡萄怎么样?”“是好。”她脱口而出。太迟了。那位妇人的嘴角已经挂上了体谅的笑容,体谅她的语法错误,而她,没有勇气去改正说出口的话。她酝酿着打趣的辞令,但很快又对自己说,竟然为这么小的事情紧张,真是愚不可及,还不如好好想想三个小时后要对夏尔发表什么样的演说。语法在情话当中根本无足轻重。只不过,根据她这么长时间以来使用法语的经验,词语的位置会完全改变句子的意思。由此,对一个男人说“我很喜欢您”还是“我喜欢您很久了”,与对他说“我永远爱您”还是“我永远只爱您”,句子与句子之间,有着千回百转的迷宫,对她而言,这是最难解决的,无论从情感的角度,还是从语法的角度。
火车以疯狂的速度飞驰。她想,也许应该在煎牛排、去头龙利鱼和半球冰激凌端上来之前,先去补补妆,洗洗手,梳梳头,然后再慢慢用一个小时进餐,迎接即将到来的人生。她冲那个里昂女人微微一笑,然后,迈着她倾倒众生的步子——中肯地说,在这趟火车上,是颠三倒四的步子——朝着自动玻璃门走去。门刷地分开了,她几乎是失去控制地扑进左边的盥洗室。她连忙插上门栓。这样很好,前进、速度、安静,太好了!但实在需要有钢铁般的手臂,野蛮人的动作,和杂耍演员的视野,才得以穿过一节行驶在巴黎和里昂之间的小小车厢,一九七五年的车厢。她突然羡慕起那些宇航员,似乎四平八稳地就抵达月球了,直接出舱,完全不用考虑梳洗更衣。返回地球时,也是一眨眼就在水里了,一眨眼,就受到欢快的水手们热情洋溢的欢迎。而她,火车到站的时候,等待她的,不是热情欢快的水手,而是一个醋意浓浓、闷闷不乐的拍卖师。但他完全有理由给她那样一张脸。因为,不管怎么说,她这样匆促而唐突地跑这么一趟,就只是为了跟他分手。
然而,这个涂着夸张的土黄色、充满消毒水味道的地方还不如车厢。至少,车厢里的棱纹布和金属包边,所有现代却过时了的装潢,毕竟还是在追求美感。洗脸池是圆形的,她一手握住水龙头,一手试着打开将倾的手袋。车快到第戎了,一阵阵的刹车,让她那摇摇晃晃的手袋在左右为难中敞开着口,一头栽倒在地上。她只好俯下身,蹲在地上收拾起来——还把脑袋撞到了洗脸池和其他什么东西的边缘上——她一会儿从这儿找到她的口红,一会又从那儿捡起她的支票簿,这儿是粉底盒,那儿是钞票;当她重新站起身来,额头都泛出了油光,火车才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第戎。她总算有那么两三分钟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涂她的睫毛膏,不用让自己再像马塞尔·马索表演默剧似的手舞足蹈了。
当然,这是唯一没从手袋里蹦出来的小盒子,她焦躁地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出来。她从左眼皮开始涂。她的左眼比右眼受宠。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所有的情人,所有的丈夫,都喜欢她的左眼胜过右眼,并且都这样告诉过她。“它显得,”他们说,“比右眼温柔许多。”而她总是乖巧地、安静地承认,她也这么认为。很有趣,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总是那些冷落她的男人,说她的乳房握在掌中有如维纳斯,也就是,说她性感难挡;总是那些令她百无聊赖的男人,称她活泼开朗;更悲哀的是,总是那些她真正爱上的男人,认为她只爱她自己。
火车重新启动,发出尖利的摩擦声。她一个踉跄,失手在脸颊由上往下划出了一道黑色的睫毛膏痕。她用英语在心里骂了句脏话,立刻又后悔了。毕竟,她将去见面并且要离开的,是一个法国情人。那么多年来漂泊在世界各地,贾洛德小姐已经习惯了用她情人们的语言来思考、感受甚至忍受。于是她当即更正过来,大声地,把同样的粗话用纯正的法语骂了一遍,然后收起她的睫毛膏,塞进手袋里,决定让那个里昂女人忍受她这个只化了一边眼妆的女人坐在面前。她随便梳了梳头,准备出去。
但她没能如愿。门一动不动。她不可置信地笑笑,使劲拉了拉门闩,再推一推门,终于相信,是有什么东西坏了。她哑然失笑。法国最时新最快速的火车,竟然在开门系统上出现瑕疵。重复试了六七遍之后,她目瞪口呆地意识到:风景仍旧在左边的小窗外连绵,她的手袋关得好好的,而准备要去吃那顿见鬼的套餐的她,被这扇门拦在了这一头,尽管那一头对她也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她再次摇晃门,又是推,又是拍,胸中一股怒火上涌,像火山爆发。她觉得自己仿佛一个正在耍脾气的幽闭恐惧症患者,但她可没有幽闭恐惧症。感谢上帝,这辈子她从没扯上这些时髦的怪癖:幽闭恐惧症、女性求偶狂、谎话癖、嗑药癖、中庸癖。至少她没这些毛病。但是此时此刻,突然地,她发现,她,雷蒂娅·贾洛德,在晴朗的九月早晨被司机送到巴黎的里昂车站,在里昂亦有个忠心耿耿的情人在苦苦等待,这样的她,竟然在火车上撞断了自己的指甲,怒气冲天地捶打着一扇跟自己过不去的硬塑料门。火车越开越快,她的身体晃动得厉害,最初的暴怒过去了,她只有听天由命,也就是,等待。她尴尬地合上马桶盖,坐在上面,并拢双膝,突然变得像个羞涩的少女,第一次坐在挤满男人的沙发上。滑稽的感觉。她看到镜中的自己,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手袋像宝贝一样合拢在膝盖上,头发蓬乱,只有一只眼睛化了妆。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仿佛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跳动,既不曾为了这个可怜的、正在等着她的夏尔,也不曾为了那个可怜的洛朗斯——夏尔前面的那个——感谢老天,他不再等待她了。肯定会有人过来,从外面把门打开。可倒霉的是,此时所有的人都在用午餐,而法国人是从来不在吃饭的时间离席的,天塌下来也不会;他们一刻也放不下眼前的盘中餐、杯中物,和来来去去的侍者。没有一个人敢在这样不可取代的仪式当中擅自离岗,这是他们的每日必修课。她自娱自乐地踩了两次冲水闸,然后还是决定继续傻傻地,但是挺直腰板地坐在马桶盖上,并且试图继续把她的左眼和右眼化得一致。火车无与伦比的速度,让她足足花了十分钟才把眼妆补好。这时候,她觉得渴了,而且真是饿了。她再次用一只手试着推了推门,还是徒劳无功。好吧,不应该发脾气,应该耐心等候附近的人,左边车厢或者右边车厢的乘客,或者检票员,或者服务生,或者哪个终于想要来用这个地方的人,那样她就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到那个里昂妇人的面前,然后在心中默默准备给夏尔的演说稿。不过,既然现在她在这里,面对着一面镜子,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练习呢?于是,她对着SNCF列车上这面其貌不扬的镜子,盯住镜子里自己棕色的大眼睛和美丽的棕发,展开演说:
“夏尔,我亲爱的夏尔,我今天对您说出这番残酷的话,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太漂泊不定的人。我这样的人,让自己痛苦,也让其他人,包括您,为此痛苦。而我对您的感情,让我不愿意去想象,夏尔,倘若我接受了您温柔无比的请求,嫁给了您,那么,我和您,将很快陷入可怕的争吵与难堪的境地。”
左边的车窗外,是金色的麦浪,沿着黄绿相间的山丘,一路铺展。她感到自己的情绪随着演说在不断增强:
“是这样,夏尔,您的生活所及,是巴黎、里昂和我;而我,是巴黎和世界。您的中转站,是尚贝里;而我的,是纽约。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我已历经沧桑。也许,夏尔,”她说道,“您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女孩,而我已不是。”
真的,夏尔是应该找一个年轻的姑娘来与他相配,像他一样温柔、忠贞,像他一样天真、淳朴。而她,真的配不上他。她的眼眶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她仓皇地擦去眼泪,霎时间,又一次看到自己坐在可笑的“板凳”上,糊了眼妆,张着嘴,孑然一身的样子。犹豫了一秒钟时间,她又开始笑了起来,然后自顾自地,又是哭,又是笑,没法停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紧紧地抓住专供行动不便的旅客使用的把手。她想到伊丽莎白二世,想到议会,想到维多利亚女王,或者任何同类型的人,坐在扶手椅上口若悬河,而面对的,却是无声无息、令人沮丧的听众。突然,她发现门把手自己提起来,又落下,再提起,再落下。她满怀希望地僵立在原地,手中的包仿佛随时要掉在地上。可之后,门把不再活动了,她这才震惊地意识到,刚刚是有人过来了,并且恰恰是以为,这地方正被别人使用,所以就默默离开了。她现在必须抓住时机。她叫出声来。为什么不求救呢?她可不想在这个逼仄的地方待上两个小时直到里昂。肯定是有办法的,总会有人经过这里,听到她的叫声。不管怎么说,即使让人笑话,也比待在这个无聊得让她快要发疯的地方好。于是,她大声喊起来,她先是叫“Help!”声音嘶哑。然后,她才猛地想起自己是在法国,于是她大叫“Au secours!Au secours!Au secours!”不知怎的,尖利的叫声让她自己都发疯似的笑了起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正坐在这个该死的“凳子”上,捂着肚子笑得岔气。看来,跟夏尔分手之后,她有必要跑到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医院去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了……不过,这的确是她的错,她本来完全没必要独自旅行。“他们”总是这样对她说:“别独自旅行。”总之,比方说,要是夏尔来接她的话——他曾在电话里恳求她的允许——那么此时,他肯定会在火车上四处找她,敲遍所有的门,而她也早就能被解救出去,品尝着龙利鱼配巴里葡萄酒,或者随便别的什么,就在夏尔那欣赏的目光之下,如此温柔,如此有安全感的,夏尔的目光。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夏尔在这儿的话……
只是,正是因为她下的命令,夏尔此刻在里昂,但他绝对已经等在里昂贝拉什车站,手捧一束鲜花。他不知道他美丽的情人此刻正像一头小兽一样,被困在涂着瓷漆的四面墙内,而且他很可能将看到,从出口向他走来的是一个头发蓬乱、精神崩溃、失魂落魄的她。这鬼地方甚至连书都没得看!她的包里连本书也没有带!这个地方唯一可以阅读的东西在说的是:注意出去的时候不要走错门,不要跳到月台上。真搞笑,这警告可真是幽默!全部读完后,她更迫切想要从这个糟糕的地方出去,哪怕直接跳到月台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关在与世隔绝的笼子里,因为滑稽可笑的意外,被粗暴地剥夺了自由。十年以来,还没有任何人胆敢侵犯她的自由。十年来,没有任何人胆敢把她关起来。尤其是,十年来,每个人都曾不假思索地试图把她从某件事或是某个人当中解脱出来。但现在,她就像一只老猫一样孤独。她狠狠地踹了一脚门,把自己撞得生疼,弄坏了她那双新买的圣罗兰薄底皮鞋,却什么也改变不了。她缩起脚,颓然坐下,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用呜咽的声音喃喃叫着:“夏尔!哦夏尔!”。
当然,夏尔这个人,也有不少缺点:他爱吹毛求疵,他的母亲实在无趣,他的朋友也很无聊;而她,她可认识不少更开朗、更英俊、更精彩的男人。但不管怎样,如果夏尔此时在这里的话,所有的火车的所有的更衣室的所有的门,都会早早就被打开,他会用他那猎犬一般的眼睛注视着她,把他那双既修长又粗粝的大手,放在她的手上,对她说:“您没有被吓坏吧?别为这件破事儿不开心,好吗?”他甚至还会责怪自己出现得不够快,也许还会声称要起诉SNCF。因为他是个疯狂的人,本质上是,尽管他看上去一丝不苟。一句话,他不能忍受一切令她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夏尔是那种为她欢喜为她愁的男人,仔细想想,这样的好男人不多了。倒不是说,她缺少爱护她的男人。爱护,这个概念太空泛,而且因人而异。但是总的来说,这世上真的缺乏懂得爱护女性的男人。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这么对她说,而实际上,也许她们说得没错。爱护女性,那是老派人的信条,但并不赖。如果此番同行的人是洛朗斯,没有看到她回来的话,应该是会认为,她已经在第戎下了车,去找另一个男人了;
如果是亚瑟,他会想……他根本就不会想什么,他会一直喝酒喝到里昂,期间可能会向侍者询问两三次;总之,惟有夏尔,系着条纹领带、面无表情的夏尔,会掀翻整列“海风”去寻找她。是的,很遗憾,很快就要跟他分手了。想到这里,真觉得疯狂。她三十六岁了,二十年来她的世界全都围绕着男人们——她的男人们——打转,他们的嗜好、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女人、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欲望。而现在,在这列火车上,以这样滑稽的方式,被一根不听话的门闩困在这里,她却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男人,会伸手拉她一把,而偏偏正是对这个男人(她是因为他才坐上这列火车,这列向他驶去的火车),她将要决绝地说出,她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她!老天啊!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在她登上这列火车的时候,她还对此是那么确凿无疑!而且,她也曾那么确凿无疑地告诉阿希礼,她的司机,在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来接她,“重获自由”的她(当然,她没把这个词说出口)。就在今早,她已经愉快地想象着她回到巴黎的样子,独自一个人,自由自在,没有谎言,没有责任;再也没有义务等待来自里昂的电话,不用为了里昂男人随时会到来的可能而拒绝一顿美妙的晚餐,不用因为这个里昂男人在身边而生硬地取消一场特别的约会……是的,那天早晨当她在家里醒来,她的心中充满了突如其来的、矛盾的狂喜。一方面,是为乘坐火车穿过美丽的法国原野而欢欣;另一方面,残酷的一面,是为了能够快刀斩乱麻。她的这次出发,正是为了去告诉一个人,她是怎样的磊落果决。磊落果决地,让他失去她。她这样一个容易欢喜的人,身上却总有那么一股残酷;然而此时此刻,这位蛇蝎美人,却被一把门闩困住,变成了一幅脏兮兮的漫画,她的脸孔,在列车浑浊的镜子里,恍如支离破碎的拼图,而让它支离破碎的,不是纵横交错的命运或往事,而是她又哭又笑时,纵横交错的泪水。
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好多匆匆而来的人,或者是女人——怎么知道的?——过来摇晃她的门。她冲她们大喊“Help!”或者“Au secours!”或者“Please!”,声嘶力竭。她想起她的童年、她的婚礼、她本可拥有的孩子、她曾经拥有的东西。她想起海滩上的零碎细节、夜色下的私语、唱片、蠢事,她甚至还不忘幽默地想,世界上没有哪间精神病室,可以比从巴黎开往里昂的列车上的头等车厢里的被锁上的厕所更有效果。
车过夏龙之后,她终于脱身出来。她甚至都没有想过对救她出来的人——那位里昂夫人——提起,她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她一如既往地,带着完美的妆容,和完美的从容,在里昂下了车。而在月台边哆嗦了快一个小时的夏尔,对她的青春洋溢惊为天人。他向她奔去,他认识她以来,这是第一次,她扑向他,把头枕在他的肩上,对他说,她累了。
“这火车还算很舒适吧。”他说。
她含含糊糊地低声应了句“是的,当然”。然后,转过头,面对着他,给了一个把他变成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的问题:
“您希望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