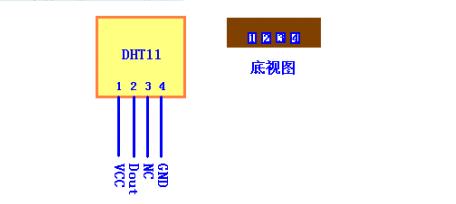作者简介

陈泽,1962年9月出生于云南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镇南山村委会贝忙村上社。1977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诗歌、散文、散文诗、文艺评论等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两百余家报章杂志。散文《名气-庙会-乡戏》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二等奖。散文《石匠大哥》获《云南日报》“我们老百姓”征文一等奖,《云南与毒品系列报道》获新华社国内专稿组“社会纪实作品”征文奖一等奖。曾获云南新闻奖一等奖;云南报业新闻奖一等奖;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协好新闻奖一等奖,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现供职于云南政协报社总编室,任新闻及文史、文化、文学副刊编辑。
烧蚕豆吃
“烧豆燃豆枝,豆在火中熟”。改一句古诗,写写我美丽如诗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小时候,在清明节前后烧蚕豆(又叫烧火焰豆)吃,是我和老家巍山贝忙村里的小伙伴儿时的一大乐趣之一。
见到田里的蚕豆成熟了,我和村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会不约而同去田里拔一些来,然后随便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将拔来的蚕豆堆在一起,拿出事先带在身上的洋火(火柴)划燃点向蚕豆堆。瞬间,蚕豆枝干间的褐黄色枯叶便燃烧起来,最终烧燃枝干,我们在旁边用木棍慢慢翻搅。不过几分钟工夫,蚕豆堆便化为一团余温依然灼人的灰烬。我们不顾被烫伤的风险,急忙将外壳烧煳的蚕豆从灰中扒出,用手或脚搓搓,就见到了烧得焦黄的一颗颗蚕豆呈现在眼前。于是,我们一边吹灰,一边将烧熟的蚕豆喂进嘴里。咀嚼时,热气和口水一起淌出来,忍不住直嚷嚷:“好吃”“香”“再去拔一些来烧吃”。说话间,只见几个小伙伴的脸上、嘴角上沾有黑乎乎的灰渍,活脱脱成为了一张张小花脸,却掩饰不住彼此纯真无邪的笑容。
有时候,烧蚕豆吃是在田里进行的。烧蚕豆时,我们将主人家割倒放在田里的蚕豆秆抓拢放在一堆,用事先准备好的火柴点燃,也是几分钟工夫,就吃到了烧熟的蚕豆。
犹记得,那个时候不怕主人来找麻烦。实际上,也没有人来找过麻烦。也因此,每次,我们几个小伙伴都是径直来到田里,尽兴随意烧蚕豆吃解馋。当然,多数时候是为了饿得咕咕乱叫的肚子。
如今回味起来,烧蚕豆时,伴随着田里袅袅升起的烟缕,我们用木棍打火,在灰里争相找食烧熟了的蚕豆模样,真的是美丽无比的画面。奇怪的是,年纪渐长,记忆反而愈发清晰。“不思量,自难忘。”或许,这种生命特定的影像,每一个人都有,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构成了我们情感的丰富内涵和色彩。成为我们需要终其一生才能回归的精神居所。
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那个特殊年代物质极度匮乏,人的梦想、心愿乃至期盼异常简单纯粹,从善如流,断不会有这样难以忘却、回味不尽的表情。并且,如此纯美至性的表情心态,大底与年龄长幼无关,与贫贱尊卑无关。
一些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专家学者曾经说过,大集体有大集体的好处和优势。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每个时代及其发展阶段,有相应的审美标准与价值认同。举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农田水利建设,大都是靠人背马驮、马车拉,靠群众投工投劳,汇集大量人力物力,以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信心和决心坚持不懈完成的。
推而广之,说当年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集体力量巨大无比,做什么事情,一声令下,万众山呼响应,所向披靡,并不为过。“敢教日月换新天,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精神意志的集中显现,是我们赖以发展和支撑的灵魂所在。
如今漫步巍山古街,不时可见店前的摊子上有用“姊妹灰火”焖炒出的蚕豆卖,吃着也很香。但相比我小时候“烧豆燃豆枝”烧出来的蚕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怀念过去,那是我魂牵梦绕的乡愁,此生已不会再有。
吃甜盏水
前几天,孙子订婚,于是借休假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巍山贝忙村。
按巍山农村风俗,订婚当天,就是认“新亲”的日子。中午时分,我随众亲朋好友从贝忙出发,前往靠近南山村的山沟箐新亲家,一路走来,不过半个小时的脚程,关键是途中欣赏品味到了清明时节田野的风光景致,感受到了浸入身心的融融春意。一直以来,我所理解的诗与远方,应该就是这样的,比如,看到了挂在树尖上的偌大鸟巢,想象鸟夫妻轮流孵化小生命的过程及养育众多儿女的艰辛与不易。看到远山拥翠,白云悠悠;近前阳光正好,蜂飞蝶舞,紫气岚烟缭绕,天时地利人和,顿时身心悦然复怡然。有诗与远方变成现实,何不诗酒趁年华,不负生命有爱,当温柔以待。
新亲家是如今巍山农村常见的独栋院落,属于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宅院。院子很宽敞,阳光很充足,空气很清新。有红花绿叶装点,有鸡犬之声相闻,屋脊上或屋檐间有鸟语如歌,相互唱和。随着男方众新亲的到来,使得原本清和井然的院子变得热闹起来。
一切都按风俗礼仪进行。比如,不可或缺的吃甜盏水环节。只见未来的新媳妇在一位熟悉双方至亲且有辈分之人(限女性)带领下,逐一给男方的一众亲友端上甜盏水。事实上,这甜盏水虽叫“盏”,其实是一次性纸杯,杯里的成分是红糖水、爆米花、枣子、桂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后面两种皆为双数,寓意将来两个新人结婚后早生贵子,好事成双,幸福美满。
令我欣慰的是,将杯子唤作盏,吃未曾改成喝,可谓雅俗并存,很有地方风情特点和韵味,与传统风俗文化一脉相承,也算记得住乡愁,用实际行动留住了乡愁。而不是喊喊口号敷衍了事。
吃甜盏水过后,未来新媳妇在之前那位长辈陪伴下依次收杯。在这个过程中,吃过甜盏水的男方一众新亲事先将数额不等的“茶钱”纷纷放在杯子里,这既是礼节也是心意,更是风俗文化的传承和彰显。有民俗专家学者曾经坦言,泱泱中华数千年发展历史表明,民族的凝聚力贯穿于正常的人情往来之中,是精神意志的依附和支撑。这,亦应该成为我们平时常说的“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末了,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在巍山农村,筹办讨媳妇、嫁姑娘或者竖柱、新居落成喜事的人家,会安排专人在客场门口摆一张桌子收礼挂账,相比城市居民办喜事时客人递红包入席,又是一道别样的风景。我想说的是,传统的、有文化内涵的礼仪程序,已根植在人们心中,得到价值认同,是一种乡村活力的载体,应当给予更多的尊重和充分认识。
洗澡汤
从我记事起,在我的故乡大理巍山农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讨媳妇或嫁姑娘)办喜事的头一天晚上,洗澡汤(谐音“喜照汤”)是一定要吃的。这是一道传统待客的方式,更是必不可少的风俗传承,一代接一代弘扬光大,是人人都尊崇向往并身体力行的仪式感,颇具民俗色彩和风情韵味。
吃洗澡汤之前,双方最亲近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依约定俗成,主动给新人送“装箱礼”,礼物包括:红糖、桂圆、大枣、葵花籽等,有的还装入一定数量的钱。
装箱礼完成之后,还要请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其前提条件是,夫妻均健在,家庭和美、子女孝顺),将新郎或新娘第二天要穿的一整套新衣裳及准备用来敬献井龙王、天地菩萨、喜神的一应供品,摆放在撑有一把红伞的圆形簸箕里面,嘴里念着“吉令”,顺着古井绕上三圈,磕头作揖,虔诚地祈求井龙王、天地菩萨、喜神保佑婚礼顺遂,清吉平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对新人必须恪守传统道德节操,才有资格举行这个神圣庄重的仪式。也唯有如此,才不至于辱没家风家教,进而受到家族和乡亲的尊重与爱戴。
紧接着,由新郎或新娘的兄弟姊妹亲自放给他们洗澡水在一个大盆里面(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洗澡间,没有淋浴,生活饮用水要靠人背肩挑或马驮),让他们洗浴身心,长辈及亲友们在旁边不停地叮咛,一定要做到夫妻互敬互爱,孝敬公婆。
这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代表两位新人在成家之前,接受亲人朋友的关心、呵护与祝福。场面十分温馨感人,充满浓浓的亲情与友情,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最后,就是进入吃洗澡汤的环节。记得当时的洗澡汤,只有手工做的碱水面条,佐料也很普通简单,有鸡蛋、杂酱、油辣子、酸腌菜、酱油、姜丝、葱花、芫荽,尽管看上去清汤寡水呢,但却十分诱人,气氛非常热闹。记忆中,为了吃上一碗洗澡汤,很多小娃娃即使眼睛再涩(俗语,困,瞌睡之意)也能和大人一起坚持等待到夜深,唯有吃上一碗洗澡汤,方才安心,踏实。
如今,生活好过了,时常有高汤熬制的扒肉饵丝、一根面吃,有各种新鲜果品享用,但再也找不回那个时候的热烈气氛、感人场景和诱人味道了。更关键的是,很少有吃洗澡汤之前的相关礼仪细节过程,以及对吃洗澡汤的渴望与无穷回味。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吃洗澡汤应该是陌生的,模糊的,没什么概念。
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洗澡汤已然渐行渐远,消失了,湮没在了历史的烟云深处。成为一代人,无数代人的追忆与怀想,时常慰藉心灵与情感。
包麦粑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包麦粑粑(乡亲俗称,即包谷粑粑),是我生命中最经典的食物之一。不仅仅因为它质地醇厚甜润,更源于饥饿和渴望。
做包麦粑粑的原料,是老辈子人传承下来的糯包谷,白得纯净,浆多似乳汁,甜糯醇厚的成分非常丰富。制作时,先用人工一包一包地将珠圆玉润的籽粒剥下来,然后拿去石磨上慢慢磨成浆,再用柴火架锅油煎,这样加工出来的美食,色泽黄而不枯,润而见光,未曾入口,已然心旌摇荡,上下揩鼻。一些人家用木甑子蒸,蒸出来的包麦粑粑鲜香诱人,清甜可口。那时,在我出生的巍山贝忙农村,村民没有美食这个概念,只要有东西吃,能果腹,就千恩万谢;遇到好吃的,便觉得非常奢侈,且十分珍惜,念念不忘。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我大妈会在她的菜园里点一些数量不多的糯包谷,到了火把节前后,就可以去掰来烧吃或煮吃,或磨成浆,煎成包谷粑粑解馋。那些年月,天如人愿,雨水充沛,5、6、7、8、9这几个月,感觉隔几天就会下雨,下得人很清爽,也很有活力。每次去菜园,看上去翠绿浅红,生机无限。在菜园中不用穿行多久,整个人湿漉漉的,却很精神,与菜园的气氛很融洽。这样的日子,从糯包谷抽出红缨帽开始,一直持续到红缨帽变黑,老老少少都处于期待和渴望之中。每每想到清甜粘牙、口舌生津的糯包谷滋味,不知流了多少口水。也让朴实普通的日子,凭添了几多情趣和亮色。
很多事情,我们之所以念念不忘,是因为已经无法重来。很多美好,因为永久失去,我们才如骨在喉,追悔莫及。很多时候,改变我们的是环境,更是变幻莫测的心。
抓周
抓周(有些地方叫抓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也是一种传统文化,至今依然在一些地方延续,部分家庭谨遵祖训,代代相传,如数家珍。再说宽泛一点,但凡上了年纪的人,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的人,深受良好家风文化熏陶的人,对此大多不会陌生。遇上机会适合,定会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将相关话题渲染得饶有情趣,回味悠长。细细想来,不言而喻,这亦是悠悠乡愁历久弥新的一部分,闪烁着先人的智慧之光。
在巍山农村,我记忆中的抓周,是专指在孩子满一岁的时候,事先给他或她准备好书本、毛笔(钢笔、铅笔、圆珠笔、水彩笔等)、纸币(硬币)、算盘、手秤(包括秤杆、秤砣、秤盘、秤钩)、煮熟的猪肉或鸡肉(有鸡头、鸡翅膀、鸡脚等)、蒸熟的米糕(年糕)、糖果、玩具等。抓周时,将这些物品呈不规则状摊开,随意放在一张干净的竹帘或一块花布上,然后让穿戴一新的孩子手握大人为他或她准备的一种带钩的物件去随意抓取。当然,在此过程中,多数家庭让孩子徒手为之,以便给他或她更多的自由和率性,最大限度释放童真天性。
俗话说,人看从小,马看蹄爪。这抓取的过程十分有趣,也是抓周的高潮部分或兴奋点所在。面对诸多新奇物品,有的孩子会迅速做出选择,如果抓到的是书本或笔,现场围观的孩子父母及一众亲人会欢呼雀跃,长舒一口气,因为,这预示他或她将来有可能喜欢读书写字,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文化人,一个有涵养、有上进心的人,是“会有出息、乃至出人头地的表现”。
如果抓到的是算盘或手秤,说明他或她将来有谋略,会算计,生活有计划,做事实在,有规律,会过日子,有勤俭持家的头脑和本事。跟喜欢读书写字一样,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祖上积下来的大德”“福泽吉瑞”“荫庇后人”;不仅是人们崇尚的美德,还是良好门第家风的弘扬和传承。也因此,在场的围观者无不相视一笑,鼓掌叫好,兴奋又欣慰。
如果抓到的是纸币,意味着他或她将来门道多,会苦钱,衣食无忧。如果抓到的是猪肉和鸡肉,则意味着他或她生性好吃,喜欢荤腥,将来有口福,有福气,命运不会差。如果抓到的是米糕、糖果,意味着他或她嘴甜心甜,品行(品性)高,会说话,讨人喜欢。如果抓到的是玩具,意味着他或她贪玩,好动,头脑灵活,兴趣爱好广泛。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抓到手的是什么东西,在场围观的孩子的父母及一众亲友表现得都很开心。抓周的过程,终究是形式而已,重在参与,谁也不会在乎和计较,目的是活跃孩子满周岁的热闹气氛,借此留下欢乐祥和温馨的生命记忆。同时,给孩子增加一些“人气”或“气场”,以期让他或她健康顺利成长,将来大吉大利,兴旺发达,给家庭乃至家族增光添彩,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归宿。
在抓周过程中,也有一些孩子睁着好奇、审视、探寻的目光,表现得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悠然自得;还有一些孩子则左顾右盼,犹豫不决,却不乏矜持自若,举手投足间,纯真天性昭然可掬。但无论何种表现,没有一个孩子会无动于衷,无所适从,最终两手空空,怅然若失。在人类的生命史上,似乎还没有孩子目空一切或傲视万物、不恋红尘的先例可考。
抓周结束后,孩子的父母及家人会将一应物品收拾好,尤其会将书本、笔墨、算盘之类有文化内涵和品位的东西放在主房或厅堂的显眼位置,供日常仰望和审视,在表达寄予和希望的同时,时常慰藉心灵和情感。如此经年累月,无形之中成为了孩子父母及家人精神意志的图腾和支撑。
北沟小河
北沟小河是我老家巍山贝忙的一条小河,因其在村子的北面,从西面群山中蜿蜒而来,形似宽大的沟渠,故名。北沟小河穿过千顷沃野,最终汇入横贯巍山坝子的大西河(阳瓜江),千百年来成为贝忙及小村村民无法磨灭的记忆与情感寄托。
自小,留给我最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村中一些人家将死亡婴儿包裹后放到北沟小河里,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这样的。听大人们说,那个时候一遇天阴,北沟小河的乌鸦就叫。长大了,从相关书本上知道,乌鸦很聪明,尤其对某些物体散发的气味特别敏感。民间还将“天阴乌鸦叫,酒醉汉子哭”连在一起,幽默风趣,颇有味道。回想起来,我并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或许是习惯了村民的做法,尽管是否有人去考证过这种做法出于何种考虑或历史因素,又始于何时。就像至今,村里的老人去世了,在出殡的头天晚上,一众孝子亲属在悲伤小号的伴奏下,要到北沟桥头“出北”一样,是约定俗成的程序仪式,不可或缺。按村民的理解,“出北”既是对逝者进入极乐世界的祭奠与祈祷,也是对其亲属后人的心灵慰藉和情感纾解。
在我17岁离开贝忙外出求学之前,北沟小河一年四季流水潺潺,古朴静美。雨季,北沟小河像其他山箐河道一样会发山洪,洪水咆哮着汹涌而来,冲走河道里的垃圾和各种污物,变得清新鲜活。河里有青鸡、石蚌、鲫鱼、花鳅等多种水生物;若是夏秋季节,在晚上还看得到很多炒豆虫在河边飞舞,白日,则不时见到落在茴香尖上或围着沙滩果树翩跹以乐的磨面虫。这也是我和小伙伴最喜欢捉了玩的两种昆虫,颜色一褐黄一墨绿,煞是好看。河畔的树上,有瓷丁丁、点水雀、麻雀、斑鸠、喜鹊、乌鸦、屎姑姑、特特嘘、黑头公公、特领哥、布谷鸟等。我们现在经常说,童年、少年时期玩场多,乐趣多,指的就是与此有关的东西,不是捞鱼就是摸虾,不是打鸟就是钓鱼,不是斗蛐蛐就是捉蚂蚱,从来不知道孤独寂寞郁郁寡欢是什么东西。大人也放心自家的娃娃去找小伙伴玩乐,即便偶尔发生不愉快,娃娃们会自行和解,大人们很少掺和其中。
数十年后的今日,曾经青春年少的我已然垂垂老矣。站在北沟小河之畔回首往昔,很多有趣的事情历历在目,以至于忍不住感慨不已,恍惚之中,竟觉万千滋味涌上心头,欲罢不能,泪光兀自盈然。眼前,一些柳树或其他树木已长得很高,树身粗如水桶,树尖上,不时可见到一两只黑色的鸟巢。小河两岸布满蔷薇、蒺藜等藤状植物,将蜿蜒的河道荫护拥簇。沿河畔缓缓而行,伴随徐徐清风及啁啾鸟鸣,使得春和景明的故乡贝忙村温婉可人的时光诗意芬芳,更具内涵韵致。放眼望去,蚕豆、油菜和其他农作物正在成熟、已经成熟的田野,呈现出一种熟悉的色彩和情趣及渴望已久的境界,对于久居城市的我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心灵慰藉,也让我圆了寻找乡愁、让灵魂赖以栖居的夙愿和梦想。或者说,我的身心本来就是属于这里的,生命的回归不过是时间问题。常言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所有思念故乡热爱故乡的游子共同的心愿和期盼,数千年来不曾改变。“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所幸褪尽铅华,浮躁不再,云水未负禅心。贝忙的景物为证,光阴倏忽,转头即逝。唯天地永恒,接续绵绵大爱。风清过后,依然月白如初。银汉迢迢暗渡。始终活在神话故事里不惹尘埃,何尝不是一种快意人生。
乡亲告诉我,北沟小河断流干涸数十年了,与天干、气候变暖、变热,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有着直接关系。被誉为巍山人民母亲河的大西河都常年断流干涸,何况北沟小河这些毛细血管乎?以至于,2020年红河源下暴雨导致一脉相承的大西河发洪水及至暴涨,惊涛拍岸,使得不少人惊呼雀跃,纷纷拍视频发微信上抖音以作留念。在分享巨大幸福的同时,更多是在追忆和缅怀曾经的美好时光,祭奠渐行渐远的悠悠乡愁。毕竟,在巍山人的记忆中,饱经沧桑、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的大西河,已经40多年没有发过这么大的洪水了。
说到北沟小河,不得不提一下曾经陪伴过无数代乡亲成长、却在前几年被毁于一旦的一座石拱桥。这座被贝忙、小村、苏家寺、字官村等附近村子村民称之为北沟桥的石拱古桥,名气虽然不如赵州桥,但其精湛的建筑艺术及其文化内涵无可替代和复制,更是乡亲情感记忆的承载与精神世界的维系。我推测,北沟石拱桥应该在巍山相关史料上有些许记载,只是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而已。我曾多次近距离实地观察过,整座桥用石头修筑而成,石头与石头之间丝丝入扣,浑然一体,显示了古人高超的造桥智慧,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工匠精神的较好见证。目测最初北沟石拱桥桥高应该超过三米,数百年间,随着河床的上升,高度有所降低;北沟石拱桥南北长在十米左右。巍山是中国茶马古道重镇之一,境内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各类古桥将纵横四面八方的茶马古道连接起来,创造了历史上货物贸易的一个又一个辉煌。如今,一些古桥犹在,南来北往的马队商帮早已湮没在了往事的烟尘中,供人凭吊和追忆了。
编柳条帽“打战”的日子
——怀念我的童年少年时光
每到夏天,就会想起小时候到西河边折柳条编“帽子”遮太阳,“打战”的事情。
西河是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母亲河。又叫“阳瓜江”,上游在巍山县永建镇境内,因是红河的发源地,所以,成为了实至名归的“红河源”。西河自北向南流经巍山沃野万顷的坝子,绵延数十公里,形成了九曲十八弯的美丽景致。
更重要的是,西河两岸很多地段有数百年的柳树,成为了西河不可替代和复制的独特景观。蕴含不一样的人文风情,魅力无限。一度是摄影家们梦寐以求的绝佳之景。亦造就了很多广为流传的摄影经典,备受关注,成为美谈。
如今,虽然这些曾经的西河的“守护神”在前几年已然悉数“消失”,但烙印在几十代人生命深处的记忆无法泯灭。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小时候,经常看《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奇袭白虎团》《地雷战》《地道战》《敌后武工队》《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闪闪红星》《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柳堡的故事》《英雄儿女》等战斗故事片,或涉及打仗的连环画(小人书)。于是,触景生情,也将屏幕上,画面中的一些情节搬到了现实游戏里。从我们的村子贝忙村到了西河边,在浓荫匝地的柳树下,不约而同折一些柳条,无师自通编一顶枝叶纷披的帽子戴在头上,与村里的一群伙伴分成“敌我”两方,迅速拉开阵势,各就各位,展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或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或跳进河中打水战,像“水葫芦”(一种水鸟)声东击西。战斗中,各种“武器”因地制宜,能用的都用上了。嘴里模仿变换各种枪声,炮声,“地雷”被踩响的爆炸声,以及冲锋陷阵的喊杀声。黄灰起处,战事激烈胶着,一时间,水花四溅,一个个变成浪里白条,嬉笑怒骂皆是乐。
在河边的时候,穿在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打了补丁的,一下到水里,全都脱个精光,数十年后,记忆依旧如此彻底,留下波光粼粼的乡愁至今上不了岸。
让天性最大限度地展现和释放,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最深刻的感受。除了留在西河边的记忆,还有玩得螺(陀螺),放纸飞机,追赶五彩风车,滚铁环,打弹弓,丢硬币进洞,折叠香烟壳,斗蛐蛐,摘老缅果(可吃的榕树果)粘鸟,雨后找鸟窝,捉青鸡,石蚌,泥鳅,黄鳝,钓鱼,等等。这些东西,乐趣多多,不仅好玩,还容易上瘾,有时候让人牵肠挂肚,魂不守舍。
父亲抽过的烟
从朋友圈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的鸿雁、春耕、金沙江三种香烟牌子的烟盒,顿时勾起了心中温暖的记忆,虽然时光逝去几十年,依然觉得很亲切。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鸿雁印象模糊,父亲最初抽过的烟,有等外烟、春耕、金沙江几种。等外烟每包零售价格八分钱,春耕烟一角三分。不过,讲究生活品质的父亲很少等外烟和春耕烟。因此,一般情况下,父亲抽的是二角八分一包的金沙江。相当于甚至超过如今的软珍云烟。偶尔,父亲还抽过数量极少的大前门,大团结,中华。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
后来,父亲抽过无过滤嘴的绿壳子(俗称青蛙皮)春城,有过滤嘴的白壳春城。还抽过红梅,以及上档次的大重九,红塔山,阿诗玛,等等。父亲说,在他抽过的纸烟(香烟)中,最喜欢的还是金沙江的味道。也许是习惯了,抑或是一种依赖。
也因此,金沙江也是父亲叫我帮他去村里的购销店买得最多的香烟。每次去买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父亲拿给我五角一块钱,我会趁着买烟不忘买几颗“狗舔糖”(棒棒糖)或几片“雪片糕”之类的“嘴头食”(零食)慰劳自己,而一向大方,疼爱我的父亲,也从不会埋怨责怪我。
父亲抽烟时,爱用火塘里燃烧的柴火或火炭点烟,即使是煮饭炒菜煨茶都烟不离手。饭后又是一根烟,按照父亲的话说,这叫“赛过活神仙”。那种自在满足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父亲白天抽烟不算,上床睡觉还不忘抽一根“倒头烟”。抽剩一小节“烟屁股”(烟骨头),父亲将它掐熄,顺手塞进床铺的草帘子(草席)下面。有几次我好奇,将草帘子下面的烟屁股翻出来,用火柴点着咂上几口,结果呛得我咳嗽淌眼泪,还被父亲呲嘴黑脸一顿咒。说小娃娃抽什么烟嘛?不像屁股样子。
父亲爱好纸烟,却对老草烟(土晒烟)兴趣不大,甚至不感冒。对水烟筒也很少依赖。我没有问过父亲其中的缘由。或许是习惯了,或许是不喜欢。
如今,父亲去世20多年了。想想,人生果真是倏忽之间的事情。不知天上的父亲,过得是否安好,是否笑口常开。如果有来生,相信“饭后一根烟”,睡前“倒头烟”,依然是父亲的最爱!
竖柱
在我的故乡巍山农村,竖柱,又叫盖新房子。在喜事中,其重要程度与儿子结婚,或打发姑娘(当地俗称,即嫁姑娘)等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子里盖新房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木结构。房子的主体是木头,包括柱子,过梁,椽子、厦子,出水,等等。竖柱那天,就是将木匠之前花数月时间,用皮尺、弹墨线、锯子、凿子、推刨等工具,纯人工(手工)料理好的柱子,对准用石头打造好的圆形墩子竖起来,再将过梁逐一穿到各个榫口里去。整个竖柱过程,其实就是搭木头架子过程。其程序步骤,完全按照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术规矩进行。
那时,村民盖新房子,丝毫没有建盖钢筋水泥洋房的概念。一直以来,头脑里烙印了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物质经济的匮乏还在其次,甚至可以忽略。加之形势特殊,任何标新立异都有可能给自家惹来麻烦。当然,更主要的是生存环境决定思想意识。因此,沿袭和保持民族建筑传统风格,依然是绝对的主流。
搭架过程中,木匠大师傅在高处手握一柄硕大的木锤,依次将过梁敲进或斗进榫口里去。一边敲一边说着“吉令”,大意是祝主人家六畜兴旺,大吉大利,大发大旺之类。
手脚麻利的木匠大师傅,一般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顺利完成竖柱的整个过程。竖柱完毕,接下来就是众人期待已久的“飘梁”时刻。
所谓“飘梁”,就是木匠大师傅骑在架好的梁头上继续说“吉令”,边说“吉令”便朝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丢大粑粑和小粑粑。引来等候的客人在惊叫笑骂间一阵追逐哄抢。这大粑粑,又叫“五方粑粑”,即朝五个方向丢的粑粑,里面不仅包有豆沙,还有五分面值的硬币。
五分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举个例子,我用钓鱼卖鱼攒的十二三块钱,就缝了一套令人羡慕的涤卡衣服。这样一对比,你就明白了五分钱的价值。
能抢到五方粑粑的人,那种灿烂的笑声,以及笑声里满满的幸福,至今想起来,依然是那个时代最为弥足珍贵的表情,无以复制和替代。
小粑粑包的也是豆沙,但只有核桃大小,没有硬币在里面。不过,抢的人多,粑粑有限,所以,能抢到也算很幸运。通常情况下,大小粑粑加在一起,也就一提箩,重量在五六斤左右。
“飘梁”完毕,主人家在新房子的居中位置摆起案桌,案桌上木升子,里面装满米,皮面放置有红糖,橘子、蜡烛,青松毛之类的东西,用以祭祀神灵和祖先。
不仅如此,竖起的柱子上,贴有鲜红的对联,地上撒有或疏或密的青松毛。以及丢粑粑时木匠大师傅放鞭炮、用提壶浇下净水残留的五彩纸屑和湿漉漉的印迹。这一切,无不渲染烘托营造出浓郁温馨热烈欢畅的喜庆氛围和色彩。
竖柱之后,主人家会邀请隔壁邻舍、三亲六戚择机适时拉土冲墙,将新柱子围起来。然后再买来瓦等材料,将顶上的柱子、椽子盖起来。整个过程,短则半年多,长则一年以上。走完所有工序,细致繁琐,一丝不苟。“偷工减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人心亘古,世风如初。

往期回顾
◆吕翼入选《中国文学年鉴》的小说《少年的金牙》,到底讲了啥?
◆群山丨存文学中篇小说 : 独龙江的麦子(三)
◆群山丨存文学中篇小说 : 独龙江的麦子(二)
◆群山丨存文学中篇小说 : 独龙江的麦子(一)
◆群山 | 吕翼中篇小说:《穿水靴的马》(三)
◆群山 | 吕翼中篇小说:《穿水靴的马》(二)
◆群山 | 吕翼中篇小说:《穿水靴的马》(一)
◆群山 | 尹宗义 : 小说创作从揭示矛盾开始 ——评吕翼的中篇小说《穿水靴的马》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ID:ztrbwx)
审核丨@空
特邀编辑丨朱镛
美术编辑丨尹婕
投稿邮箱丨519045426@qq.com
广告咨询丨0870—3191969
@昭通日报 微信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