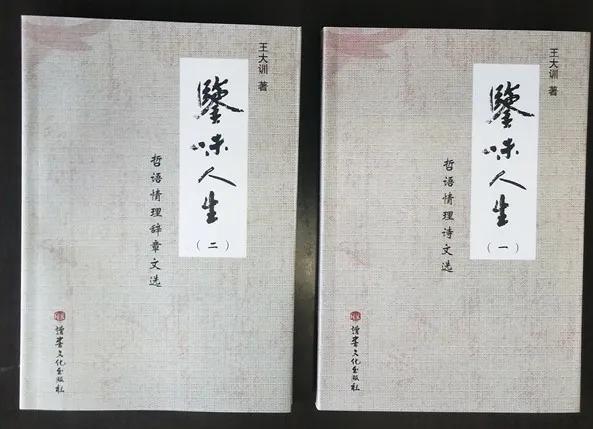然而,要思辨参透人性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人既非寻常之物,亦非寻常之生物,人是复杂性之最的物性形式,也是自为性主动性动变性之最的生物形式,而且,人性作为一种思辨对象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具象物象的直观形式。人性不是具象现象,而是内在而抽象的存在属性,无可直观,无可量化与实证。具象者为物,既是空间性又是时间性存在的实在,有光色,有边界,有空间,有数量,可以直观与量化,因而,物的存在对象以及对象与对象的存在关系,是可对应的也是可确定的,是可以证实的也可以证伪的。人性则否,人性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形式,人性存在于人的形式中,但人的形式不等于人性,只是人性的表观表现。人形是物,观人形者不是人学而是物学,即是经验的实证的自然科学,如关乎人体生理、病理之医学等等。但人学不是这样,人学不是识人体观人形,而是识人性观人性,而人性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的特殊观照对象,从直接性而言,实际上为无可直视无可直观,即没有直接可对应的具象对象、只具有决定这些具象对象的虚存在,但却是具有真实内容内涵,或者说具有真实属性特性的实在概念观念。也可以说,人性存在于人体人形中,但作为一种虚在的对象实在的概念,仅仅存在于思辨和观照者的抽象思维中。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存在着先天的局限,一是人性是人而非人形的特征使得玄学和物学都难于完全适境,二是人是识者又是被识者,人性是工具又是工具对象,在认识上存在着主客难分的困境,三是人性存在于人体人形中,但却难于确定其存在的载体,四是不能直观人性仅可直观人性之表现表征。
因此,古来的思想家一直在寻找破译人性之道,但却一直难于获得大的突破。虽然古人很早即在寻找何为人本人性的载体,也很早发现人心主人事,人心为人意人志的载体,但人心究竟为何,却一直未有定说。甚至在漫长的远古和近古时代,先贤们一直难于确定人心是什么,人心是人的生理之心吗?显然不是。因为古人无论从宰杀畜禽还是战争杀戮行为中,都见过生理之心,都知道生理之心不过是与血路相联的生理器官而已。很显然,这样的生理之心难主人意人志,只是主人体之生理生存而已。这样直视直观而对生理之心的理解为医学,亦为物学,即中医所谓的心主脉,西医所谓的人体生理学。但中国古人所谓“心之官则思”,其观照之心已非生理之心,即心脏之心,而是有了近现代心理学之心的内容。这样的心理之心已非实在的具象,而是决定实在的人体人形具象现象即其功能和属性存在形式的抽象。这样的“心”,既非生理之心亦非生理之脑,而是近现代以来心理学之“心”概念的源头和萌芽。西方学家总乐于将德国人冯特作为心理学之父,当然,是冯特首创近代心理学并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为近代心理学第一人,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他的学术是无源之水,不能认为古代没有心理的概念,没有对人的心理予以观照和思辨。如中国最伟大的兵学家孙子,其所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对敌我双方心理战的重视和心理学术的理论发现与实践。孔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心同样为心理之“心”,而非生理之心;中国古人之治国驭邦,极为重视人心的分量,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天下失”,亦属此类。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看到,对人类心理和对人性的重视和关注古已有之,只是较为原始简易,其思辨思想大都分散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尚未形成规模形成专业化的学术体系罢了。
叔本华是哲学家,但他更关心人性和人的意志,他甚至为此苦苦寻找,人的各部分生理脏器、生理组织和人性特别是意志的关系。他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性器官是生命的中心,他说,“性器官比身体上任何外露的器官更是只服从意志而全不服从认识的……性器官可说是意志的真正的焦点”。叔本华认为脑是认识的代表,而认识是与意志相对立的另一极。
古人关注人性亦关注人心,是因为他们发现人心中有人性,人心中有人的行为和生存个性的全部奥秘,或者说,是人心决定人的意欲意志,决定人的行为方向行为力度等生存个性生存形式形相。他们发现人心的重要性,正如其发现人性的重要性一样。然而,发现人性的重要并非可轻易地发现人性的奥秘,人性之善说、恶说、善恶混合说,正说明破解人性之难,达成共识之难;同样发现人心存在的重要性,发现人心与人性有相当大的强关联性,也并非意味着人们在发掘人心存在奥秘中可以成功。这是因为,在古代人类学术尚处于原始之混成期,亦处于较为初级的原始状态,各门学术相互交杂分化分离尚不充分,其理论工具少而简易,除玄学以外的其他各类次级学术,尚处于与其母体和其他子体相分离的萌芽期,人类文化的成长和积淀尚处于初级阶段。这样,尽管古代的思想家已隐约发现可将人心作为发掘人性存在的载体,但他们难以完成这样的使命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