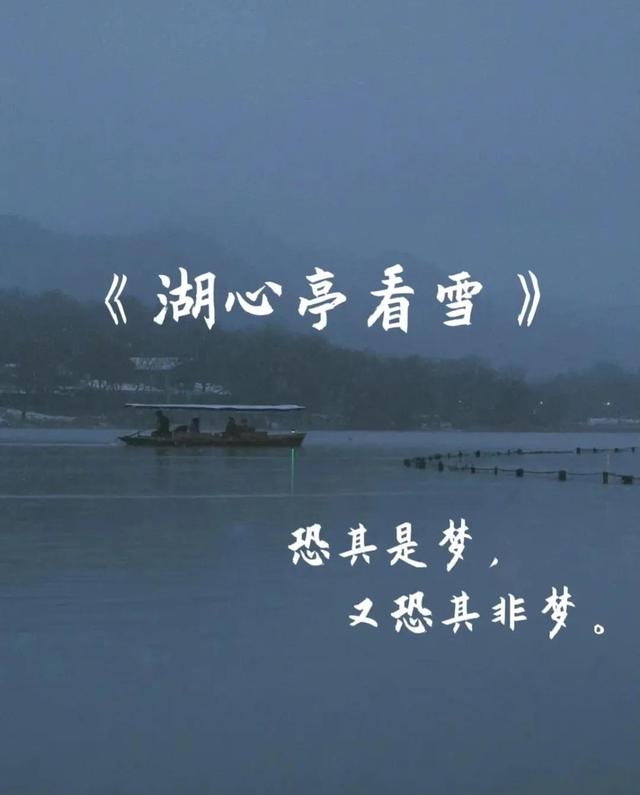作者:高波

作者父母与姥姥合影

姥姥是缠了足的旧式妇女,小小的三寸金莲,印证了旧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品味,小时常见姥姥隔段时间放下腿布,烧好热水去洗脚,我悄悄偷看,她便怪责:“去一边去,小孩子看啥。"我看到了姥姥的脚指头弯曲变形,镶嵌入脚深凸处,这哪是在审美,分明是造丑而藏于云间,便是满夷人的尚美观,陈腐而令人悲催。姥姥当初幼女缠足时的痛苦,似乎听命父母或社会陋习,不得以或是这样能找到好婆家的宿命所致。现在市场上很难寻找姥姥穿的小脚鞋,随着姥姥那代人渐渐走进历史,姥姥的小脚便成了我们永远的追忆,留下的都是片片不息,无法忘却的儿时影像,姥姥虽平凡,但她记录了一个时代。姥姥在我们心中是一本读不完或是看不透的书,她就是色彩滨纷的传说,悠久与现代的重叠,姥姥生长在农村,她留恋乡下,又低视乡下,心里多少带点虚荣,童趣的表达让人缔笑皆非,小时常问她:”姥姥您是城里人吗?"姥姥当着大家的面,又故意漂了女婿一眼,抖抖肩,似乎很有底气,仰头大声说:"俺革了根的,就是城边长大的"。表情自然又自信,似乎告诉我们,河北的老高家农村里边的,还不如我呢。姥姥是我们幼时的守护神,她生于清朝未年,清末的甲午那个令国人耻辱日子,便是姥姥开始的苦难岁月,战乱,疾病。少女便成了童养媳,进了唐家门先后生育了八个孩子,中途夭折了6个,悲痛与泪水伴随着她走过了年轻岁月,活下来的两个女儿相继嫁给了共和国年轻的军官,他们后来都进阶党的高级干部。
姥姥性格坚韧,泼辣,从不向困难低头,或许是早年过多磨难砺炼所致。文革动乱时,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满街乱跑,又常与同伴打架,气得姥姥大便不通,常去医院灌肠。姥姥手很巧,她常给我们剪纸彩,粘贴在窗上,有蝴蝶,有牛馬,生态各异,形象逼真,那时只觉得姥姥是个传统的绣花女的手,现在猛悟,姥姥聪慧而伟大,其剪纸手艺,足以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几十年后,回想姥姥的妙手,再联想她老人家点滴祖孙情,常常勾起我们对姥姥无尽的思念与缅怀。小时候母亲常常给我们讲起大姨和小姨,倆人在母亲心中刻骨铭心,大姨18岁刚嫁人被毒蛇咬伤致死,最可怜的还是小姨,那天,她肚子痛疼在地上打滚“哇哇”大叫,喊着妈妈,姐姐,眼睁睁离开了人世,每每忆述此景,母亲眼里浸满了泪水,她很爱这个围在自已身边活蹦乱跳的小妹。姥姥在我们面前从不提及这些悲怆往事。走了六个孩子,姥姥姥爷想要儿子防老,就从亲戚家过继来唐家一个男孩,取名国青。后来姥姥晚年的安度,是在两个孝敬的女儿家度过的,离世时,外孙外孙女扶柩送终。
姥姥胃粘冷就痛,她吃水果特小心,冬天常将水果放在暖器上加温后去皮吃。姥姥上衣兜里有个小手绢,那不是擦口水的,那是装钱的小包裹,三层皮,包裹着几十块钱,那是她两个女儿给她的零花钱。她偶尔高兴时,给外孙外孙女们买点糖果。我家的菜园子都是我和姥姥伺弄。姥姥教我如何播种,除草。姥姥在院里养了十几支母鸡,她常抓起鸡摸摸腚根,判定此鸡能否产蛋,若判定此鸡不再产蛋,她便自语说:"杀了它。"姥姥杀鸡别样,正常杀鸡在鸡脖气管切开口子放血,而姥姥挽起袖子,一手拎起鸡头,一脚踩着鸡身,一刀将鸡头斩断,扔在地上,她拎起鸡血染红的菜刀,迈着小脚很威武的样子径直走进屋里。
我幼时姥姥常常牵着我的手,到离我家一墙之隔的锦州市图书馆庭院小憩,姥姥将手绢铺在草坪上盘腿而坐,院内鸟语花香,我围在姥姥身边转悠,寻找毛毛草,姥姥眼晴时刻盯视着我,生怕我跑出她的视野。太阳西落时分,她又牵着我的手,走到院外,等候我父亲下班,当父亲走到我身旁,伸手将我抱在怀中时,总能看到姥姥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幼时的记忆是零碎的,模糊的,只是记得住了,便永生难忘。
姥姥是我们心中的一盏灯,时时照亮着整个家。姥姥去二姨家时,家里顿时觉得空荡荡的,沒有了生气。我家住平房有独立的小院,姥姥进出方便,常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内晒太阳。姥姥是幸福的,晚年得到了两个女儿和女婿的无微不致的关爱,记得部队盖新房子,特意想到了我姥姥爱睡火炕,所以,便有了每户首长家有个火炕的设计。
每到春节,到家拜年的人首先到姥姥火炕屋里,给姥姥拜年。姥姥在沈阳二姨家或我家患病时,都得到了精心治疗和呵护。姥姥把所有的爱洒在自已的外孙外孙女们身上,姥姥只有两个女儿四个外孙,两个外孙女,她都拉扯过,姥姥多少偏爱两个长外孙,疼爱有加。不知那个年代,姥姥看到我们围在她身边戏闹,她叹了口气说:"我先前生了个儿子,都长到8岁了,可着人喜欢了,可惜得病沒治过来,死了。瞧我这命。”那时我小,不懂深纯的人间情感。成人后,尤其为人父后,才理解姥姥那一声叹气,对失去骨肉,失去爱子的彻彻的遗痛。我终于明白,姥姥爱孙,生怕失去他们。若干年后,当我站在姥姥墓前,真正觉悟到,姥姥在我们身上延续着伟大的母爱…
姥姥沒念过一天书,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头脑敏悅,是非条理清晰,为人和气善良,谁做错的事儿,她都据理力争。偶尔护着我哥小峰,表哥可心两个长外孙小短。选择性偏爱后代,这是长辈们共性。姥姥十分喜欢两个外孙女,大外孙女丹丹我表姐,小时不听她招呼时,她常怪责:"死丫头片子"对小外孙女我妹妹丽达常呼“达达"。姥姥遇事好拨尖,保姆和我奶奶都很怵她,她是老太太群里的老大,谁招惹她,准让她下不了台。姥姥较起真来口齿尖砺,得理不让人,邻居们都晓得姥姥的厉害,自然都敬畏她三分。
我小时不懂事,时常在姥姥面前戏闹,姥姥后来不大稀见我,再有我常跟她耍嘴皮子,便给我起个外号:二白呼。每每叫时,充满了爱意,脸色显得温怒。即使我再调皮,也是装装面带怒气般的脸色吓唬我,或是拿起扫炕的扫把轻轻的在我腚上打两下,无奈时就冲她的女儿女婿嚷嚷两句:“还笑,都是你们惯的。”再急就喊:"小死波。"当然我跑了,知道姥姥的小脚追不上我。姥姥晚年无大病缠身,这得益于两个女儿女婿的孝敬,还有两个家庭的优越条件,有部队医院和二姨所在医院的特殊照顾,姥姥身体一直无大碍。寿终96岁高龄,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姥姥饮食简单规律,从不暴饮暴食,即便吃鸡虾鱼肉,也是点点入口。姥姥爱吃野菜,在阜新市政府大院居住时,夏秋季节院内长满各种能食的野菜,姥姥便摘一大筐野菜拿回家里,放上肉丁包包子给大家吃。姥姥最操心也是最惯宠的就是大外孙小峰。小峰儿时淘气的很,在外面时常惹点是非,又逢文革动乱,不时能听到街里响起的枪声,姥姥怕我们被伤害着,惊吓着,此后几年总犯大便不通的病,常常到军卫生所去灌肠。后来我家搬到阜新坦克五师后,此病便渐渐好了。我的记忆里,二姨和我母亲结婚后,姥姥再未曾回凤城凤凰山脚下的二台子老家,就是在姥爷病重至离世,她也未能看看相依为命的老伴最后一眼,因她放不下我们几个嗷嗷待哺外孙外孙女,留下了无法补救的遗憾。几十年后,姥姥临终弥留之际,昏迷中喊我姥爷:“唐本利,你这死鬼,我找你去了,等着我。"姥姥终生挂念姥爷,很少言语表达,把对姥爷的爱与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
姥姥在我母亲面前常常数落国青,怨责国青不孝顺,白给他养大了,也不来个信,也不过来看看我,也不知道孙子小喜这孩子怎样了,心里总是惦记着他们。每年的清明时节,姥姥总是望着窗外自然自语:“也不知国青给他爹上坟沒有。”母亲见姥姥思念孙子小喜心切,七十年代初请舅母和小喜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期间,见姥姥脸颊红润,天天喜不自禁,总拉着孙子手嘘寒问暖,爱不释手。我们小时的棉裤都是姥姥和我母亲一起量做,旧的棉裤的棉絮散发着尿的骚味,姥姥便放在窗台或暖器上晒烤。我们都穿过姥姥做的千层底。每次做鞋,姥姥将浆糊均洒在布上,一层层沾好烘干,找来旧鞋量好脚的尺寸,剪下样后,便一针一针的纳,看着姥姥的表情总是淡然的,穿线中交响着生活的寄望。姥姥做的鞋虽不时尚,但憨实,那是姥姥对我们的心爱。现在城市的孩子都不穿自家做的鞋了,生活已经现代派,但姥姥做的鞋,始终在我的儿时记忆里如同珍贵的家宝什物,牢牢摆在我心中的柜台上。
姥姥的火炕屋里,是我家最热闹的地方。姥姥在屋里常常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讲得最多的是鬼呀仙呀的民间故事。她也常与母亲唠叨乡下亲戚街坊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姥姥常说我耳朵大,有福像,能找个好媳妇,过上不操心的好日子。高兴时,拧我腚蛋:“你这臭小子,肉还挺紧的。”笑得她眼晴乐成一条缝。
姥姥晚年过得舒心快乐。她从不跟我们去军人俱乐部看电影看戏,也不听戏匣子,偶尔坐在炕上哼哼几句乡下民歌,什么二郎神呀,嫂子哥哥之类的民俗小调。姥姥心胸豁达,凡事想得开,很少见到她愁眉苦脸的样子。姥姥笑时,慈祥而让人觉得温暖,充滿着对家人的厚厚的爱。姥姥有棵菩萨心肠。那是文革初始的一天,我在武警营房门外石阶上看到一家外省逃荒的难民,父母带着三个孩子,最小是个女孩,是个依在母亲怀里嗷嗷待哺的婴儿,全家人衣衫褴褛,父母看我们是从部队大院里出来的孩子,就央求我们送点吃的给他们。我跑回家里告诉了姥姥,姥姥二话沒说,盛碗大米饭,拿着两个馒头,一同来到要饭的一家人身边,说:"地旱了吧,沒吃的了。"说罢将饭递给他们。过了几天,姥姥跟我们说,那家要饭人家,把最小的孩子送给了火车站前一户人家,那孩子可怜,比小达达小一岁。记得6岁以后便不再和父母睡了,和姥姥睡小火炕,直到我小学毕业。
记得奶奶那年到我家住时,也睡在小火炕,和姥姥言语中,奶奶颇显弱势,由于姥姥处处展示强势,奶奶有意谦让她,每当交流争论问题时,奶奶都避开姥姥鋒芒。我和奶奶回河北老家时,记得她向我的叔叔婶婶们谈起我姥姥:“那个老太太厉害子呢,俺那敢着惹她。"小锋小时偶尔半夜起夜站在炕头撒尿,好几次喷到姥姥的脸上,她怕吓着大外孙子,当时,从不惊呼他。第二天,她将此事悄悄告诉我父母。父母自然一笑了之。
在锦州住时,客厅中央小桌抽屉总是上着小锁头,抽屉里放着糖果饼干点心,那是父母给小妹丽达留着吃的,平时姥姥藏着抽屉的钥匙,我有时和小鋒哄骗姥姥打开抽屉,每每都是徒劳的。不得以,就小手伸进抽屉缝间“偷"贡果,每次小手胳膊磨划出一道道红印,火辣辣的痛。当我们吃着糖果食品,心里总有种成功的喜悦,这样前仆后继不知“偷"了多少次,姥姥也未曾发现。
在姥姥的生活中,她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候,是二姨到我家时,两个姑娘围坐在火炕上,守着我姥姥聊些过去的往事,每每这时,见姥姥神彩飞扬,眉飞色舞有讲不完的新旧话题。偶尔评价一番这些外孙外孙女们,讲到我时,自然数落我一番,离不了她对我的称谓:"二白呼,二滑,二坏蛋”记得俺姨儿子小三也被姥姥起过外号,现在想不起来了。我们参军后,心里总挂念着姥姥,那个拉扯过我们,一个颠着小脚,时不时吆喝着我们,把长辈的慈爱点点滴滴滋润着我们的姥姥。探亲回家总忘不了给姥姥买些点心水果。每每这时姥姥脸上挂满笑容:“这二坏蛋,还知道孝敬我。"后来我结婚后,对姥姥关爱不那么热频了,虽说心里仍牵挂着她,或许是年轻不虑事,或许是有了孩子,情感的着力点渐浙有了偏移,或许是婆媳蜗居相处中种种自然不适,使然我忽略了姥姥,没有更多的触及她的精神世界,温延我们的祖孙的血脉之情,那时姥姥少有言语,颇显无奈,她知道孙儿们成家立业了,而发生这里的一切都缘于生活缘于成长,烦恼是自然的。
怪我年轻时的无知和自私,孰轻孰重无需更多的释怀,其实忽略也是一种伤害。姥姥虽说嘴上沒有半句怨责,脸上表情却是一种直白的坦露的表述,一个不变的挂在她脸上的表情画"阴雨天”,就像她心里对我的儿时的评价:没错,你就是我骂对的二坏蛋。其实姥姥对我的祖孙情爱是无私的,不变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从未忘掉姥姥的养育之恩。若干年后,当我们人近黄昏,岁月的波涛不停的冲洗我们情感的螺旋时,脑海中的姥姥总是活现在眼前,我们年轻时把生命的时间自觉推断遥远而未来,现在转身一看,生命的岸头,竟如此接近我们,所以,姥姥她离我们并不遥不可及,越是临近她,越是想念她,想念中总是带着对她的亏欠,老人家余下的时光里未能与她多聊两句,陪陪她叙叙旧,割尺布给她做件衣褂,买双小脚鞋,我知道人世间,多有遗憾!而遗憾使我们渐渐学会了如何感恩。是的,如果沒有遗憾,世界就不会完整,就沒有美丽传说,甚至沒有梦想,姥姥给了我们最好的回忆,她是从最后一代封建王朝走过来的,经历了清朝,北洋时代,中华民国,新中国四朝,她虽平凡,却光彩四溢,冯高两家后人因她而有说不尽道不完的历史故事,这故事是质朴的,农家的也是巷子里的,她风趣的童话般的语录,让后人心旷神怡。
那是一个炎热而静悄的夏日,一位世纪老人安详的走了,外孙外孙女们扶柩送别。姥姥沒留遗嘱,弥留昏迷中曾几次重复一句:"光溜溜来,光溜溜去。"人生价值哲理姥姥竟深明在心,道出了人活着与死去的归宿,现在我才读懂了姥姥,姥姥不简单!姥姥安葬在大连乔山墓区,一个青山绿水的山腰间,墓碑刻下姥姥和姥爷的名字,与姥爷并骨合葬,姥爷与姥姥终于在天堂相见,沒有留下遗憾。
每年的清明,我们都到姥姥姥爷墓地看望二老,寄上几句孙儿的悼语,散絮我们晚辈们不尽的怀念,斯人已去,留下的是往日刻骨铭心的印记,当我们两鬓斑白,膝下儿孙缠绕,我们扮演姥姥这辈人的角色时,无不更加崇敬我们敬爱的姥姥,她爱的无私,毕生心血寄望于孙儿们,求他们平安幸福。姥姥离开我们三十年了,缅怀姥姥恩情似海,寄托哀思千古流芳。姥姥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