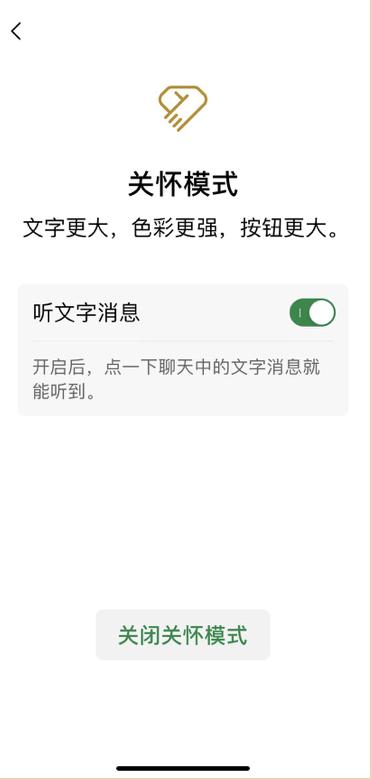上学的时候特别羡慕南方的同学,因为除了专门学习的外语之外,他们都自带双语技能——普通话和家乡话。江西的同学当着我的面打电话,我却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感觉真的是“同一个祖国,不同的世界”,有种面对密码茫然无措的忧伤。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方言种类也相当多。北方长大的我,是在面对来自五湖四海同学的时候才知道,方言的差异那么大。南腔北调,各有千秋,你的一句最普通的话,对我来说可能堪比外语。这种差异除了让人惊奇,也给人带来乐趣。
比如热爱研究语言的郑子宁老师,他首先是一个普通话吴语双母语的人,另外他还了解英、法、土耳其、老挝等语言以及常州、上海、西安、广州、海口话等多种汉语方言。这个“语言迷”曾经发表过很多语言相关的文章,最近他把文章集结在《南腔北调》一书中出版。
在《南腔北调——在方言中重新发现中国》的网络直播活动中,看到了郑子宁老师。活动中,郑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语言相关的趣事,很有活力、很有热情。刘昂老师即兴唱了一段《天净沙》,那种古朴韵味、苍凉之感,果然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能替代得了的。这就是方言和古汉语的魅力。
《南腔北调》是文章合集。这些文章并非我所期待的那种系统性地梳理各地方言整体变迁脉络的完整研究成果。当然,方言种类的多样以及语言变迁的复杂性,可能导致这样的成果很难梳理清楚,也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南腔北调》的文章特点在于散而有趣,解答我们常见的疑惑,又不乏专业知识的分析,让人在趣味中增长了见识。

其实,日常用的方言或者说土话的读音跟字典里的读音不一样,是挺常见的现象。比如老北京人都管“大珊栏”叫“大shi栏”。在《汉语拼音为什么不好用》这篇文章里,郑子宁老师解释了这个问题。首先说,汉字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虽然我们经常可以试着对陌生的字“读半边”,但这也不是什么时候都通用的规律。
自秦朝以来我国统一了书面语,但口语并没有统一,早期也没有记录读音。所以,出现很多念得出却写不出的字,也就不奇怪了。最早的拼音设计其实是外国人做的,他们为了快速学习和使用汉语,才想出了用他们认识的字母或文字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而最早对汉语进行系统性拼音化的,居然是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他们在1583年到1588年之间编写了汉葡字典,但这套方案并没有广泛传播。真正对后世影响力较大的是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编的《西儒耳目资》。
从启蒙时就先学拼音的我们,很难想象古人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拼音。不过,古人其实是有一种叫“反切法”的注音方法的,分别切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个字的韵母与声调。这种形式在一些古文书籍或者注释中也很常见。

爨,cuàn
相对于一句uncle喊遍父辈所有男性亲戚的西方人,我国的亲戚称谓可以说是非常复杂了。在《为什么uncle和cousin就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代表了》这篇文章中,郑子宁专门讨论了这个现象。
原来,对亲属的称谓一般有类分法和叙称法两种方式。相对来说,类分法区分得比较粗糙,同等、同类的亲属就用同一种称呼来表示。比如英语中的cousin,就能把汉语的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八类亲戚都代表了。叙称法就区分得比较详细,会明确得把亲属跟自己的关系表示出来。汉语的亲戚称谓就是用的叙称法。当然,中西方的亲戚称谓差别这么大,都是有各自的历史原因的,郑子宁对相关原因都做了解说。
从《南腔北调》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郑子宁不仅是在研究语言,更是从小处着眼,通过特定的语言现象,来追溯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从代代相传的日常言语中,总能捕捉到历史的气息。每一次大的群体迁移、族群融合,总能让不同的语言互相渗透,形成新的语言特征,为后人留下线索。郑子宁正擅于从每一个小的语言现象入手,深挖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成因,并通过相关的语言资料去诠释和验证。
以小见大,从南腔北调中去追寻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这正是痴迷语言的郑子宁最大的乐事了吧。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