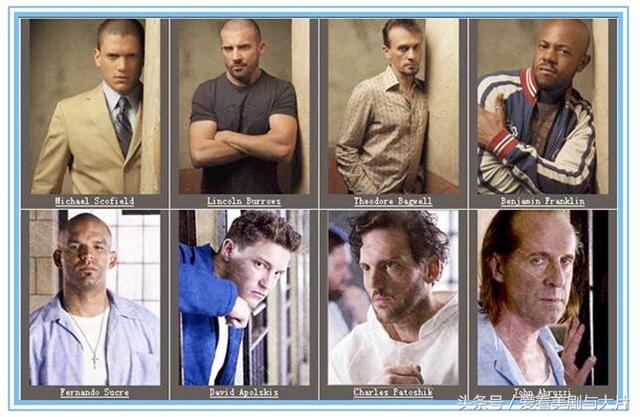过去五年,中国年轻创业者是什么样子的?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舞下,很多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年涌入创业浪潮中,一股势不可挡的创新力量翻涌而起。他们所创立的公司,有的走到了纽交所,有的成为行业领军者,有的在产业纵深改革中成为最锐利的科技创新力量。但还有更多人在创业创新的路上,正在寻找助力梦想启动的“第一桶油”。
青年创业创新力量促进产学研用的融合,也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最重要的原初力量。眼下,越来越多的90、95后新生代创业者带着新鲜的视角和梦想加入创业阵营。但仅仅拥有创业热情和对梦想的渴望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多来自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进行到2.0阶段,这些刚踏上创业路的年轻人正面临着哪些难题?再过几年,我们能帮助这些青年创业者书写出怎样的答卷?呵护这些梦想的种子又意味着什么?
创新的起点:解决一个微小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小时候都曾梦想做一名科学家,创造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王力从小就觉得科学家很酷,从复旦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毕业后,王力在杜克大学继续深造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而后进入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科技公司负责研发工作。此时他从未想过,日后自己会从喜欢的研发工作离开,开始在“垃圾堆”里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2019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迈入“硬约束”时代。“你是什么垃圾?”对于监督阿姨的灵魂拷问,盯着自己手提的一袋垃圾是要想一想。为什么要推行生活垃圾管理,这从城市建设、环保和产业角度来看,都势在必行。
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报纸上一则关于中国环境的报道对王力触动很大:一位村民去垃圾山捡可回收的家电和塑料,但他并不知道渗滤液会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也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会致癌。对于这类问题,王力所学的生物技术,完全有可能带来一些改变。
2018年,王力回国创立爱降解,他和同届的几位同学希望把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生物技术转化为真正可以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难题的产品,进而推动中国环境产业的改变。
从研发人员转型为创业者,最难的不是创建和管理团队,而是找到能够落地环保技术的商业化场景,这也成为摆在爱降解团队面前的头号难题。团队希望做进一步的技术研究,但如果无法实现商业化,那么现有资金则无法支撑他们的想法。
为了解决资金难题,王力开始接触投资人。对投资人来说,他们对生物技术非常感兴趣,可当听到是被应用到垃圾降解领域,王力明显感觉到投资人们的犹豫。

除了环保,公益教育也是不容易获得资金支持的领域。乡村笔记创始人汪星宇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毕业于纽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他曾在美国一家投资公司实习,每天将自己套在西装里,手上过着200多个项目,“天天指点江山,觉得自己牛的不行。”
实习期间,公司举办“中国周”,全球政治学者聊中国,汪星宇明显感觉到,这些宏大叙事的探讨似乎不能直接解决“微小”的社会问题。有一次,外国伙伴问他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只去过大城市,对于中国乡村真实的样子,他给不出答案。
那一刻,汪星宇觉得自己不够接地气,这感觉就像是对好奇事情充满了盲区。中国乡村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汪星宇特别想知道。
2017年,汪星宇开始扎根中国乡村,创办乡村笔记。他用教育连接城乡,一头把城市孩子领到乡村,让他们亲身体验乡村生活;另一头资助乡村孩子到城市进行职业发展生涯规划学习,扩展他们的视野。为了让项目可持续进行,他希望能用商业模式赚的钱反哺乡村教育。
然而,公益教育的行业反馈慢,用汪星宇自己的话说是 “又累又不挣钱”。乡村笔记在启动之初频频受挫,愿意去理解和支持的人寥寥。

在多数年轻人心里,创业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带来一些善意的改变。罗锋以前认为设计是漂在上空的,但后来发现设计是最难落地的环节。创业前,罗锋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他跟民工兄弟同吃同住,感受颇深,每一位设计师都希望自己的设计能完美落地,但现实却屡屡事与愿违。当建筑师将二维、三维图纸带到现场,一线的建筑工人往往在理解读图的环节就会出现偏差。
这本质上是信息传递的问题。除了加强一线建筑工人的培训,还需要用数字化手段降低信息传递的难度。但过去20年,建筑工程行业长期粗放式发展,导致这个行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一直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
从复旦大学MBA毕业后,罗锋就想能否借助可视化的解决方案,让自己的设计在落地施工时能变得更加高效和人性化。2018年,以见科技由此成立。
创业的执着:成为别人眼中的“怪人”
创业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焦虑,罗锋需要逐渐习惯创业带来的变动。
在以见科技成立的2018年,建筑信息化行业仍处于蛮荒时代,业内不熟悉甚至不认可用可视化技术将建设过程标准化的理念,罗锋和团队一度接触了200多家客户,但最终达成合作的只有5个。
产品在市场反馈不佳,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起初罗锋对自己的项目非常乐观,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他估值8000万,而资本给到的反馈是在他预估基础上缩水了近三分之二。
“相当于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因为工程回款没到,融资资金没到,公司两次面临生死关头,能借能贷的都达到了极限,最艰难的一次账户只剩下几十块钱。创业的艰难,直到现在罗锋还能回想起来,某天在便利店买水,想喝牛奶,却因为舍不得掏8块钱,而又放了回去。

无论你是否做好心理准备,一旦决定跳上创业这班列车,就意味着必须学会面对公司的未卜前途,同时也要学会过滤身边的嘈杂声,专注当下。
用生物菌剂去处理餐厨垃圾,本身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实现技术突破,王力用了两年时间在实验室埋头摸索。因为需要准确模拟湿垃圾的降解场景,王力和团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复旦食堂挑满满一桶湿垃圾,师弟师妹经常会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家人也不能理解王力的选择,他们更希望王力从事一些体面的工作。但王力仍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在湿垃圾降解领域,做研究突破。
“把路走窄了”,很多人这样评价汪星宇的选择。他们不理解,一个海归高材生,《一站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冠军,为什么去做“公益”?有些亲戚甚至会跟孩子说:“你可以学星宇哥哥当年读书的那一段,后面创业这段就不用学了……”
有一种孤独,除了创业者以外,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对汪星宇来说,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最难的是建立信任。
恐惧来源于未知。把城里的孩子领往农村,家长会问农村是不是没水没电?带乡村孩子到城市学习是免费的,但家长担心孩子会遇到人口贩子。时常有家长打电话来质疑乡村笔记:“做这件事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在汪星宇看来,建立信任的方式不是解释,而是把它做出来。令他欣慰的是,孩子们的反馈带给汪星宇极大的信心,一位参与乡土研学的高中生在旅程结束时对汪星宇说,“我不知道乡村会不会记住我,但我记住了乡村。”
创业创新的土壤: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
2020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创业者的日子不好过。但对罗锋来说,信息化给他来一些新机遇。
2020年底,以见科技承接了一个重要项目,将软件应用于香港北大屿山医院的建设。为了抗击疫情,医院对工期的要求非常紧,但通过以见科技的软件,有效帮助了施工方控制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使项目顺利竣工。以北大屿山医院为开端,以见科技在此后的半年内相继在香港落地了近10个项目。
罗锋从不考虑后路,他只想朝前看。他总说,创业是一条完美的微笑曲线,所有低谷都是离希望最近的地方。在命运的转角处,总有人愿意给创业者们搭把手。
2018年4月,当现金流险些断裂的时候,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成为以见科技的首个无偿外援,帮助以见科技度过了最艰难的生存期,让罗锋的创业团队开始走向正轨。今年9月,以见科技顺利完成了A轮市场化融资,公司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爱降解仍在研究如何将降解后的垃圾转化成工业原料。相比于以见科技这种有实用场景的项目,爱降解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这也就意味着王力和伙伴们获得商业化进展的难度更高。
过去3年,整个公司一边承担着科研压力,一边苦于寻找资金支持。2019年,爱降解申请到来自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的无偿资助,同时王力也在持续做商业化的尝试。目前爱降解的产品开始相继在高校食堂、居民小区、餐饮企业及垃圾中转站等实际场景中落地应用,整个降解过程真正做到有机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王力希望用实验室的生物技术改变湿垃圾降解的现状。事实上,爱降解所研发的有机垃圾降解处理机,其微生物降解专利技术正是源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30年研究成果。王力深知,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是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爱降解也可能走不到终点,但他希望这把“微弱的火光”能照亮更多路,能有更多人加入进来,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对创业者来说,风雨兼程的经历究竟值不值得,没人可以给出答案,但即使前景不明朗,也不妨碍创业者继续去做向善的事。
汪星宇觉得,一个好的世界,应该是人与人之间能彼此感同身受、将心比心,隔阂慢慢被缩减、被填平的一个世界。乡村笔记带城市孩子去农村研学,他们去了湘西的山村、甘孜的藏区、红河的梯田、菏泽的戏班,还有敖鲁古雅的狩猎部落。孩子们不是去旅游、不是去支教,更不是忆苦思甜,而是去社会调研,学戏曲表演、建筑设计等课程,身体力行融入乡村生活,汪星宇希望城市的孩子们能用一颗平等心去了解乡村。
2018年,国务院规划部署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振兴乡村教育是工作重点,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到底什么才能改变农村?汪星宇觉得一定不是瓜果蔬菜,而是乡村的孩子,比如带乡村孩子来一场城市职旅,让小镇乡村的孩子了解各行各业,看到世界的更多可能性。最近两年,乡村笔记和云锋基金联合开展“公益职旅课堂”,云锋基金的投资人会以亲身经验帮助学生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创业四年,乡村笔记已经和全国各地的上百个乡村建立联系,带领4000多位孩子从城市去乡村研学,同时资助了400多个孩子从乡村到城市。课程已经覆盖到5万人。
“让城乡之间能够彼此看见,让大家认识到世界的更多可能性。”汪星宇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除了汪星宇、罗锋、王力,还有许多依然在实现梦想路上的青年创业者。在复旦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里,有一面梦想墙,上面悬挂有151个项目名称。汪星宇的乡村笔记、罗锋的以见科技、王力的爱降解只是其中的缩影,他们共同用科技创新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同时也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路径。

创业创新的成长:无条件的公益陪伴
孵化创业创新的梦想需要来自多方支持。2015年,云锋基金与复旦大学达成战略合作,捐资设立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用以支持复旦大学创业创新人才的培育以及创新科研成果的转化。这些项目在通过复旦大学的评审后,即可获得来自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的无偿资助,不占股权,不求回报。截至目前已支持孵化151个项目,涉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集成电路、低碳环保、乡村教育等行业。
其中,以森亿智能为代表的医疗AI企业,通过向医疗科研、医务管理、患者服务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速了智慧型医疗系统的建设;以瑞凝生物为代表的生物科技企业,在医用水凝胶领域开发出独创的技术路线,有望为肿瘤临床治疗带来全新方法;以上海大芯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企业,致力于通过自主研发的SPAD工艺,实现混合型堆叠封装3D Lidar芯片,全面提升手机、AR/VR等3D应用水平……
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将以10年为期,在10年内持续为复旦大学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启动资金支持与创业辅导帮助,促进复旦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
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运行六年,目前双方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效应。复旦大学在办公场所、人才招聘上给予年轻创业者支持,云锋基金则能在资金支持、辅导培训、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层面给予有效补充。在具体实践中,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通过设立云锋创新大讲堂,邀请诺奖得主等知名学者与高校创业者对话,以此培养更多前沿科技、生命健康领域有竞争力的创新人才。目前,云锋创新大讲堂已邀请包括诺贝尔奖华人女科学家周芷、哈佛大学免疫学家吴皓、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院士Jeremy Nicholson等在内的49位顶尖学者到访,与创业创新班同学进行面对面交流。
在云锋基金看来,好的土壤能让创业创新的种子萌发,而每一棵参天大树都始于一粒微小的种子。创业创新越来越回归原创的科技创新,回归基础科学研究,创新的主要力量正在从大学实验室里走出。
在设立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的6年里,云锋基金发现,帮助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从校园里培育创业创新的点子,需要给予这些种子无条件的公益支持,这也是云锋基金设立复旦-云锋创业公益基金的初衷。立足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云锋基金希望帮助孵化、连接、转化原始创新的成果。科技强国,创新为先,涓埃之力,未来可期。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来看,科技创新的原初力量往往来自校园。以校园为起点,成长出了如谷歌、微软、戴尔等创新企业。经过多年实践,国外部分高校通过与基金合作,构建了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包括创业教育、创业活动,到提供创业服务的孵化器、加速器等,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的高校和投资机构们也正在摸索符合国情的创新企业孵化道路,为这些宝贵的“种子”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帮助科研成果、创新想法实现产业化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