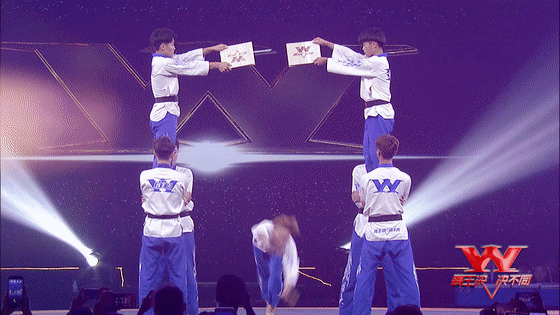海蓝蓝/文
海在我心里有着无法用语言描述的魔力,竟将三十年笔名屏蔽。从2014年,我的文学作品全部署名:海蓝蓝。
海对我来说,不仅是因它的颜色同我乳名,更有它带给人的宽广和气魄。小时候,我眼里的海,是公园的游泳池,比澡堂大很多;是洋河,比泳池长很多;是人工湖,我目睹哥横渡,畅游。
读师范第一年秋,陪同学回家。下车已是深夜,不知她家位于何方。翌日,在站台意外发现,偌大一汪秋水就在眼前。那片荡漾的碧波,惊呆了怀揣海之梦的我:“这是什么海?”
“哪是海啊?官厅湖!”同学笑我。
深居盆地二十载,没见过家乡之外的世界,比人工湖大多少倍?海会是什么样?在我心里,对海的向往越发强烈。
一九八六年,我作为出席全国煤炭系统先进个人,获得一种独特奖励:到北戴河“中国煤矿疗养院”。 对二十五岁的我,这种机遇极其难得。我果断决定:撇下两岁儿子,到海边去,到北戴河去,看梦寐以求的海。
独自到陌生地,坐班车再乘火车,到北戴河已晚八点。公交停运,寻一位面善年长的出租车司机,送我到指定地点。
我一路主动和他聊天。车到市区停下来。我急了:“您怎么不到疗养院?”
他笑了:“前面就是。出租车夜间不能靠海。”
我近乎喊起来:“我怎么相信您?人生地不熟,让我往哪儿?”
“先别给钱,问问交警。对了,再给我。”
我穿过斑马线,问值班警察。他指指身后:“就这儿。”
借着灯光,我看到刻字卧石,心里踏实了,又过去将十块钱给了司机:“对不起大叔。”司机点点头,叮嘱我一定要去鸽子窝,看海上日出。
疗养院晚上也有人接待。办好手续已是十一点。躺在床上,我觉得有凉意,拽拽被子,潮乎乎的也不舒服。
外面有撞击声。同屋姐姐说:疗养院离老虎滩很近。
“老虎滩!是海边吗?”我轻声问。
“嗯。”姐姐点点头。她是鸡西煤矿护士长。我不好意思问她见没见过海,忍着异样激动,听海浪有节奏地拍打岸边,进入梦乡。
“看海了!看海了!”不知谁在楼道喊。
院里许多叫不上名的树开着粉的、紫色的花。油绿油绿的草地,衬着环境格外清幽。潮湿的空气弥散着香味。我跟着人群往海边走,一上坡,面前豁然开阔。清爽的空气直入丹田,从未有过这么顺畅的呼吸。
“海?”
什么泳池啊,小河啊,人工湖统统不在话下,就连令我兴奋的官厅水库也不值一叹!
海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给父亲信中写道:“爸爸,我看到海了!看到大海了!您知道吗?当我站在海边,心像被打开一样!我的眼睛从没有这么亮,能看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喜欢海的颜色。我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一种蓝啊!爸爸,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豁然开朗’的含义。”
我穿过拾贝人群,径直踏进海里,举着双臂高呼:“大海——,我来啦——”
蔚蓝的天空,湛蓝的海水。海天一色,相偎相依,我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海。我该怎样表达对海的爱。
小时读《海洋探险》,对遇险人为活下来接雨水,喝尿水的故事很好奇。总不明白为什么不喝海水。
《虾球传》有句歌词:“都说那海水又苦又咸,谁知道流浪的悲痛心酸。”
置身海中,我特别想亲口尝尝海水的味道,弯腰捧起海水,如同轻轻拾起一块碧玉。当手离开海的时候,水变白。我伸出舌尖舔了一下,上下嘴唇抿了抿:哇!我赶紧吐出来,真是又苦又咸,还有点儿涩!比吃没熟透的柿子还涩呢。难怪海水不能喝呢。
和各地来的矿长、书记、院长、校长熟悉了,一起下海,一起拾贝,可快乐的日子刚到第三天,我就待不下去了。
那天在海边游泳,突然传来找妈妈的哭喊声。 “儿子!”心“咯噔”一下,我慌忙向哭声跑去。一位年轻女子正搂着哄哭的小男孩儿。不是儿子。我恍然大悟,责备自己:为看海,竟将刚两周的儿子留在家里。他一定也哭着找我吧!我无心再和大海嬉戏,满脑子都是儿子。
老矿长看我转身离开,大喊:“小蓝蓝,干嘛不游泳了?急什么,还早呢!”我摆摆手,跑去更衣。
办理出院手续时,院长温和地说:“再住几天有其他活动,明早要去鸽子窝!”
戴眼镜的男医生说:“你看看,身边来的都是矿长、书记、院长、校长吧?哪个学校会让你这么年轻的教师来北戴河疗养?机会这么好还不多玩几天?”
儿子想妈妈或许正在哭吧?我要离开疗养院,离开北戴河,离开向往的大海。
到北京南换乘下午三点多的火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开。我坐在树下,想着马上能见到儿子,心里既喜又难过。为看海把儿子搁在婆婆家,那么小。想想自己的行为,我实在惭愧。突然,我突然看到蜂拥而出的人流,“噌”得起来,拎包就往站里跑。检票员拦住我,说:“不能进站,快开车了。你去买五点多的票吧,否则下趟也来得及。”
再看海,儿子已经五岁。我们乘渔船出海,在无边的海面颠簸,轻飘飘如同一片树叶。下船后,我躺在沙滩上,似乎还在海上摇晃。我敬佩渔民在风浪里练就“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后来,我去过很多看海的地方,从北到南:锦州、大连、天津、青岛、日照、湛江、广州、海口。在琼州海峡的渡轮上见过日落,却一直没机会看海上日出。遗憾,或许也是一种美。海在心里依旧占重要地位,让我总有海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