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北京一家著名医院的心血管内科收治了一位58岁的患者,这位大爷住院的理由,是“给自己持续了12年的症状,要一个明确的诊断”。乍一听的话,就像是那种“多方求医无门”的标准疑难杂症。
如果把症状和病史一介绍,估计很多人也会在诊断思路上挠头:患者主诉每年会发作1-4次的面部、前胸皮肤潮红,发作时伴有鼻塞、眼球充血、胸腹部不适,听起来就很像脸红脖子粗。症状出现的1-2小时后,患者血压还会明显下降。
最严重的几次发作中,患者甚至短时间失去意识,这次也是因为严重发作而住院,患者的血压降到了72/43 mmHg,直接上了重症监护,但在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维持血压后,患者也像以往一样很快就恢复如常,各种症状逐渐消失。
虽然患者被送到心内科住院,但发作时并不伴有心血管疾病常见的胸痛、发热和呼吸困难症状。患者自己也想不到每一次的症状发作,和饮食、休息、季节等因素有明显的关系。
遇到这种不容易诊断的病例,首先是要全面完善检查。但血常规、肝肾功能、血气分析、肿瘤和风湿性疾病标志物、甲状腺功能等实验室检查,以及超声/CT/MRI等影像学检查,一大堆做下来的结果,又全都是阴性或无特殊。

各种检查检测做下来没有线索,下一步咋办?
(图片来源:Pixabay)
到了这一步,大家说该怎么办?或者换个问法,诊断的头绪在哪里呢?
最终给医生们提供诊断关键线索的,是对患者胰蛋白酶水平的检测,发病当天这一指标为81.6ng/ml,9天后降到36.3ng/ml,但仍然高于参考值上限(13.0ng/ml)。
医生们接下来通过骨髓穿刺,找到了诊断核心依据——多灶性肥大细胞密集浸润,加上前面的胰蛋白酶升高,让诊断被最终确定。患者这才知道自己所患的病,是相当罕见的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Systemic Mastocytosis,SM)。

患者骨髓涂片结果,可见显著肥大细胞浸润
(图片来源: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好消息是,这位患者相对比较幸运,在此后的四年随访内不需要治疗,也没有再次出现发作[1]。但如果发展到晚期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AdvSM),那患者的症状和凶险程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往也会非常缺乏治疗手段。
肥大细胞浸润,全身各处遭殃
从病名就能看出来,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病根”,就在肥大细胞这种免疫细胞身上:形态不规则的肥大细胞,由于某些原因开始大规模异常增殖,并且浸润到患者皮肤,或者是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
细胞形态不规则、异常增殖和浸润导致症状,这听起来和癌症就很像,所以过去在疾病分类中,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曾经属于骨髓增殖性肿瘤(MPNs)的一个亚型,一直到2016年世卫组织修订血液肿瘤分型,才将它专门独立出来[2]。
目前对于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我国还没有具体的发病率报告,丹麦全国性研究报告的患病率是10万分之12,其中AdvSM的占比约为10-20%,德国研究推测的AdvSM发病率在百万分之0.8-5.2。这么低的发病率,也比较符合“疑难杂症”都罕见的认知[3-4]。
不过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发病率,也可能因为它的确诊困难而被低估了。由于肥大细胞可能浸润到各种部位,患者的症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下面这张图列出的还只是一部分较为常见的症状[5],病例报告中的情况就更是千奇百怪了。

常见的SM症状及提示浸润部位倾向
(图片来源: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自行汉化及修改版)
像开头提到的这位患者大爷,表现出的皮肤潮红、低血压等症状,就不容易一下子被确诊。而AdvSM患者如果伴有血液肿瘤(SM-AHN),或是达到肥大细胞白血病(Mast Cell Leukemia)的程度,表现又会类似淋巴瘤、白血病患者。
要准确诊断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应该注意哪些指标和检测呢?
临床诊断不易,检测需要努力
确诊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要看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症状,是否符合世卫组织诊断标准中的主要标准 一条次要标准,或者≥3条次要标准。像这种需要卡诊断标准的疾病,确诊起来一般都不容易,具体标准是这样的:

WHO制定的SM诊断标准
根据这些标准确诊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后,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患者是否有“B症状”、“C症状”对患者所属的亚型进行判断,这里就不完全展开了。下面这张流程图,清晰地给出了对疑似患者的诊断流程:

SM诊断流程
(图片来源: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但是从临床上的实际情况来看,次要诊断标准中的胰蛋白酶检测频率就比较低,骨髓穿刺进行涂片也是需要慎重考量的。而即使是在妙佑医疗国际(Mayo Clinic)这样的顶级医院,也没有对所有患者检测KIT D816V这个关键的突变[6]。
关于KIT基因的D816V突变还要多说一句,在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患者中,该突变的检出率高达95%[7],因此被纳入次要诊断标准,也是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普及外周血中该突变的检测,有助于提高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检出率。
不过KIT D816V突变的作用和意义,目前仍然不太明确,有研究认为仅存在这一突变并不足以致病[8],TET2等突变对致病和预后也有重要影响,所以通过二代测序全面检测相关突变,可能比实时PCR检测单一突变,对判断预后更有价值[9]。
诊断复杂的疾病,治疗一般也会比较棘手,不过可喜的是,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的治疗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医生们终于摆脱了只能对症治疗的困局。
精准打击元凶,初步疗效良好
如果被确诊的患者疾病恶性程度不高,那症状一般只有与肥大细胞介质释放/脱颗粒有关的面色潮红、皮肤损伤等,治疗也主要是简单对症,比如用抗组胺类药物、糖皮质激素拮抗肥大细胞介质,以及避开一些诱发症状的过敏原。
这些药物和治疗毕竟是治标不治本,对于恶性程度高、预后较差的AdvSM患者来说,直接清除泛滥浸润的肥大细胞才是关键,但此前国内还没有专门获批治疗的药物,在欧美获批的KIT激酶抑制剂Midostaurin疗效也比较有限。
不过就在2021年6月17日,美国FDA基于两项早期临床研究数据,批准能高度选择性抑制KIT激酶,有效针对KIT D816V突变的阿伐替尼(Avapritinib),用于治疗成人AdvSM患者。

阿伐替尼可选择性和强效地抑制KIT和PDGFRA突变激酶,此类致癌激酶均通过活性激酶构象进行信号传导,而阿伐替尼是一种能够靶向活性激酶构象的I型抑制剂,因此对胃肠间质瘤(GIST)、AdvSM相关的KIT和PDGFRA突变具有广泛抑制作用,且抑制效果强于此前已上市的多激酶抑制剂药物。
在美国、欧盟、中国,阿伐替尼分别于2020年1月、2020年9月、2021年4月获得批准,用于治疗PDGFRA外显子18突变(包括PDGFRA D842V突变)不可切除或转移性GIST成人患者,这是首个批准用于GIST的精准疗法,也是首个对PDGFRA基因18外显子突变型GIST具有高活性的药物。
而在AdvSM中开展的临床研究显示,阿伐替尼能够显著降低肥大细胞负荷,诱导持久缓解,且缓解深度随时间推移而加深,患者总生存期相对历史数据显著延长,有望为AdvSM的治疗带来大变革,帮助患者摆脱“疑难杂症”的纠缠。如果检测和诊断也能同步跟上,阿伐替尼这一精准高效的靶向药就能惠及更多患者。
参考资料:
1.Chen A T, Ren X Y, Chen W. Systemic mastocytosis with flushing and hypotension: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J].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2021, 21(4): 1-7.
2.Arber D A, Orazi A, Hasserjian R, et al. The 2016 revis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and acute leukemia[J]. Blood, 2016, 127(20): 2391-2405.
3.Cohen S S, Skovbo S, Vestergaard H, et al. Epidemiology of systemic mastocytosis in Denmark[J].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4, 166(4): 521-528.
4.Schwaab J, do O Hartmann N C, Naumann N, et al. Importance of adequate diagnostic workup for correct diagnosis of advanced systemic mastocytosis[J]. The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In Practice, 2020, 8(9): 3121-3127. e1.
5.Pardanani A. Systemic mastocytosis in adults: 2021 Update on diagnosis,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21, 96(4): 508-525.
6.Lim K H, Tefferi A, Lasho T L, et al. Systemic mastocytosis in 342 consecutive adults: survival studi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J]. Blood, 2009, 113(23): 5727-5736.
7.Kristensen T, Vestergaard H, Møller M B. Improved detection of the KIT D816V mutation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mastocytosis using a quantitative and highly sensitive real-time qPCR assay[J]. The Journal of Molecular Diagnostics, 2011, 13(2): 180-188.
8.Zappulla J P, Dubreuil P, Desbois S, et al. Mastocytosis in mice expressing human Kit receptor with the activating Asp816Val mutation[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005, 202(12): 1635-1641.
9.Pardanani A, Lasho T, Elala Y, et al.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systemic mastocytosis: derivation of a mutation‐augmented clinical prognostic model for survival[J]. 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16, 91(9): 888-8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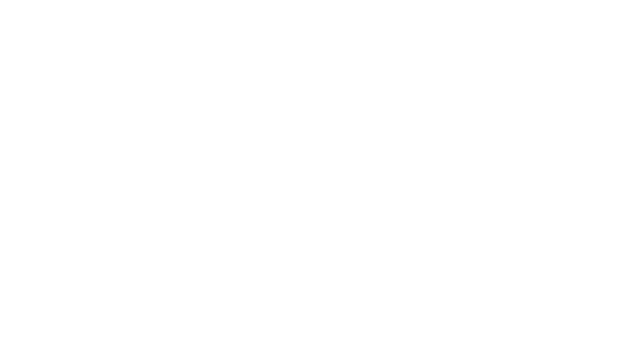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 | 谭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