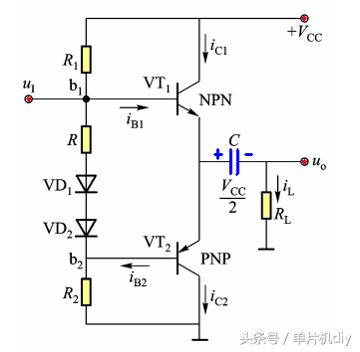她态度的陡变太明显了,那么她突陷如此深的悲哀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素爱追根溯源的我疑窦难消,于是把这事告诉给了哈蒙·高,他算是村子的智者贤人了,但令我痛苦的是,他听完只似懂非懂地哼了一声,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弗洛姆全集译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弗洛姆全集译者
她态度的陡变太明显了,那么她突陷如此深的悲哀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素爱追根溯源的我疑窦难消,于是把这事告诉给了哈蒙·高,他算是村子的智者贤人了,但令我痛苦的是,他听完只似懂非懂地哼了一声。
“鲁斯·沃纳姆老是这么像耗子似的神经兮兮;哦,想起来了,伊桑和他媳妇凑合在一起后,最早认识他们的人就是她,聚会地点就在沃纳姆律师事务所下的石路转角处,时间好像是鲁斯和奈德·黑尔刚订婚不久。那时候年轻人全都呼朋引伴的。我猜她就是受不了谈到那事儿。其实她本人也多灾多难的。”
斯达克菲尔德人,与我们熟知的社区居民一样,本身都已自顾不暇哪有精力去关注邻里的冷暖;虽大家都承认伊桑·弗罗姆的遭遇是常人想象不到的,但没一个人给我解说他那副表情背后的故事,这也是一直让我萦怀的,经济的困窘和身体的病苦都不至于把人折磨到那种程度。
我到斯达克菲尔德后,与富裕的爱尔兰杂货商丹尼斯·伊迪(斯达克菲尔德通往车站最近的那条道归他掌管)商定好要他每日把我送到考博瑞·弗莱茨,然后我在那儿等去往枢纽站的火车。然而大概冬天过了一半时本地瘟疫流行,他的马都病倒了,疫病又很快扩散到了别的马厩,就这样一两天后我开始催着寻找新的交通工具了,于是就听到哈蒙·高透露说伊桑·弗罗姆的马还好好的而马主人可能愿意送我去车站。
听完他的建议我一愣,说:“伊桑·弗罗姆?可是我从没跟他说过话啊。凭什么人家麻麻烦烦地出来送我?”
哈蒙的话更令我吃惊:“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但他多挣个钱不会难受的。”
我听说过伊桑很穷,他的锯木厂和贫瘠的田地养活一家人过冬都成问题,但没料到如哈蒙说的那样窘迫,我惊讶之意溢于言表。
“嗯,他一向是个七灾八难的人。”哈蒙说,“当一个人像艘废船的残壳一样漂流二十余年,而且逆事缠身,他失掉抗争的勇气了。弗罗姆的农场就像一个喂猫的盘子,总被舔得一毫不留,而你也看到了现在他们用的还是什么年代的老水磨。伊桑在锯厂和农田从早到晚挥汗如雨,人都快累没命了,所得却几乎都让他家人耗掉了。就那样艰难,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最早呢,他父亲因还贷受了刺激,脑袋疯掉了,死前像圣经讲的那样把钱都施舍了出去;后来他母亲患了异症,比婴儿还虚弱,跌跌撞撞了好几年;他老婆齐娜,是村中寻医的常客问药的高手。就这样一发不可收,伊桑的生命之盘里盛满了疾病与困苦的砝码。”
次日清晨,我向外张望。一匹弓背枣红马正停在沃纳姆的云杉小道上,伊桑把那件破熊皮大衣扔到后面,将雪橇上他身边的位子让给了我。从此,整整一周,他每天早晨负责把我拉到考博瑞·弗莱茨,赶晚上他又得来接我,穿过冰冷砭骨的星夜返回斯达克菲尔德。两地单程仅三英里,不过由于老马行动缓慢,虽然脚下的雪路平实如镜,我们还是用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路上,伊桑·弗罗姆一言不发,左手松松地拢着缰绳,他那伤疤累累的褐色侧脸掩在活像武士头盔的帽檐之下,再加上两边皑皑白雪的辉映,酷似一个青铜骑士的英雄肖像。自始至终他都没把脸转向过我,我提问题或仗着胆子开个小玩笑时,他也不回话,只不过“嗯啊这是”敷衍几声罢了。他似乎已与万籁俱寂而沉郁的天地融为了一体,是为这严冬冻结了的天地悲怀赋予了他形体,而形体深处重重的桎梏之下隐藏无限的温暖与情愫;不过他的沉默寡言并无丝毫怠慢之意。我当时的感觉是,他自闭得太厉害所以不易与人接近,还有就是他的孤立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因素,如哈蒙·高所透露的,几多斯达克菲尔德的严冬日复一日累积的寒意,谁扛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