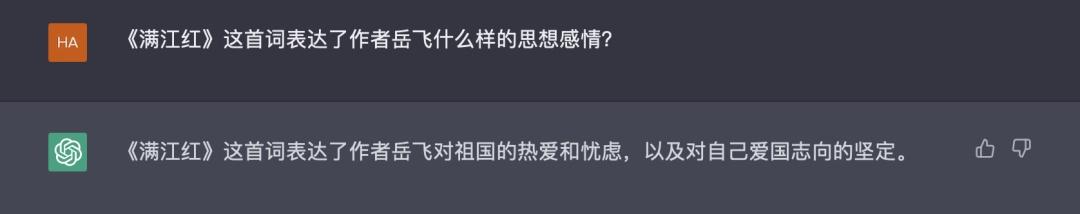横身势欲填沧海
----王安石与北宋诗风
文|熊盛元
王安石有《戏长安岭石》绝句云:“附巘凭崖岂易跻,无心应合与云齐。横身势欲填沧海,肯为行人惜马蹄?”长安岭在舒州(今安徽潜山),此绝作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时年三十三岁,在舒州通判任上。诗中以荒野巨石自喻,寄托遥深。前二句言虽出处无心,然能“附巘凭崖”,则定大有所为。后二句用精卫填海之典,而气魄极大,“肯为行人惜马蹄”,意谓我本巨石,势欲填海,安能因爱惜攀登者之马蹄而自损其高乎?其高远抱负与执拗性格,均见之言外。
关于荆公生平,可参见《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俄直集贤院。神宗立,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始行新法。三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罢。八年,复相。屡谢病,出判江宁府。元丰二年(1079),复拜左仆射,封舒国公,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1086),卒,年六十六,谥曰文。”安石晚年居金陵,自号半山老人。

一、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在北宋诗坛的地位
北宋诗坛,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开国到英宗末(960-1067),可分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总体而言,是承袭唐风,可略分三个流派:(1)以王禹偁为代表的一派,学白居易;(2)以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宇昭、惟凤、怀古、惠崇)为代表的一派,学贾岛;(3)以钱惟演、刘筠、晏殊为代表的“西昆派”,学李商隐。其中以“西昆派”影响最大。2、第二阶段乃仁宗、英宗二朝,以苏舜卿、梅尧臣、欧阳修为代表,反对西昆,致力于诗风改革,宋诗风貌初呈。北宋后期,即从神宗至北宋末(1068-1127),亦分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神宗、哲宗时期,为宋诗的高潮期:(1)、王安石的“荆公体”;(2)、苏轼的“东坡体”。2、第二阶段:哲宗、徽宗、钦宗三朝:黄庭坚的“山谷体”和陈师道的“后山体”,被吕本中列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之首,乃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
北宋时期,江西诗派形成以前,影响最大的诗人有三位,即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当然还有“宛陵体”的杰出诗人梅尧臣,此处从略)。这三人卒年都是六十六岁,今年是王安石冥诞一千周年(1021-2021),欧公比介甫年长十四岁,坡仙则比荆公小十五岁。陈师道《后山诗话》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
荆公早期仕途之顺,诗名之著,均得力于欧阳修。仁宗嘉祐三年(1056),介甫四十六岁,在汴京任群牧判官,以好友曾巩之介,终于见到钦慕已久的欧阳修,欧公作《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介甫亦作《奉酬永叔见赠》以答:“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履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欧公对介甫之期许及荆公对永叔的感激均见于言外。及乎介甫推行新法,两人政见不同,势同水火。然欧公辞世,介甫作《祭欧阳文忠公文》,有“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之语,推崇可谓备至矣。
荆公与坡翁,虽政见不同,然元丰七年(1084)七月,即介甫去世前两年,东坡由黄州转任汝州团练副使,过江宁时曾与金陵守王胜之同往蒋山访介甫,见到介甫《北山》“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爱赏不置,当即作《次荆公韵四绝》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就诗论诗,坡翁此绝,逊介甫原作远矣,容稍后论介甫诗艺术特色时再分析。惟东坡在荆公逝后(元祐元年,1086),噤而不言,次年,即元祐二年(1087),司马光卒,东坡作《司马温公行状》诋毁荆公曰:“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士之忠信者,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第二十七首曾涉及此段公案,诗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
稍稍解释如下: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严羽《沧浪诗话》:“元祐体:苏、黄、陈诸公”。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金陵,当指王荆公。‘犹有说’,即以人废言之意。”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张)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翁方纲《石洲诗话》:“此‘回’字,即坡公‘升平格律未全回’之‘回’字,是遗山力争上游处也。亦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亦何尝有人欲‘废欧梅’?观此可以得文章风会气脉矣。”查慎行《初白庵诗评》:“若就诗论诗,半山亦不在欧、梅下,谁能废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祐苏、黄诸人次第变古。”按:芸叟即张舜民,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屡遭贬谪,元祐元年,经司马温公引荐为监察御史,对荆公死后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作《哀王荆公》四绝:“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我甚赏明代胡应麟《诗薮》外卷五对介甫诗的评论:“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由胡氏之论,可见王安石在北宋诗坛的地位,是处于欧翁与苏、黄之间,既承継永叔,扫荡了西昆的遗习;又下启坡、谷,开创了坡翁的新变与山谷的奇诡,在某种程度上看,甚至可以说,荆公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人物。只是因为人们大抵不满荆公的变法,故有意无意地抹杀了其承上启下的功绩而已。

二、半山绝句当朝餐
----王安石“荆公体”对两宋诗坛及后代的影响
“荆公体”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一种诗体,主要指介甫晚岁退隐金陵的七绝。诗风近乎晚唐,境幽而味永,所以南宋的杨诚斋特别赏爱,称自己把“半山绝句当朝餐”。窃以为“荆公体”不仅指其七绝,也包括其他体式的诗作。下面不妨引用两宋及后代对荆公诗的评价,并适当加几句按语:
1、黄山谷:“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
2、陈师道《后山诗话》:“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
(梅云按:元遗山亦曾论及东坡之“新”,见《论诗三十首》之二十六:“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或作“许”)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稍作阐释:沈德潜《说诗晬语》“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可与元氏“金入洪炉”同参。郭绍虞云:“以上二句(指第一二两句)是褒苏之词,真金经过锻炼,本自精纯不受纤尘。然诗家古调,亦至苏而亡,古末句又以‘百态新’贬之。”明何仲默《答李献吉书》云:‘文靡于隋,韩(愈)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渊明),谢(灵运)力振之,然古诗之法亦亡于谢。’东坡亦云:‘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诗人玉屑》)。赵翼《瓯北诗话》‘元遗山论诗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言似是而非也,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此论对元氏贬弹苏诗‘百态新’之意有误解,盖以苏诗‘斗靡夸多’为新,有失风雅之古意耳。”翁方纲《石洲诗话》:“此章收足论苏诗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也。‘百态新’者,即前章‘更出奇’也。”又,元遗山亦论坡、谷之“奇”,见《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二:“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亦略加解释:关于“奇外无奇”,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波澜开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关于“诗到苏黄”,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严羽《沧浪诗话》则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沧浪所谓“骂詈”云云,遗山亦曾论及,见其《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三首:“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分析从略。其实“新”“奇”之弊,实起于荆公,苏、黄不过推波助澜,达到极至而已。)
3、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齿间。”
4、《王直方诗话》:“陈无己云:‘荆公晚年诗伤工。’”
5、叶梦得《石林诗话》:“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
6、又:“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
7、《艇斋诗话》:“荆公诗及四六,法度甚严。汤进之丞相曾云:‘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此说甚然。”
8、《诚斋诗话》:“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然鲜有四句全好者。”
9、杨万里《读诗》(其一):“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读诗》(其二):“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
11、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则有……王荆公体,又自注云:‘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
12、明代胡应麟《诗薮》外卷五:“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
13、明末清初贺黄公《载酒园诗话》:“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自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特推为宋诗中第一。其最妙者在乐府,五言古、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稍后安排,七言律尤嫌气盛,然佳篇亦时在也。”
14、吴之振《临川诗钞序》:“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遣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梅云按:“悲壮即寓闲淡之中”之评,可谓“荆公体”之知言也。”
15、清代方植之《昭昧詹言》十二:“向谓欧公思深,今读半山,其思深妙,更过于欧。学诗不从此入,皆粗才浮气俗子也。用意深,用笔布置逆顺深,章法疏密,伸缩裁剪。有阔达之境,眼孔心胸大,不迫猝浅陋易尽,如此乃为作家,而用字、取材、造句可法。半山有才而不深,欧公深而才短。”
16、清末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七:“读荆公集竟,摘句如下(略)。皆山林气重,而时觉黯然销魂者,所以虽作宰相,终为诗人也。”(梅云按:“虽作宰相,终为诗人”,诚荆公异代知音也!)
17、当代钱锺书《宋诗选注》论王安石:“他比欧阳修渊博,更讲究修词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内容充实,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地表达了新颖的意思,而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诗往往是搬弄词汇和典故的游戏,测验学问的考题;借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把不经见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鲜而其实古旧的词藻来代替常用的语言。典故词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于《六经》《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书,就愈见工夫。”

三、一鸟不鸣山更幽
-----从苏老泉《辨奸论》说开去
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以暄闹衬幽静,历来被人称赏。荆公以“风定花犹落”,以对“鸟鸣山更幽”(见《梦溪笔谈》),诚绝妙无论。又在《锺山即事》诗中借用王籍句云:“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人多讥其点金成铁,盖“一鸟不鸣”,死寂而无生机,实在大杀风景。然而,此正见介甫遭谴归隐时特殊心境,因其推行新法,遭众人反对,故希望人皆噤声也,此亦见其“三不足”之执拗本性(“三不足”乃介甫名言,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与孔子之“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反)。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收入《辨奸论》,有“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之语。《古文观止》将此文列于苏洵名下,评曰:“介甫名始盛时,老苏作《辨奸论》,讥其不近人情,厥后新法烦苛,流毒寰宇。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此书影响极大,人皆信之。老泉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此文最早见于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死于王安石变法前三年,故学术界普遍认为此乃伪托。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力辩其伪,引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留苏洵。洵问欧公:“适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乃王安石,子不闻其名乎?”洵曰:“此人若得志立朝,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何以与之交友?”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蔡上翔辨曰:“士大夫一起吃饭,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属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何以了解得如此周详,且攻击其丑恶如此激烈?”
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
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邓广铭、郭沫若等均同意蔡上翔的观点。
宋代《京本通俗小说》有《拗相公》话本,其中有诗曰:“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军岂得渡黄河?”将北宋灭亡归罪于荆公,《大宋宣和遗事》对介甫更极尽漫骂之能事。

四、荆公诗简析
(一)不畏浮云遮望眼
——王安石的言志诗
1.《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峰”亦作“山”)
介甫24岁时登进士第,任淮南判官二年,入汴京,未求馆职,直接分配郢县任知县。此诗即作于此时。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试比较太白《登金陵凤凰台》,老杜的《望岳》,毛泽东《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蒋中正《励志》:“腾腾杀气满全球”鲁迅《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2.《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此诗作于晚年,豪情尽失,亦包含其对当时毁誉不一之慨叹)
荆公自熙宁十年(1077)57岁回江宁起,至元祐元年(1086)66岁逝世为止,十年间一直在钟山半山园过着隐居生活。这首《读史》当作于此时。虽曰“读史”,实是自况,以“高贤”自诩,谓将来史书亦必“岂尽高贤意”,唯“独守千秋纸上尘”,一任后人评说而已。
鲁迅《题呐喊》诗云:“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亦谓己多骂名,凭此小说,或可让后代有心人读懂自己的心境也。
(二)爵位自高言尽废
——王安石的翻案诗
1.《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此诗作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介甫年39岁)似为以后罢相之谶也!
陈衍《宋诗菁华录》:“‘低徊’二句,言汉帝之犹有眼力,胜于神宗;‘意态’句言人不易知。‘可怜’句用意忠厚,末言君恩之不可恃。‘汉恩’二句即‘与我善者为善人’意,本普通公理,说得太露耳。”二诗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此诗其二有“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之叹)
2.《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谊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的身世,千古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同情,或叹息歌咏,介甫此诗却独特异议,认为贾谊的主张能得到汉文帝的采纳,施行了自己的谋略与建议,比起历史上许多身居高位而其谋略却被放置的达官贵人,应该是幸运的。)
《汉书·贾谊传》:“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李白《田园言怀》:“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弔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李义山《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弔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梁王,汉文帝之子-梁怀王刘胜)“哭泣情怀”指《治安策》“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三)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晚年谪居南京时的闲适诗
1.《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容斋随笔》续笔卷八谓“绿”字先后为“到”“过”“入”“满”)
此诗写作时间,向有四说:
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48岁,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
②熙宁七年(1074)四月,54岁,第一次罢相,知江宁府,途经瓜洲。(我持此说)
③熙宁八年(1075)二月,55岁,第二次拜相,赴京途经瓜洲。
④熙宁九年(1076)十月,56岁,辞相,判江宁府,途经瓜洲。
2.《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北山,即钟山,周颙隐处,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屈子《九章·思美文》:“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
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径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笙歌。”
曾季狸《艇斋诗话》:“荆公绝句云‘细数’云云,东湖(徐师川的)晚年绝句云:‘细数李花那可数,缓行芳草步因迟’。自题云:‘荆公绝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窃取之邪?学诗者不可不辨。予谓东湖之诗,因荆公之诗触类而长,所谓举一隅三隅反者也。非偶似之,亦非窃取之。”
3.《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宋诗菁华录》:末二语恰是自己身分。
《石遗室诗话》卷十七:“读荆公集竟,摘句如下(略)。皆山林气重,而时觉黯然销魂者,所以虽作宰相,终为诗人也。”

熊盛元 字复初,号晦窗主人,笔名郁云,网名梅云,一九四九年元夕生,江西剑邑人。江右诗社社长,《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江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师从毗陵吕小薇先生学诗古文辞。诗学樊南,词宗花外。有《静安词探微》《晦窗吟稿》《晦窗诗话》《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民国词卷)等。

编辑/章雪芳 审核/小楼听雨 校对/冯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