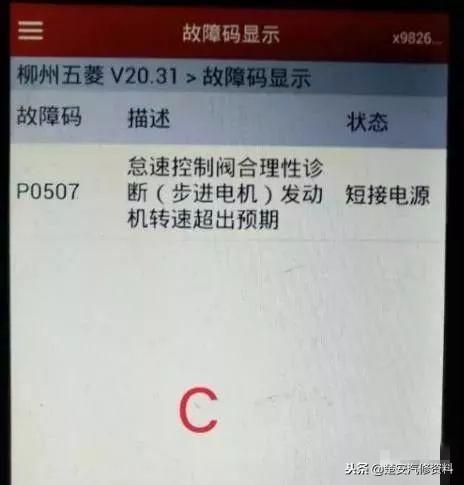黄有韬(左一)和友人合影。
7月21日,柳川诗社己亥年会暨黄有韬的《神笔飞扬——二黄散板名家点评集》《二黄散板·戊戌卷》首发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及乐清本土诗人或诗歌爱好者共二百余人参加首发式。今年73岁的黄有韬自13岁开始写诗,整整六十年,创作了30000多首诗、词、曲。他的诗作在全国400多家市级以上的诗刊、报刊发表,并在美国《纽约时报》等21个国家的报刊、诗刊上发表,他的诗词纵横捭阖,气象壮阔,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笔锋所及,五彩缤纷。
少年初识诗滋味
黄有韬出生在北白象镇三房村,因为诗写得好,黄有韬成为当年农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说起写诗,黄有韬说是他当年的班主任陈立诚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十三岁时开始写诗,当年年少的他看到夏收夏种热闹的劳动场景,在脑海里蹦出几句诗,就写在作文本上,老师根本不相信,这诗出自少年之手,经再三核实后,老师将黄有韬写的诗寄到上海的《少年文艺》。令黄有韬没有想到的是,这首诗很快就发表了。
“当时《少年文艺》主编胡绳给我写信,很可惜,与胡先生及其他老师的通信因为老房子的一把火都被烧为灰烬。只记得他跟我说要坚持写诗,要再接再厉。这首很稚嫩的诗的发表,对我鼓励非常大。”正是众多老师的鼓励成就了他的诗情。
诗作发表后,成为黄有韬学习写诗的动力,他向村里的老先生黄允中请教,老先生指出了这首诗在平仄、对仗等方面不足,并拿出了一本诗韵词典。有韬、允中老先生及附近寺庙里的一位老道长,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诗词。黄有韬写诗后,他们几个进行了修改,从平仄、用词等方面都是相互进行了探讨。整整三年多时间,黄有韬非常努力地学写诗,平时,他看《三言二拍》《红楼梦》等小说时,都将书中的诗抄下来,慢慢地品味,慢慢地学。
渐渐地,他的诗越来越成熟,他将诗寄到了《广州日报》副刊,没有想到,深得时任编辑周克光先生的赏识,他的诗多次在副刊上刊发,周克光先生还向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推荐了黄有韬,王季思先生对这位温州老乡也是加倍地栽培,黄有韬将诗写成后,寄给了王季思先生,王先生将诗改后,重新誊写一份发到《广州日报》,将修改稿重新寄给黄有韬,“在王先生的指导下,我的散曲进步非常快,我们交往了几十年,直至王先生去世。”黄有韬说起在诗意的路上,许许多多老师对他的提携和帮助,“我把诗作寄给夏承焘先生,夏先生给我改过诗稿。”
借助诗成业务多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有韬诗在全国小有名气,《当代诗词》《诗词》《中国诗书画》等诗刊和报纸发表了他的诗作,他还以诗为媒介,做成了一笔笔业务,这在诗界颇为传奇。
当年,黄有韬像很多乐清人一样,成为供销大军中的一员,有一次他到四川成都金堂县一家国营企业接业务,他一过去,供销科张科长对他不理不睬,并明确地告诉他,他们单位用的产品都是国营企业生产的,不用民办企业的产品,说完后,张科长看看报、喝喝茶,无视黄有韬的存在,跑了五次,全是这种情景。第六次,黄有韬又上门,看见张科长拿着了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他将头伸过来看看,见他又来,张科长心里很不舒服:“你看得懂吗?”“我指出你的几个问题,你这首的韵律和平仄都不对。”张科长非常纳闷,供销员也懂诗?接着,黄有韬自报家门,自己是四川诗词学会的理事,《岷峨诗稿》《四川诗词》经常发表诗作,并当场指出了该首诗中的几个错误,张科长当场拜他为师。当他再一次来这家企业时,张科长拿出当年要采购电器的单子说:“你自己挑吧。”这家企业每月业务量都有好几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业务。
“我发现爱诗的人挺多的。”黄有韬的另一个经历是在四川广汉市高骈镇,认识了一位姓曾的老先生,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两人喝茶、喝酒、读诗,因为诗缩短了两人的距离,两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经曾先生介绍,该市105家企业,黄有韬与101家企业有业务联系。
黄有韬说自己接业务时,请客吃饭不多,经常是在谈诗、吟诗中,接下了一笔笔业务,有一家企业的一位工程师为黄有韬解决了一个质量上的难题,当黄有韬要答谢他时,该工程师却说:“你为我写一首诗吧。”“后来这首诗在泰国的《星暹日报》上刊发。”黄有韬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直言品说显风格
黄有韬两大爱好,就是写诗和喝酒,他强调自己是一个农民,他说话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善恶明辨,闻善倾赞,嫉恶如仇。
有一次,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水利部原副总工程师欧阳鹤教授来温州,因为共同的爱好,黄有韬成为当时的接待人之一,诗人们在一起时,当场吟诗作对。谁知欧阳先生吟诵了一句七言诗后,黄有韬却指出,欧阳先生的这句诗需要修改一下或重新写一句,听到此时,大家面面相觑,欧阳先生听后拉着黄有韬的手:“这几十年里,没有人说我的作品不行,你是第一个,你这个朋友我必须交。”此后的十几年的春节,黄有韬都会收到欧阳先生寄来的明信片,开头总是写着“黄有韬诗友新春快乐。”有问候的,也有他的诗作。
在黄有韬看来,写诗必须真实。有一次,四川省里的一位领导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云锁祁连风劲吹”这么一句有诗意的诗,黄有韬竟然认为该诗句违反自然规律,风如果劲吹的话云就不会锁住,直至将诗句改成“雾锁祁连风止”后,他才作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浙江省诗词学会成立,当黄有韬听说学会经费紧张时,当即表示,诗刊首刊的钱由自己及同乡黄永强一起出,当时出了1000元。在随后的大会上,常务副会长叶元章表扬黄有韬两人,说温州人财大气粗,这在一般人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黄有韬一听,当即跑到主席台上,当着大家的面,跟叶先生说:“我没什么钱,出钱是因为喜欢诗,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诗。”叶先生一听,当即向黄有韬表示歉意,叶先生对敢于说真话的黄有韬非常钦佩。后来,叶元章先生为温岭诗人林崇增的诗集写序时,特别用较多的笔墨写到诗坛“浙南现象”代表人物黄有韬。
在浙江诗界,还流传一段佳话:在某次盛会上,有领导请其代作诗词,他不但断然拒绝,还作诗嘲之曰:“云间明月好三分,无赖官员占半轮。独有风骚清洁地,难容伪巧拍山君。”
“浙南现象”点评多
黄有韬说自己也不清楚有多少首诗刊发在诗刊,也不清楚自己的诗获得过多少个奖项,他多次成为诗词比赛的终审评委。他担任乐清市诗词学会正副会长20年,他担任柳川诗社社长期间,他与社员共有5人成为中镇诗社社员,作为一个镇级社团在全国也很罕见。
写诗填词赋曲60年,有两件事让黄有韬至今津津乐道,第一件事就是2011年11月,由重庆市诗词学会、“东方诗风”论坛和重庆技术职业学院诗词学会联合主办的“黄有韬诗词恳谈会”在重庆日报社举行。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陆大献、《银河系》诗刊执行主编黄兴邦、《作家视野》编辑张华和双桥区诗词学会、江津《几江》诗刊和初春二月文学社的代表等40多人应邀出席恳谈会。十几位发言者对黄有韬诗词继承我国自《诗经》以来所产生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敏锐地反映时代,有力地针砭时弊,给予高度评论,称赞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重庆日报》《重庆国诗》《东方诗风》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专题报道,一些网站等对黄有韬的诗及其现象进行了讨论,许多诗友向黄有韬求书。后来,林宏安先生将这些评论及平时读黄有韬诗评结集出版,书名为《神笔飞扬——二黄散板名家点评集》。
另一件事就是我国诗坛名宿叶元章、熊鉴先生先后提出了当代诗坛的“浙南现象”:高度赞扬浙南有一大批中青年诗人,敢于直面人生,吟诵出一大批振聋发聩的诗作,黄有韬作为“浙南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备受关注。
熊鉴先生对其评价:“我心中深刻感受到黄兄诗篇中对社会、对人生、对大众、对友人的热爱与真情,还有他敏锐的头脑、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历和得心应手的诗词造诣,尤是他那份蕴藏在作品中的挚情。”
在他的《二黄散板集》里处处可见他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他对民族的爱、对山河的爱、对苍生的爱、对朋友的爱,无不激昂于胸间,奔涌于笔底。
诗因生巧熟尤佳
当记者问起,30000多首诗,他是如何保持热情,如何有题材每天高效地写诗,黄有韬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熟能生巧。”
黄有韬的诗词作品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其朋友张荣辉对其的评价非常中肯:从国内外新闻大事、历史人物典故,到身边所见所闻,大到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小到身边的小花小草小虫,远到几千年之前几万里之外,近到眼皮底下衣袖旁边,嬉笑怒骂,无所不有。更难得的是他的作品看似随手拈来,其实都意境高远,内涵丰富。有人曾“讥”黄有韬是“造诗机器”,虽然不无想“讥”他写诗数量多、速度快之意,但这也说明了黄有韬过人的诗词创作能力,还有作为一般诗人所没有的,捕捉各种题材的超常敏感力,对各种事物储存的知识力,综合分析时下和情化各种人物诗词意境的构建能力,以及炼字构词造句的驾驭能力。其诗词作品中,对诗词创作各种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可以说是娴熟至随心所欲,令人叹为观止。赋比兴手法比比皆是,使得看似枯燥的时政话题或琐碎的生活小事,在诗词中一样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黄有韬的诗带有很明显的时代印记,他的诗语就是当下的时代语言,如写《特朗普宣布美从叙利亚撤军》:“反恐之时竟撤兵,管它战火正频仍。终教华府招非议,利益当前失弟兄。”一个平常人讲都讲不清的话题,竟可以用诗笔如此调侃。
又如他回忆当年跑业务做生意的生涯,通过描述既有辛酸泪又使人喷饭的故事:“广汉骑车抵什邡,迎风沐雨苦奔忙。向男施主分三五,对女同胞递凤凰。我以香烟开话匣,佛需檀樾贴金装。十年巴蜀淘金客,辛辣诗风满肚肠。”每一句诗看似都很平常,却从侧面写出了自己生活经历,令人回味。
如今,黄有韬每天将自己的诗作写了发给朋友,一天最多的达十来首。他说,写诗其实并不难,他经常开讲座并定期在柳市实验中学、白象中学、柳市老年大学、柳川诗词沙龙进行诗词知识的授课和指导,提高学员的创作热情和技巧,吸引更多的诗词爱好者加入诗词创作队伍中。有了诗和远方,生活因此变得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