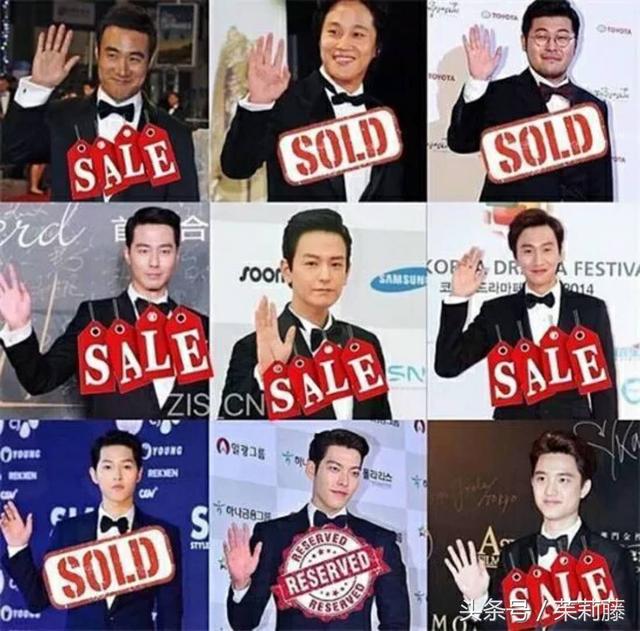时间轻轻一笔,便已划过一百年。回首望时,那个风云际会,文化融汇,新旧之交的二十世纪初,主张个性解放人性张扬的新文化运动正酝酿着狂风暴雨般的时代浪潮。无数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新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冲击着旧有的文化体系。站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无论是谁,都会情不自禁心潮起伏,汹涌澎拜,恨不得打开所有的窗户与大门,任那些叫嚣着有无限可能的新事物完全冲进来,来彻底颠覆整个世界。
巨浪面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纪元是如此陌生,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选择,而且,他们还有了如此多可以自由表达和发挥的机会:天高海阔,鸟飞鱼跃……这一切,都化成了对新知识,新理念、新文化的渴望。于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业凭借这股强劲风浪,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晚清的书籍主要采用古籍形式,样式延续传统的线装书,内容上也以文言文为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加之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传入,在1909年到1919年的十年间,以白话文为主的阅读需求量剧增,每年出版的杂志、书籍从百余种一下发展到上万种。新的语言,新的阅读方式、新的阅读群体、新的阅读目标,都促生着新的书籍装帧方式出现。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文士参与制作书籍的传统,在出版业“暴起”之时,这样的传统也得到了继承。蔡元培、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叶圣陶、周作人、郑振铎等文化名人,曾多次为自己或朋友的作品设计封面。而其中,以鲁迅成就最为突出,风格也最具代表性。
从1909年鲁迅设计《域外小说集》开始,便和书籍装帧结下了浓厚的缘分,他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自己作品进行装帧设计的第一人,一生更是亲力亲为,参与设计的书刊封面多达60多个。鲁迅曾对陶元庆说:
钱君陶《我对鲁迅的回忆》:
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
既觉老套,势必革新。于是,他对中国旧的书籍设计面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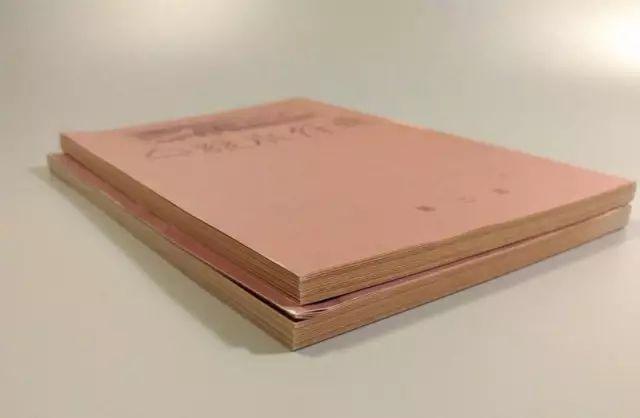
《域外小说集》
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已经印制得特别考究,封面用的是一种蓝色的“罗沙纸”(青灰色的磁青纸),书页则采用国外的毛边纸。上方的横幅图案画的是文艺女神缪斯在日将破晓的微光中弹奏竖琴。整个装帧看上去朴实、雅致、富有古意。

鲁迅的一些关于版式的想法至今仍被沿用,有的甚至成为书籍版式设计的定规,如文章题目占有一定的行数并与正文空开,每篇文章另页开始,逗号、句号等标点不占行首等等。
整体:明确而自觉的设计意识作为中国现代装帧艺术设计第一人的鲁迅,对于书籍装帧,首先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对书籍在排版、印刷、纸张、开本、装订、插图、装饰、甚至价格制定上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整体的观赏性与书籍本身的深度结合。鲁迅将书籍内容连同装帧看做一个完整的作品呈现方式,这注定他的格局,将远比同时代作者来得广阔。
他总是习惯于细心推敲、反复琢磨。即使是字体的大小、文字的样式、标点的位置,文字内容的校对,他都会从整体出发,以达到编排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开本而言,他编的刊物不仅有通行的32开本(如《莽原》半月刊)和16开本(如《朝花周刊》),也有25开本,如《奔流》《萌芽月刊》;而《译文》则是23开本。
黄源《鲁迅先生与〈译文〉》:
现在的杂志都是16开本,我们来个23开本吧。
23开本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给人方正厚实的分量感。同样为23开的还有他自费印的《毁灭》《铁流》,采用重磅道林纸印,毛边,横排,再配上厚布纹纸作封面,更显得大方、庄严、肃重。《朝花小集》则是狭长的40开本,便于携带和随时阅读,特别适宜于篇幅不大的小品集。为纪念自己最好的朋友瞿秋白,鲁迅特地自费在日本印制其译文集《海上述林》以求达到最佳印刷效果,此书分皮脊麻布面精装和绒面精装两种,都烫金字——鲁迅在书籍装帧上的郑重与讲究,无疑体现着他身为设计师的“细节控”。
他曾设计过两本儿童书籍《小约翰》与《小彼得》,在封面设计上,都选择富有装饰意味,深具童趣的元素作为视觉中心。特别是荷兰望·霭覃的童话《小约翰》,实际上1926年,孙福熙已经为这本书绘制了一个封面,为一个裸体的幼儿,从海边的山脚下朝着月亮奔去。但显然鲁迅对这个设计不是很满意,等到再版时,他选用勃伦斯的《妖精与小鸟》作为封面图案,并手写了“小约翰”三个生动活泼的字体,整本书的装帧给人感觉于是更轻松愉悦,更贴近儿童视野,也更具天真浪漫、清新温婉的童话风味。这正是鲁迅对整本书做过认真的研读推敲后,才能深刻体悟到的形神完美结合。

《小彼得》封面 1929年
圆形图案中是一棵姿态优美的蒲公英。作者为德国著名漫画家乔治·格罗斯。鲁迅非常欣赏他的政治漫画。
《小约翰》封面 1926年 孙福熙设计
《小约翰》1929年 鲁迅重新设计
另一更广为人称赞的封面佳作是鲁迅1923年为自己小说集《呐喊》设计的。暗红色的书面纸,仿佛是血迹的隐喻。黑底白字,字的四周则是细细的白线框子。这种镂空、阴文形式,外加细线框装饰效果,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的印章;细细一看,却不由得感到阴暗压抑,让人生出“铁屋子”的联想。最具设计感的,还是他精心打磨过的“呐喊”二字:两个偏旁“口”偏上,喊字右半部分的“口”刻意居下,三个上宽下窄的“口”,组成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加强了标题文字的象形功能,正如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张开嘴,发出发自内心的呐喊。如此简洁有力、意味深长的设计,绝对是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呐喊·自序》
留白:现代感与东方神韵的结合陈丹青曾说:
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
在五四作家群体中,恐怕唯有鲁迅担得起这番称誉。他高超的美术素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中国文化传统的从小的熏陶。
鲁迅自幼就喜欢美术,并自觉地进行美术训练。作为一个敏感而又有着艺术方面天赋的孩子,爱美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于是在《朝花夕拾》等许多描述童年记忆的散文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他充满柔情回忆起自己对于图画的渴望,周作人回忆道: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五·避难》:
鲁迅小时候也随意自画人物,在院子里矮墙上画有尖嘴鸡爪的雷公,荆川纸小册子上也画过“射死八斤”的漫画……鲁迅买了这明公纸来,一张张的描写……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
正因为这份由传统的民间文化所培养出的审美,使得鲁迅的装帧设计自带一股“书卷气”。同时,他对书籍的现代性又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喜爱抽象、有力、凝练的事物,追求形式感。这两者体现在书籍装帧中便是他非常注重空间与留白。鲁迅曾说:
鲁迅《忽然想到·二》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用,“余裕”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
最能代表他“留白”构思的,是他为自己设计的许多杂文集,封面白底黑字,偶尔加盖一枚朱文印章,黑白红所构成的效果便足够凝练醒目了。1926年,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杂文集《华盖集》。封面上只有三行字,书名几乎上移到了封面最上方的六分之一处,与最下方的出版年限拉出了极大的空白。在方正的“华盖集”三字上方最顶端处,则是“鲁迅”两个字的拉丁文拼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元素。如此大胆的打破视觉规则,鲁迅要营造的不仅是现实环境的逼仄感,还有一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感。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的。”
——《华盖集·题记》
1927年《华盖集续编》出版,书籍装帧以第一本为基础,咋一看几乎一模一样,但稍一留意,便可发现“华盖集”三字下方醒目的加盖了一个四十五度斜角的红色“印章”——“续编”。可谓既古朴,又具书章的文化底蕴,更见力度和用心。在当时彩色印刷条件很差,基本只能进行两色印刷的情况下,鲁迅因地制宜对极少元素的把控,非常有东方式的“极简”禅意,今人看来,也不禁拍案叫绝。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集》中的杂文具有浓浓的传统士人意味的讽刺,鲁迅极简的封面,也透露着同样的气韵。
除了书法、印章设计的封面外,鲁迅也追求传统笔墨的手效果。其含蓄、稳重、空灵的风格,具有强烈的东方式韵味和情调。
1923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北大歌谣周刊》请鲁迅画个封面,有人请教他封面用什么颜色,他笑着说:
常惠《回忆鲁迅先生》: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
这句柴世宗对御窑瓷器的批示,一直代表着传统文化对颜色的审美追求,鲁迅无疑是认同那“雨过天晴”的迷蒙空灵之美的。
整个封面左上角和右下角采用不同颜色,只简单的勾勒着淡淡的闲云和夜暮天空的轮廓,大面积留白突出了那轮斜月。幽雅、清新、典雅的气韵扑面而来。据常惠回忆,这套书是木版印刷,把封面画底稿贴在木板上再刻,因此原稿的精神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封面比鲁迅所绘差了很多,但我们也可感受其留白理念。
留白:现代感与东方神韵的结合鲁迅在评及陶元庆的作品时曾评价
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这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并且非常看重书籍装帧设计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气韵,他一生也在这方面做了最多的尝试和探索。
从1915年至1918年里,鲁迅搜集、购买了大量的碑帖拓片和古籍插图,并带着学人的严谨细致,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不仅临摹汉魏六朝的碑帖文字, 甚至把墓志上的纹饰也临摹下来。在鲁迅的日记里,也经常能够看到“录碑”、“整理拓片”的记载,并将不同的拓片作对照。后来,他也把这些石刻的纹样运用到了书籍装帧设计之中。1923年,鲁迅翻译出版了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在纹饰上用汉画人物、流云组成带状图案,和“桃色的云”高度切合,更有一种灵动雍容的传统之类。
在1926年出版的《心的探险》中,他同样采用六朝人墓门画像图做书面,青灰色的底纹,云朵以及腾飞于云间的龙铺满了整个画面,而一群小鬼,则围绕着“心的探险”做跃跃欲试状。《心的探险》中,所强调的个人内心的挣扎撕裂,
鲁迅《<乌合丛书>与<未名丛刊>》:
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苦痛的战叫。
在封面中就呼之欲出了。
鲁迅在目录页注明为“掠取六朝人墓门画像”,很可能这些图案并非采自一处,而是许多同时代墓门画像重加组合而成。但其布局精密,构思精巧,让人印象深刻。
但鲁迅对“民族性”的强调并非刻意,更多是他用世界性的眼光进行“拿来主义”的结果。他强调把“引入世界上灿烂的新作”和“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融入书籍装帧设计领域,因此,不仅大量借鉴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对浮世绘和欧洲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介绍表现主义画家蒙克以及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的作品,对立体派、未来派、构成派也都有关照。尤其推崇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在封面设计中大量使用欧洲木刻版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装帧设计呈现出鲜明的“中西合璧”风格。鲁迅正是在对多元化的追求中确定并寻找“民族性”的。
1934年,鲁迅编选了11位苏联版画家作品59幅。淡黄色的底,红色的木刻,黑色的书脊,不仅使用了其常用的“印章”元素,色彩搭配也非常具有传统气息,整体装饰突出了线装书的格调。但木刻作者的名字却是西文的。整本书体现了鲁迅对艺术“兼容并蓄”的态度。
鲁迅并非专业的设计师,在设计领域只是小试牛刀而已。他之所以向刚刚兴起的装帧设计投去深深的注视,是因为对他这样自觉的“启蒙者”来说,书籍的装帧设计和内容一样,都属于“文化启蒙”中的一部分。在百花之中,无非是“春兰”“秋菊”的方式差别而已。早年他与同乡许寿裳、经亨颐、蒋智由等26人共同联名撰写《绍兴同乡公函》中,就已经有对日本工艺美术能“救国”的关注,
试一入日本工艺美术各学校中,其深漆,其调(雕)刻,其锻冶,又若刺绣,若织物,若染色物,皆日新月异,精益求精。而又若造纸(今日新发明用木料造纸),若铜板,若写真,若制皮诸事,无不尽工极巧,日有进步。
将工艺纳入“中华振兴”视野中的思路,终鲁迅一生也并未改变。鲁迅曾说:
鲁迅《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
1913年,在教育部工作的他,写了一篇《意见书》谈美术的作用,强调除一般的教化作用外,人们要更多地看重审美,纯粹的文化静观会给人带来快慰。鲁迅始终认为,工艺(包括今日所说的设计)与工业、与人们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工艺之美可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进人的心灵世界中,这就是作为书籍装帧设计的“启蒙”之途,也是鲁迅作为设计师超越性的艺术视野所在。
陈丹青在1998年参观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的西方世界第一次中国美术大展时,看到了鲁迅的几件装帧设计,连连感叹道
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
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
这也是今天我们翻开那个时代的书籍时,同样会产生的惊异感。可以说,鲁迅在奠定中国装帧艺术格局上发挥的作用,仍因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低估乃至掩盖——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一流书籍装帧设计师。
《奔流》 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的文艺期刊,1928年创刊。
第一期的设计看似很简单,鲁迅把功夫主要花在了“奔流”这两个美术字上,这两个字的笔画仿佛一条条畅通渠道,有直通到底的,有四散放射的,有阻断迂回的,仿佛是动荡变化中的社会激流,“奔流”的感觉扑面而来。
两地书 1933年,鲁迅将自己与许广平的通信集结集出版。
封面为炒米色布纹纸,墨绿色字体,书名为刻字。依然是23开毛边本,简洁、朴素、大气的封面布局犹如一个信封,是极简设计的范本之作。
《而已集》 1928年的《而已集》是鲁迅第四本杂文集,
鲁迅的设计一向以简洁、低成本为主,因此他非常注重字体设计。这几个字也是鲁迅自己设计的自由美术体,非常有趣味性。
花边文学 《花边文学》是鲁迅的第四本杂文集。
鲁迅的杂文在《自由谈》上发表时常被围以花边以示重要,且围绕“花边文学”发生过论战(廖沫沙写过《论“花边文学”》)。他以此为书名,却保持了一贯简洁的封面风格,只在封面居中位置竖行排印书名及作者名,外围却围以《自由谈》式的花边。既有寓意,又富有装饰美。
彗星 鲁迅相当喜爱这个几颗小星加上彗星的木刻图案,一生曾多次在杂志和书籍上使用,只是排版都不一样。
在此使用,仿佛寓意着本书作者作品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许这个图案对他有特殊的情感意义吧~~
毁灭 本书描写的是苏联内战时一支游击队的故事,充满了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
鲁迅的设计凸显了肃重感,出版时间下面的线是本书画龙点睛之作,仿佛是在计算着历史一样的厚重深刻,又寄寓了作者内心无限的情感和期待。
萌芽 以扶持新文学青年作品为主的《萌芽》,1930年月刊。
除了鲁迅一贯的简洁风格、醒目风格外,比起鲁迅其他的字体设计,“萌芽月刊”字体的变形更年轻化,更“萌”,更富有亲和力,针对群体明显较为年轻。
艺术论 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由鲁迅翻译,1929年出版。
因为是理论书籍,鲁迅在封面设计时采用了较为抽象的图案,在中上部设计了一个圆形图案,两种颜色的虚实相间,盈缺互见不只是有意还是无意,但都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感觉,这可能更多出自鲁迅的独特触觉吧。双线描的“艺术论”三个美术字体部分嵌入,似乎暗示了这是一本谈“艺术规律”的书籍。这个封面更体现了鲁迅对于艺术一种直觉式的感悟。
文艺研究 1930年刊印的《文艺研究》杂志。
虽然仍采用大型美术字体组合占据主要空间的方法,但这次在字列转角下方设一不完全的弄堂门洞,里面密集的建筑隐约可现,似乎是寄予了鲁迅借《文艺研究》欲探求文艺的规律,但又窥而不得,有所缺憾的探索心理,别有韵味。
萧伯纳在上海 1933年,鲁迅为《萧伯纳在上海〉〉设计封面。
其设计上又运用了新的设计技法,用各种报道萧伯纳来上海的报纸拼组成书籍的封面,并且用赭红色来印刷,既装饰了书籍的封面,又烘托了气氛,使其一目了然,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上方黑色的书名和左上角线描的萧伯纳漫画头像,增加了封面的趣味性,并点明了本书的主题。这种创新的设计技法,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