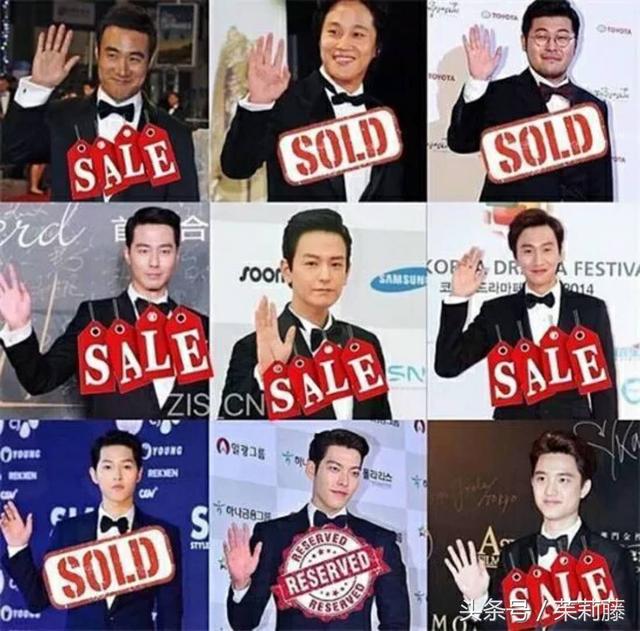郭沫若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经由陈独秀、胡适发起和开展。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可以说没什么作为。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期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创造社开始提倡文学革命,他们在文学革命运动要算到了第二个阶段。前一期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树人着重在向旧文学进攻,这一期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却着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郭沫若认为“我们眼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指出“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第二义才是形式的革命。”这就是说胡适等侧重从语言,形式方面为文学寻找突破口,而郭沫若所领导的创造社所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意识的革命”。从郭沫若早期的《女神》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到创造社后期,中国的社会呈现出了一个“剧变”,创造社也就又来了一个“剧变”。“新锐斗士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由日本回来,以清醒的唯物辨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郭沫若既然已赶不上文学革命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他就准备在第二个阶段即文学革命的建设时期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努力要争取在提倡“革命文学”的阶段取得主导的地位;表现之一,就是对文学革命第一阶段的批判,以及对自己所做的“意识的革命”的标榜。

鲁迅
创造社的转变,自“五卅运动”的前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自从创造社引入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便开始介入“革命文学”中,他们在“文学革命”中表现出极端宗派主义的倾向。首先,从理论上郭沫若表现出“惟我独尊”的姿态,郭沫若将文学简单的划分为两种,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我们应该说凡是革命的文学就是应该受赞美的文学,而凡是反革命的文学便应该受反对的文学。应该受反对的文学我们可以根本否认他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简切的说它不是文学。”“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郭沫若的这些观点表现出革命的狂热和褊狭。这种褊狭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郭沫若同鲁迅的论战。
郭沫若指责鲁迅所领导的“丝社”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1928年2月25日,《文化批判》第二期,李初梨提出“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文章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钱杏chun说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不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就是鲁迅他自己也走到了尽头。”“完全变成了落伍者,没有阶级的意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他对于革命和革命文艺,态度是异常的不庄严。”更有郭沫若化名“杜荃”,给鲁迅戴了诸多的大帽子,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在鲁郭的论战中,创造社成员极力褒扬郭沫若,打击鲁迅。冯乃超提出“只有郭沫若一人是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把鲁迅、叶圣陶以及从创造社分离出去的郁达夫、张资平算作小资产阶级,说“他们的历史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

郭沫若
鲁郭的论战,体现了郭沫若在“文学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利用“革命文学”的口号向第一阶段的先锋鲁迅,以及在第二阶段仍有影响的鲁迅的地位进行挑战。鲁迅曾作诗“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尽,春兰秋菊不同时。”表现了对世事艰危的世态下,革命文学却处于分裂状态的苦恼和惋惜。其实,在鲁郭论战之前,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路线,向旧社会进攻。”郭沫若在著作中也有与鲁迅联合的表示,但由于种种原因,二人的愿望没能实现。而鲁郭的论战不可阻遏地爆发了,鲁迅遭到了空前的“围剿”。
然而鲁迅和郭沫若的论战最终还必须完结,或者二人都会有一点因为未决胜负而带来的遗憾,但历史已不容许这两位文化巨人完成这淋漓酣畅的论战了。鲁迅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处境窘迫,或许已有休战的念头,怎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得不屡屡出动刀枪。恰好这时,鲁迅被作为革命文化的领袖,以领导文化战线的工作,而郭沫若的创造社正是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由于形势需要,在共产党的干预下鲁郭论战结束。郭沫若迅速改变态度,表示“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级,同立在一个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