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下文简称陀翁)的《穷人》中,多布罗谢洛娃曾给杰武什金一本书,并提醒杰武什金读一读《外套》。杰武什金看过之后却感到极为不满,他说:他那样写,只不过是我们日常平庸生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而已。由此,《外套》和《穷人》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这也是我们进行对比的一个重要基础。
陀翁曾说,他所有小说都是从《外套》中孕育出来的。这话或有夸大之嫌,但用在《穷人》这部作品上却非常适合。《穷人》的题材没有超出《外套》,主人公的形象、追求、所处环境都极为相似。当然,陀翁在继承《外套》的同时,还极为艺术地在结构形态和主人公意识方面做出了发展。事实上,巴赫金的“对话—独白”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

《穷人》封面
下面以《外套》和《穷人》为例,分三部分讨论陀翁对果戈里小说的继承以及陀翁作品的对话性和开放性。
一、《穷人》在题材方面对《外套》的继承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穷人》属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写作传统。这一传统由普希金开创,在果戈里和陀翁那里得到重要发展。《穷人》中主人公杰武什金的身份、地位、个人追求都和《外套》极为相似,这是陀翁对果戈里的继承。
1. 亚卡基耶维奇和杰武什金的身份地位
《外套》中的亚卡基耶维奇是一个九品文官,许多年来总是“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干着抄写的工作。他特别忠于职守,简直是怀着爱心在工作,仿佛在抄写中能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升职加薪,甚至得不到比他年幼的同事们的尊重,小说中这样写道:
年轻的官员们,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房东大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说房东太太打他,问他们多咱结婚,又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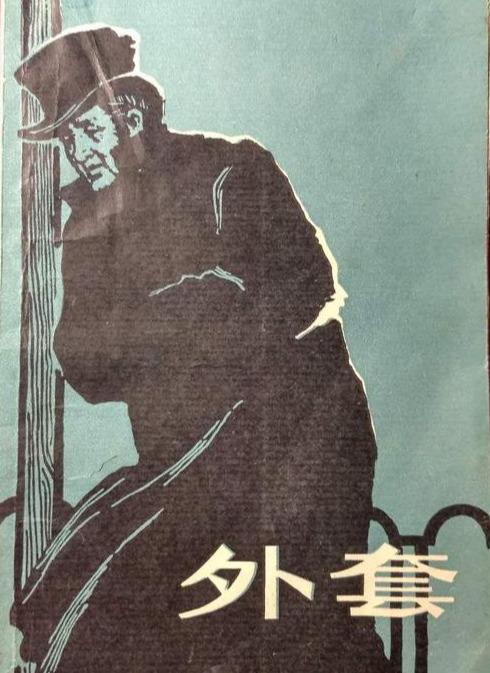
《外套》封面
《穷人》中的杰武什金同样是一个九品文官,同样孜孜不倦地干着抄写的工作。他和亚卡基耶维奇一样对抄写工作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当然这可能是出于无奈。但不管怎么说,故事中的他已经干了整整三十年。可是,他也同样得不到尊重。在给多布罗谢洛娃的信中,杰武什金便曾这样倾诉道:
他们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几乎把我当成骂人的代名词。我什么都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挑剔我的靴子,指责我的制服,说我的头发,甚至我的身材;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得重来。
2. 亚卡基耶维奇和杰武什金的追求
在《外套》中,亚卡基耶维奇的所有追求集中到了一件外套身上。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外套能为他抵御彼得堡冬天的酷寒。从精神的角度来讲,外套能为他维持最后的一点体面。
为了得到一件新外套,亚卡基耶维奇不仅花光了多面的积蓄,还“取消晚间的一顿茶,夜里不点蜡烛”。感到饥饿之时,他便用“外套”这个精神食粮来抵御。长此以往,“外套”不再是一件外套,而是变成了一个将陪他度过终身的女伴。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因丢失外套而死去,甚至在死去之后变为鬼魂。

《外套》插图
在《穷人》中,杰武什金则把自己所有的追求放到了多布罗谢洛娃身上。对杰武什金来说,多布罗谢洛娃就是他的“外套”。
为了帮助贫困的多布罗谢洛娃,杰武什金用尽了自己的积蓄,不得不从更为舒适的住宅区搬到了她所在的贫民区。即使自己的生活已经极为艰难,他也不惜用仅有的钱财为她买礼物,带她去看电影。他不惜将礼服卖掉,牺牲自己仅有的体面。
但即使是这样,他依然留不住她。在小说的结尾,多布罗谢洛娃似乎要永远离开他。而他,或许也将像亚卡基耶维奇一样失去自己外套。
二、《穷人》叙事的开放性《外套》的结构是封闭的,在果戈里的叙述之下,亚卡基耶维奇的一生一览无余,没有别的可能性。但是《穷人》的结构却是开放的,在故事的结尾作者并未给出明确的结局。不仅如此,陀翁还通过波克罗夫斯基、老波克罗夫斯基、高尔什科夫的故事,展现了人生不同时段的一些可能。
《外套》中亚卡基耶维奇因外套被抢受气而死,即使之后他化为鬼魂残留人间,这悲惨的事实也得不到改变。但在《穷人》的结尾,陀翁虽然制造出了多布罗谢洛娃将要离开杰武什金的氛围,但却没有明确给出结果。

《穷人》插图
我们可以认为多布罗谢洛娃离开了杰武什金,杰武什金像亚卡基耶维奇一样死去了,而他的魂灵永远留在了她曾居住过的屋子里。我们也可以认为,她离开了他,但他却没有死去。我们还可以认为,她最终留了下来,和他生活在了一起,或是并没有和他生活在一起。总之,故事是开放的。
事实上,《穷人》叙事的开放性并不仅仅体现在结尾处,还体现在波克罗夫斯基、老波克罗夫斯基、高尔什科夫几个人的小故事中。他们三个人都和主人公杰武什金一样,出身卑微、有一定知识、生活艰难,命运虽然相似却又有较大不同。他们这三个处于人生不同时期的小人物,其实可以理解为对“杰武什金命运到底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
故事中的波克罗夫斯基是一个非常贫穷的青年人,健康状况不好,无法继续求学。他过着简朴安静的生活,走路时显得很笨拙,鞠躬行礼时也笨手笨脚。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非常善良,令人尊重的人。多布罗谢洛娃称他为“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好的人”,杰武什金何尝不是一个像他一样对她好的人?

陀翁
但是好人没能得到好报,波克罗夫斯基不幸过早离世,多布罗谢洛娃的不幸也从此开始。青年波克罗夫斯基的命运,会是杰武什金的命运吗?杰武什金离开了这个世界,多布罗谢洛娃开始了自己一段更为不幸的生活。
故事中的高尔什科夫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文官,七年前被开除公职,过得比杰武什金还要落魄。不过家里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高尔什科夫最后赢得了一大笔钱,但忽然却不幸逝世。高尔什科夫暗示着杰武什金命运的另一种可能:多布罗谢洛娃将和杰武什金生活在一起,但贫困的他们不会过得幸福。
故事中的老波克罗夫斯是波克罗夫斯的父亲,曾在某个地方任职,因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只能在机关里做最低等、最不重要的工作。发妻死后,他将儿子送给了别人收养。儿子长大了,而他则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这也是杰武什金命运的一种可能。
三、《穷人》的对话性在《外套》中,果戈里具有绝对的叙事权威,主人公的外貌、心理、性格和行为都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但在《穷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具备叙事权威,他以书信体的形式将作者的完全隐藏起来了。不仅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故意展现出了主人公叙事的不可靠性。主人公最终拥有了足够的主体性,作品亦因之拥有了区别于作者独白的对话性质。

果戈里
1. 书信体具有的对话性
《穷人》由54封信件组成,叙述者不是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主人公多布罗谢洛娃和杰武什金。《外套》中的亚卡基耶维奇是由作者呈现的,主人公完全受作者控制。《穷人》中的多布罗谢洛娃和杰武什金当然也受到作者控制,但他们并不是由作者呈现的,而是由自己呈现的。又因为书信体的缘故,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带有一种对话性质。
多布罗谢洛娃和杰武什金通过书信的方式交谈,一步步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展现在对方面前,同时也将之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叙述方式的好处绝不仅仅在于真实性,还在于主人公的主动性。受与对话者关系的影响,主人公有可能并且也有必要选择性地叙述关于自己的故事。
在《穷人》中,前期的杰武什金绝不谈及自身的经济状况,也不谈及对贫民区居住环境的不满。当然,聪明的多布罗谢洛娃是清楚地知道事实的真相的。但是,她也没有对杰武什金说出自己所有的忧虑。要不然,她就不会答应贝科夫的求婚。也就是说,多布罗谢洛娃并不确信杰武什金的爱能拯救自己。之前的她,只是需要他的爱 。
因此,对话理论除了巴赫金看重的必然性、布伯强调的平等性和伯姆强调的创造性之外,还具有极为明显的选择性。

对话理论的提出者巴赫金
2. 不可靠叙述加强了主人公的自主意识
书信体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变式,在陀翁之前就有许多大作家创作过书信体小说,如卢梭的《新爱洛依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题材的创造在于,通过主人公的不可靠叙述加强主人公的自主意识。
在《穷人》中,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主人公的自主意识。如杰武什金虽然遭到他人的屈辱,但他却并不感觉自己低人一等,他认为:一个人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就从不依赖别人……这块面包是我劳动所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享用它。又如杰武什金看到果戈里的《外套》,不满地说道:这是一本怀有恶意的书,瓦莲卡,简直不符合情理。又如多布罗谢洛娃面对艰难选择之时,对杰武什金这样说道:我不是在征询您的建议,我要独自一人想清楚这事。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杰武什金生活得到改善之后,他给多布罗谢洛娃的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和拉塔扎耶夫已和好,我心里高兴就主动跑去找他了。他的确是个好人,宝贝儿,那些说他的坏话都是胡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一切都是恶意诽谤,他压根没有打算写我们的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这容易让我们怀疑杰武什金之前的叙述有多少不可靠的地方,但这种不可靠性却也加强了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所知有限的他,如果说的一切都是客观事实,那反而是不真实的。由此,《穷人》最终成为了一部不同于作者独白性质的对话小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