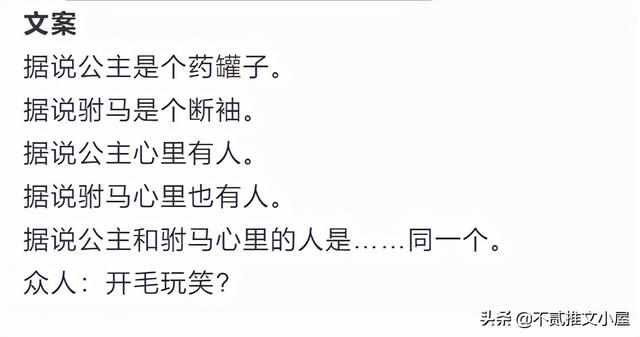吴钩
拜《水浒传》与《金瓶梅》所赐,潘金莲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荡妇。但是,对潘金莲背后的历史知识,你却未必了解,也许还会误信传闻。让我来问几个问题吧。

【1】
第一个问题:以武大郞卖“炊饼”(馒头)的收入,能够养活潘金莲这个美女老婆,住着二层小楼房吗?
从历史看,宋代的城市底层市民,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做小买卖,日收入一般都是100文~300文钱。那么这个收入水平可以维持怎么样的生活呢?
按照宋代的物价,一个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
【2】
第二个问题:潘金莲后来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如果潘金莲并没毒杀亲夫武大郞,只是与西门庆通奸,那按宋代的法律,会受到什么处罚?
我们看小说、戏剧,总以为古代妇女与人通奸,会被判处什么“骑木驴”、“浸猪笼”之类的酷刑,其实这多出于民间小文人的杜撰。虽然个别地方确实发生过将奸夫奸妇“骑木驴”、“浸猪笼”的事情,但那不过是落后、封闭之地的私刑而已,既为主流社会所反对,也为法律所禁止;国家正刑中从来没有什么“骑木驴”、“浸猪笼”。根据《宋刑统》,“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奸的男女将被判处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则徒二年。
但实际执行的处罚,还要更轻一些。因为宋朝创设“折杖法”,除了死刑之外,流刑﹑徒刑﹑杖刑﹑笞刑在实际执行时均折成杖刑。根据宋朝“折杖法”,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如果没有发生毒杀武大郞的情节,单按通奸罪量刑的话,二人会被判“徒二年”之刑,折脊杖十七,即打脊背各十七下就可释放了。

【3】
第三个问题:脊杖十七会不会将潘金莲与西门庆活活打死?
我们从电视剧画面看到的水火棍,又粗又长,绝对可能打死人。但宋代用于行刑的常行杖,其实并没有这么粗,也没有那么长,法律规定常行杖“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并且“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行刑的执法人员不能停下来歇口气再打。应该说,一般情况下,杖刑是不会致命的,脊杖十七不致要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命。
宋人自己认为,折杖法的推行,是轻刑化的体现,一洗五代时期刑法之苛严,使“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

【4】
第四个问题:假设武大郞一日回家,发现潘金莲与西门庆正“滚床单”,他一怒之下,当场杀了奸夫淫妇。武大郞用不用对此负刑事责任?
我们经常听人说,古时捉奸在床,当场杀死无罪。其实,这样的法律规定,只存在于秦汉—魏晋时期,又在元、明、清时恢复,如元朝的律法规定,“诸夫获妻奸,妻拒捕,杀之无罪。……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明清刑律也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这样的立法,无异于赤裸裸鼓励亲夫将通奸的奸夫与奸妇一并杀死。
但是,唐宋法律却无类似的规定。换言之,在武大郞生活的宋代,国家法律并不承认亲夫有什么“捉奸在床、当场杀死”的权利。假设武大郞杀了奸夫奸妇,就必须负杀人的刑事责任。

【5】
第五个问题:发现西门庆与潘金莲有奸情的小郓哥,能不能跑到衙门去检举,然后衙门捉住奸夫奸妇治罪。
根据宋朝的立法,小郓哥不具有诉权,即使跑去检控了,衙门也不会受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妇女与他人通奸,法院要不要立案,以妇女之丈夫的意见为准。从表面看,这一立法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却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益的保护,以免女性被外人控告犯奸。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属于亲告罪,受害人(丈夫)亲告乃论,政府与其他人都没有诉权。
宋代的“奸从夫捕”立法,其实是一条良法,被元人废除了非常可惜。为什么说它是良法呢,我讲一个《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故事你就理解了。
南宋理宗朝,平江府(今苏州)有一名道士,被人检控与平民李高的妻子通奸,案子送到两浙西路提刑司那里,提刑官胡颖作出终审判决:被告的道士“必其素行有亏”,才会受到控告,“自人必贪财也,然后人疑其为盗;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为淫”。然后,胡颖笔锋一转,说:“但在法:诸奸,许夫捕。今李高既未有词,则官司不必自为多事。” 既然通奸案的受害者李高没有提出诉讼,旁人就不必多管闲事,法院也不必受理。
元朝时,“奸从夫捕”的旧法被宣布作废,元廷颁下新法:今后四邻若发现有人通奸,准许捉奸,“许诸人首捉到官,取问明白”,本夫、奸妇、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强制本夫与奸妇离婚。从此,人民群众心底的“捉奸精神”被激发了出来,涌现了很多被坊间小文人津津乐道的捉奸故事。

【6】
第六个问题:那么“奸从夫捕”的立法,又会不会给男人滥用诉权、诬告妻子大开方便之门呢?
应该说,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不过,《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另一个判例显示,宋朝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已经注意到防范男性滥用“奸从夫捕”的诉权。
宋理宗时,有一个叫江滨臾的平民,因为妻子虞氏得罪他母亲,意欲休掉虞氏,便寻了个理由,将妻子告上法庭,“而所诉之事,又是与人私通”。法官胡颖受理了此案,并判江虞二人离婚,因为虞氏受到通奸的指控,“有何面目复归其家”?肯定无法再与丈夫、家婆相处。虞氏自己也“自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
但是,胡颖同时又反驳了通奸的指控,并惩罚了原告江滨臾:“在法,奸从夫捕,谓其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江滨臾乃以暧昧之事,诬执其妻,使官司何从为据?”判处江滨臾“勘杖八十”,即杖八十,缓期执行。
从法官胡颖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宋时,丈夫要起诉妻子犯奸,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有明确的奸夫,“形状显著,有可捕之人”。这一起诉门槛,应该可以将大部分诬告挡之法庭门外。
现在,你应该看出来了,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潘金莲的故事,而是宋朝的司法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