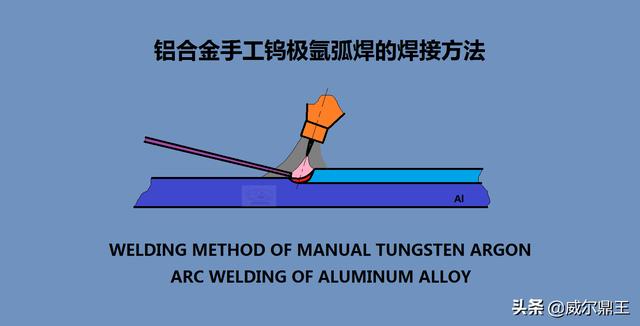三位女知青在水利工地劳动的情景
难忘在君山农场当知青的岁月
潘兵役
1972年的阳春三月,我们贮木场知青在万众瞩目下乘着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那天,岳阳城区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大街小巷挤满了人,都在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随处可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大有作为”“上山下乡光荣”等横幅标语。说实在话,这情景,比“老三届”的哥哥姐姐们好像是热闹多了,政府成立了知青办,开始重视知青工作。
载着知青的汽车在欢庆的锣鼓声中缓缓开动,我们经过最热闹的火车站、南正街、岳阳楼,汽车行驶到岳阳北门渡口停下,此时一辆辆的汽车像巨型长龙一样,井然有序等待轮渡船。
望着眼前的洞庭湖,我们从此与她结下不解之缘。
省贮木场知青和铁中知青分配在君山农场二分场,贮木场知青分在二队和四队。据说那天,岳阳、长沙知青共6000多人抵达君山农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国营君山农场就是不一样。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分场有独立的机耕队,开渠犁田基本上都是机械化。田地像豆腐块似的很平整,田里的作物看不到尽头。
我们生产队中心有个不大的礼堂(我们的食堂也在此)。队上的欢迎仪式在此举行,蒋芝新支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到每月有工资18元,但要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按劳分配,工资不保底不封顶,年底还有分红。这是在激励和刺激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愣小子,感觉勤奋才是硬道理。
生产队长熊绍尧同志介绍了二队的基本情况,以种棉花为主,有少量水田。生产队地处农场灌渠北面的北闸(也就是现在的旅游金滩的位置)叫新河二队,临近长江,汛期有防汛任务。
知青住的房子非常简陋, 隔墙是用芦苇秆隔的,女生两间房,男生两间房,中间住着一位生产队的黄姓队长。二队分配知青共20人,男知青12人,女知青8人。分配生产一组知青6人,我被分配在一组,生产小组长是老农黄希林同志。
去后不久,正值油菜待收,黄希林老人家手把手地教我们,对我们要求极严。黄组长虽年过半百,但精力旺盛,使不完的劲,在劳动中生活上从不鄙视我们。
三四月正是春意盎然的季节,但阴雨绵绵,史书说“春寒料峭,冻杀年少”,江风寒冷袭人,知青与贫下中农仍一起下地播棉籽种,虽说是机械化播种,有时覆土未完全盖上,需人工覆土。不生长缺苗是常有的事,须用培育棉种营养钵补苗。培育水田秧苗,推广小苗带土移栽。经过近两个月的锻炼,可能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入乡随俗,很快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慢慢地习惯早出晚归了。 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我光荣地加入了团组织。
每年的“双抢”是农村抢季节的重头戏。四五点钟生产队长就敲起了钟,各生产小组长的口哨不停地屋前屋后来回吹。起床简单地漱口洗脸,跟着他们来到5里开外的黄泥套水田开始拔秧插秧,8点钟回来吃早餐后,马上接着去棉田地打农药。虽然 “双抢”时间不长,但对于十六七岁正在长身体的男女知青来讲,还是有些吃不消。
生活像万花筒一样,有笑有哭,当然也有有趣的花絮:有一天,知青中几个较调皮好动的同学,用门板长条椅搭起临近屋檐高的一个台子,王同学拉起了二胡,男女知青同学齐声引吭高歌,场景好不热闹,也同时吸引不少村民观看。当时知青即被广泛流传的一首《知青之歌》(当时属禁封的)所感染,大家真的动情地唱哭了,不一会阴转晴,情绪化的我们又唱起一首首革命歌曲,自娱自乐,正达到高潮时,“嘭”的一声,整个台子突然垮了,在上面几个蹦、跳、唱的“主角”也摔了下来,还好都没事,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就这样谢幕了。
在农场时间一长,陆续有举荐工农兵学员或招工的,马同学就是第一个被推荐上技校读书的。我虽然被贫下中农多次推荐,但是基本上都不是我满意的去处,先是分场的机耕队的拖拉机手,招工君山纸厂,我的心还是想回家想回城,对生产队党支部的好意婉言谢绝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君山农场人基本上都知道黄泥套工程、二五工程。
那年的冬季,在黄泥套工地上垦荒,我们分场北临长江,地处农场最北端,可想湖区的北风是何等厉害。让人感觉得特别的湿冷,寒风刺骨,手脚冻得冰凉,我们知青男女硬是与贫下中农一起同甘共苦,战严寒磨意志,经过数月的硬战,在芦苇荡中造出了百亩良田,我们知青也是付出了艰辛的汗水!

知青回到君山与新河二队原党支书记和现任党支部委员合影
1974年的冬天又是一个冬修季。
规模宏大的“二五工程”是当年学大寨的成果。农场李朗秋老领导和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掀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热潮,在岳华公路的两旁打造样板工程,既改造了良田,又兴修了水利,先后出动上万人的队伍。长长的岳华公路,红旗飘扬,高音喇叭唱起革命歌曲,鼓舞士气。早晨零下几度是常有的事,我们知青还好有长筒雨鞋,贫下中农是没有长筒雨鞋的,他们挽起裤脚站在刺骨的泥水中劳动。我们用麻绳编织的簸箕虽不黏土,但脚穿粘着沉重泥土的雨鞋,担着上百斤的担子,爬上45度高的坡还是相当吃力的。当时大家的那种热情,那种积极性,现在的人可能都想象不出来。
我是一个惜真情懂感情的人,很是怀念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怀念那里淳朴和善待我的父老乡亲。
大厨张六生,人称六哥,眼睛不大,脸上时常挂着笑容。四十岁还未娶亲(后来听说娶了媳妇,并生育一子)。一生一世很是坎坷和艰辛,一只手还有残疾,不能参加笨重的体力劳动,但很勤劳,很善良。我们虽不沾亲带故,但他对我关爱有加。刚去不久,我每次打饭,发现碗里饭下一个荷包蛋,内心感激,但也不敢声张,久而久之,这个秘密还是被知青同学发现。我招工回岳后,还走动了好多年。闻悉好人不幸意外去世,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只能默默地祈祷,天堂过得还好吗?
熊绍坤,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纯朴,谦虚而寡言,是我们队的机械修理工。不大的工作间,摆满了各种 待修的农用器具,打谷机、拌桶、 铁锨、风车、水车、犁、耙、犟、喷雾器、中耕器等等,在他手里没有修不好的农具。在这里不得不夸他的夫人许福,对下放知青的姓名,至今快50年了还清楚地记得,甚至还记得少部分家长的姓名。每次我们知青回到第二故乡访友时,都是由她们家热情款待,真的是情深意切,难能可贵。
浮云一别后,流水五十年,蓦然回首,感慨万千。五十年前,我们从风华正茂懵懵懂懂的毛小伙子,走过年富力强的中年,步进了两鬓斑白的老年,这是最难忘的一段人生。每年的3月14日是个特殊的日子,知青同学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活动。知青的时代虽已经过去了,但是知青的甜酸苦辣依旧在心里装着,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激情燃烧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