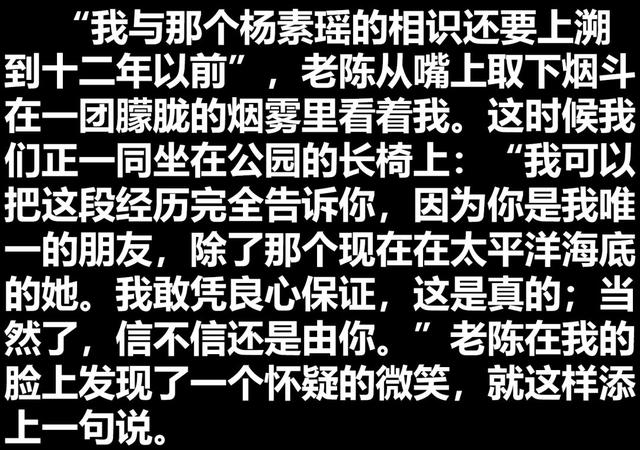旮旯村的徐寿星,这几年春风得意,百事顺心,就有一条儿不满意一一 年过四十,膝下无子。他寝食不安,犹如百爪搔心。
咋能不让人发急呢?你想,这高门大屋的四合院留给谁呢?城里那寿星药店谁来继承呢?百年之后谁领棺下墓摔老盆呢?不错,徐寿星有两个丫头片子,可闺女出嫁是人家的人,说得再好,十个花花女,不抵一个跛脚男。唉,我徐寿星没黑心烂肺,没卖假药坑人,咋积了个断子绝孙!
徐寿星发急,还有人比他更急。谁?他娘刘氏。徐家七代单传,延续到今天不容易。一根弦,不经弹。眼看儿子年过四十,没有子息。这根弦岂不眼睁睁就要断了?这叫我日后咋见我那早去的老头子?咋有脸去见二老公婆、列祖列宗?刘氏越想越揪心,整天唉声叹气,吃饭不香、睡觉不甜、茶饭日渐减少,最后竟绝食了。
儿媳秀英是个孝顺媳妇,见娘这样急得不知咋好,再问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
老太太心里也有一本帐:我说啥呢?还不是怪你光生闺女?你要是能给我生个孙子,我这病不治自好。可这话儿媳不能说,说了生分,伤人心。要是她呛自己几句:“俺娘啊,种麦出不来秫秫,这事儿,问您儿子去!”这岂不是疤菊眼照镜子——自找难看?
儿媳见套不出娘的话,再这样下去自己也担不了责任,就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徐寿星接了电话,撂下药店生意,开车回来了。
一进家先到老娘房里,见娘面朝里躺着,就坐到床面前,叫声:“娘,咋睡了?哪里不得劲儿?”
娘硬梆梆掷过一句:“我没劲的很!”
徐寿星见娘话里带气,更加倍陪着小心:“娘,是秀英惹你老人家生气了?”
“没有。”
“是怪我没常回来看你?”
“不是。”
“是吃饭不对味儿?”
娘摇摇头。
“是穿衣裳不合适?”
娘摆摆手。
“是想俺姐了,我捎信让她来?”
老太太又摇摇头。
“是想俺舅了,我开车去接他?”
老太太还是摆摆手。
这不是,那不是,徐寿星毛头了:“娘,你究竟因为啥?”
娘不答话,叫着儿子的小名反问道:“尿壶,你是装迷糊,还是真不知道?”
“娘,我真不知道。”
娘动气了:“你真是个孝顺孩子。我问你,不孝有三,以何为大?”
徐寿星豁然明白,挺为难地对娘说:“娘,想开点儿吧。你想孙子,我想儿子,不都是为了徐门有后吗?可我已经‘计划’了,为了有后,总不能让秀英‘那个’,让人捣脊梁沟子。”
刘氏不听倒罢,一听气从中来:“呸!亏你还是个男人,头上瞎顶四两羊毛!你不会生法子要一个?”
要孩子?徐寿星不是没想过。可如今男孩金贵,一时半晌上哪儿要去?
刘氏见儿子为难,继续点拨道:“我问你,你要钱干啥?你就不能花钱买一个?”
响鼓不用重槌敲,老娘一点,徐寿星恍然大悟:“娘,你放心,我经常出门在外,只要留意,迟早给你抱回个大胖孙子。只是,你老人家可得养好身子,别糟践自己。”
老人一听笑了。扑楞从床上坐起来:“儿子呀,你早这样说,娘哪还来的病呢?”
徐寿星见状,一块石头落地,高兴地喊:“秀英,快给咱娘做饭,咱娘饿了。”
秀英也挺高兴,甜甜地应了一声。不一会儿,饭端来了,刘氏扑扑棱棱扒了两碗面条,外加四个焦黄的荷包鸡蛋。
从此,徐寿屋生意之外又多了一项任务:要找儿子。
这一天,徐寿星要到大别山区吴家岗收购药材。在汽车站候车,这候车室虽说不大,却也人声喧嚷,热闹非凡。徐寿星拣一个位子坐下,一不小心背的挎包把邻坐碰了一下。
那人立即说道,“你小心点儿,别碰坏了孩子。"
徐寿星一看,见邻坐是一个三十不到,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那孩子眉清目秀,水水灵灵,正甜甜地睡着。
徐寿星满怀歉意地说道:“对不起,没吓着孩子吧?”一转眼,见孩子头上有一根草棍,他顺手捏起扔在地上。
小伙子瞟了他一眼,弯腰拣起草棍,又别在小孩的头上。
徐寿星不解地问;“小伙子,你怎么又把它别上了?”
小伙子笑了笑:“老大哥,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明知故问?”
徐寿星从戏文里知道头插草棍是自卖自身。于是,便知趣地问道:“这孩子莫非……”
那小伙子显出焦急的神情,神秘地答道:“嗯,是的。”
徐寿星情不禁地问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儿?”
“是个带把儿的。”
“哎呀,这么漂亮的孩子,你怎么舍得卖?”
“没法子呀,”小伙子叹了口气,“他妈产后得了不治之症,要花一大笔钱。眼下要顾大人,就顾不了孩子了。”
徐寿星深表同情,便也酸酸地问道:“这孩子要多少钱?”
“怎么,你想要?”
徐寿星点了点头。
“那好。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咱找个僻静地方唠唠。”说罢,起身就走。
徐寿星急忙紧跟在他的后边。来到一个僻静地方,先有一个女人等在那里,小伙子说:“他娘,这位大哥要孩子。”
女人没有说话,竟自伤心地哭了,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男人说:“你哭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看,这位大哥心眼挺好的, 不会亏待咱孩子。”又转身对徐寿星说:“大哥,你尽管放心,女人嘛心软,没事儿。”
徐寿星疑疑迟迟地问:“多少钱?”
“不要钱。”小伙子说,“一说价,我不成了卖孩子了?”
“那,我也不能白要你的孩子!”
“说得也是。那你就给个孕期费、抚养费吧。”
“好的。”
男人扭怩了一下:“不好意思。怀孕期间一天按八十块钱算吧,这二百八十天,二八一六,八八六四,两万二千四。”
“哎呀,怎么这么贵?”徐寿星叫起苦来。
小伙子说:“不贵。你出门在外,也该知道房价。像这样四季恒温,安全舒适的单间独房儿,何止八十块?你要同意,咱接着往下谈。”
徐寿星要看看他葫芦里卖啥药,狠了狠说道:“是不贵。你往下说吧。”
“好,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还有抚养费,一天按二十块,这一个月就是六百块。合计两万三千块。此外,还有精神损失费……”
“咋?还要精神损失费?”
“是呀。亲生骨肉给了别人,当父母的谁不心痛?哎呀,这精神损失费可是没价呀!别太少,给两万吧。”
徐寿星账头清楚,乖乖,四万三千块买个“屎爪爪”,不是讹人吗?“不要,要不起。”
“那你给个价。”
“一万!”
“一万?你是买个猪崽子?还是牵个驴驹子?这可是个活儿子,能顶门立户、扛幡子摔老盆的活儿子!”
徐寿星摇了摇头。
“怎么,还嫌贵?那就降价处理,零头不要,给四万块吧。”
“四万?两万也不要!”
“多少要?”
“一万五。多一分不添,少一分不去。”
那男人装出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样子,一咬牙:“卖给你!”徐寿星提出要验验孩子。
小伙子说:“这是自然。”
随即打开包,跃入徐寿星眼帘的果然是一个肉豆豆的,蚕蛹般的小JJ。
于是,这边数钞票,那边交孩子。徐寿星接过孩子,好不高兴!一万五千块买个儿子,值!要钱干啥?钱再多不会叫我爹,花了钱买个会叫爹的儿子,越想越高兴。他乘汽车,坐火车,连天加夜赶回旮旯村。
一进家门,自然合家欢喜。更有凑趣的人说:“尿壶哥,你得了个大胖小子, 这喜酒得喝!”
徐寿星咧嘴 说:“那还用说?喝!”
喝喜酒那天,更是热闹。七大姑、八大姨,妻侄小舅子都来了,一个庄的老少爷们更是不请自到。
这个抹灰,那个抹鞋油,徐寿星、秀英,连刘太太都抹得花狗脸样。
老太太好不高兴:嘿,不得孙子, 想抹还没人抹呢!
正在高兴,就听屋里一片声地嚷道:“毁了,毁了,小鸡鸡飞了!”徐寿星一扭头,一个粘糊糊的东西“啪”地一下叮在鼻尖上。
原来秀英给儿子换包布,徐寿星的丈母娘想逗逗外孙。用手一边拨拉小鸡鸡,一边说,“唔,您奶奶的小茶壶呢,给你奶奶泡壶好叶子茶。”
一拨拉,小鸡鸡竟粘在手上,一甩手,“嗖”地一下飞起来,不偏不斜正好飞到徐寿星的鼻子上。
霎时间胖小子变成秃妮子。那小鸡鸡呢?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尿一浸,时间一长,发软变粘,结果出了这么个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