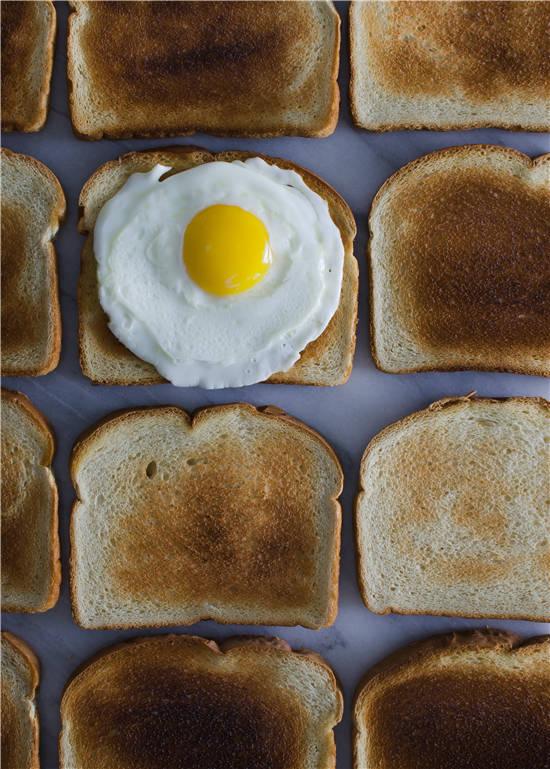(本文首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4日06版,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全文版)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里一个非常关键的范畴,早在先秦道家的哲学体系中即被赋予了至上本体的意义,但其意涵十分复杂,难以准确把握,故而《老子》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到了宋明理学,在由韩愈首倡、程朱发扬光大的儒学“道统”思想中,“道”主要是指儒家学术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而在具体的理学哲学思想中,道家的“道”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接纳,与“理”(或曰“天理”)这一理学基本范畴发生了关联并形成了较复杂的关系。
关于“理”,许慎于《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理”的本意是指对玉石的“剖析”打磨。到了后来,“理”具备了越来越丰富的哲学与伦理意蕴,并衍生出“天理”一词。这一意义的生成与衍化究竟始于何时,过程如何,笔者无从查考。但至少在《礼记》成书的时代,“理”于物理的意义之外就已经具备了较充分的伦理与哲理意义,并出现了“天理”的说法。如《礼记·乐记》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在此,“天理”即被明确为人的本体规定性,具备了强烈的伦理属性。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朱熹对之十分重视。按照陈荣捷先生的看法,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声意指分开,实际上应读去声,指义务、所得份、赋受。(《论朱熹与程颐之不同》)而朱熹对程颐所提出来的“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命题。如他说:“‘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此所谓“一实”即“理一”;“万分”乃“分殊”,为那“一理”在具体的万千事物中的分别体现。因此,总体来说,“理一分殊”的实质是“道德基本原理表现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具体规范中又贯穿着普遍原理。”(陈来,《宋明理学》)而对“理一分殊”与“道”、“理”这一组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则可依据朱熹对“理一分殊”在伦理与性理两个层面的演绎分别进行解析。
从伦理的层面看,朱熹说:“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六)朱熹所说的“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即“理一”,乃“统一的道德原则”(陈来语),与作为“统名”、“人所共由之路”的朱熹“道”“理”之辨中的“道”涵义基本相同。这一“统一的道德原则”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分”则是“细目”、“条理界瓣”,即“分殊”,为“不同的道德规范”,对应的是朱熹“道”“理”之辨中的“理”。
尔后朱熹又曾以太极观念从性理的层面继续解释“理一分殊”,他在《太极图说解》中道:“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对此陈来先生解释说:“朱熹认为,把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其中有一个太极,是这整个宇宙的本体、本性,这个太极是一。而就每一事物来看,每一事物都禀受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太极(理)作为自己的性理。”(《宋明理学》)太极为“本然之妙也”,即“天理”,“万物统体一太极”即是“理一”;“一物各具一太极”则为“分殊”。对照朱熹的“道”“理”之辨来看,前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乃作为“统名”、“人所共由之路”的“宏大”的“道”;后者是作为“细目”与“理脉”的“理”,在事物的具体性质与规律方面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其特殊性又并不妨碍事物在最高原理上的同一与统一。
综上可见,显然前述“道是统名,理是细目”的“道”“理”之辨与“理一分殊”的观点十分相似。但由于朱熹对“道”、“理”之间的关系论述不多,前者比起后者来就较少引起学者的注意,因而没能在学术史中盛行。
本文系儒风大家读者原创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作者简介:冯兵(1975—),男,重庆奉节人,哲学博士,国立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儒家礼学的哲学思想及朱子学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及台湾的《哲学与文化》《鹅湖》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传承者
中国风骨 天下情怀
中国孔子基金会战略合作伙伴 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请关注微信公号:儒风大家(rufengda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