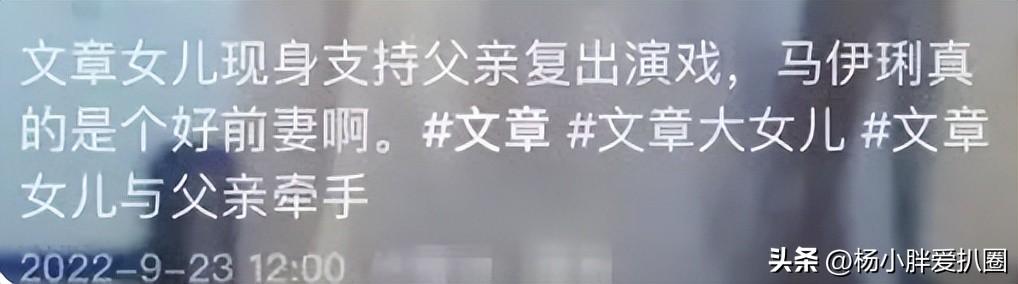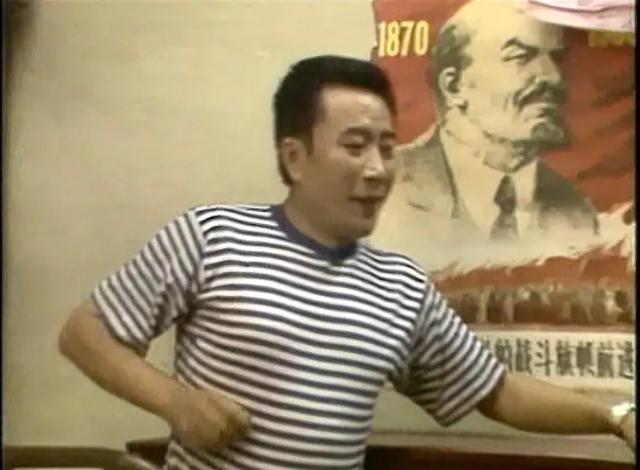楔子:崇祯六年腊月间, 中午时分, 浙江海宁府郊外野庙,朔雪漫卷,寒气袭人。
海宁府西北紫微山上,新科举人查伊璜约了三五好友来到紫薇山上赏雪饮酒,几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而上,江南的山虽不及五岳那样巍峨壮观,却也温婉可人,美艳秀丽的山林间点缀着片片白雪,别是一番风光。大家一路有说有笑,不知不觉登上了顶峰,只见一破烂的古庙映入眼帘,古庙千疮百孔,房门半掩。“冻云宵遍岭,素雪晓凝华。入牖千重碎,迎风一半斜。”查伊璜情不自禁道。“真可惜了好山却有个破庙,我们进去生火烧饭,寒雪配浊酒,能饮一杯否?”友人附和着。

“好主意,只是这庙大煞风景,我们几人不如出钱修缮一下,也算积功德一件。”说着几人走进了庙里。庙中最显眼的不是神像,而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铜钟,扣在地上,高约五尺,两臂不能合抱,钟身上下有手抓过的新痕,众人好奇,透过底部的缝隙,见里边有一小竹筐,筐内不知装有何物。“莫非是盗贼藏的金银珠宝?”一人好奇地打量着。
于是众人合力抓着钟耳上提,没曾想,铜钟纹丝不动。就在此时,进来一人,衣衫褴褛,但器宇不凡,坦胸露乳,但举止潇洒,天寒地冻,他却毫无惧色,说道:“拿我食物干甚?”说着一手掀钟,一手把讨来的饭菜倒进框里,轻松自在,一连掀了几次才把食物放完。众人惊诧不已,查伊璜对此人说:“先生天生神力,相貌堂堂,为何要做乞丐?”
来人答道:“俺饭量巨大,没有东家愿意聘俺!”查伊璜怜悯不已,带这位乞丐回家小住几天,好生招待,后觉得他是当兵的好料,等到来年开春,托人把乞丐送到兵马司参军去了,并赠碎银五十两。乞丐临走时,告诉查伊璜:“谢谢恩公!俺叫吴六奇,广东丰顺人,后会有期!”

康熙初年,查家无端遭遇飞来横祸。什么祸?
在湖州府南浔镇有一巨富人家,户主叫庄允城,是明末复社的会员。大儿子庄廷鑨大概三四十岁时,因为中了“疯疾”眼睛突然瞎了,瞎了就好好治病吧。但是这位秀才不向命运妥协,想要编写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史书流传于世。因为“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他也想留下“廷鑨失明,乃著《明史》”。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著史需要一定资料和文学功底的,这位秀才学问真不真不知道,但是家里就一个特点:穷,穷的只剩下钱。庄廷鑨先是向一个落魄的前朝宰相朱国桢后人买了本遗作《明史》,这位宰相在崇祯时去世的,所以记载的历史还差一丢丢,把它补上就完美了。庄廷鑨也是这样想的,聘请了当时的名士、大明时候的孝廉、贡生等十五六人代为润色,给了不菲的薪酬。
这些人都是大明的遗老遗少,写的话语自然对大清有点大不敬了,比方说称努尔哈赤为“贼”,大清为“夷”,所用年号均为大明或者南明年号,南明这时候虽然一直存在,但是皇帝已经从江苏跑到福建,再到广西最后出国了,整个天下是大清的。可以这样说这部书准备写的时候还是大明,写着写着变大清了。
庄廷鑨也在顺治十三年去世了,去世后他爹为了把儿子几十年的心愿完成,就拉来庄廷鑨的岳父也是南浔屈指一数的富豪朱侑明出资赞助,光看朱侑明的名字就觉得此人有点反动思想,两人聘请了最好的刻工雕刻母版,最好的刷匠负责印制。最后觉得这么精美的书籍,修订者署上先前的吴炎、潘柽章等人还不够分量,这两人虽说是大儒顾炎武的好朋友,但是名气还是小了点。

庄允城就把当时名气较大的査继佐(查伊璜)、陆圻、范骧加上了,不知道是缺钱了没有请这三人,还是请不动人家,毕竟这几人挺清高的,一般暴发户是很难与他们交往的。这部书就在这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行了,当时的江南读书人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皇帝每天很抑郁,自己的爱妃去世,所以就下令严加管束那些不安分的人:“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其投刺往来也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一句话,就是不要读书人聚众结社,又大兴江南科场案,打压江南士子的傲气。
顺治不这样做不行,南明小朝廷虽然不足为虑,但是占据台湾的郑成功已经率领十七万军队,浩浩荡荡地开赴长江口岸,攻下镇江,接着要打南京,浙江舟山的张煌言也连克皖南及苏南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南方的不安宁很快治好了顺治的抑郁,他对大臣们说,朕需不需要御驾亲征剿灭叛乱。鳌拜说,皇上只需管好读书人就行,剩下的交给臣子就行了。
就在江南的读书人闷在家里无聊时,一部大作《明史》出世了,里面的猛料很多,譬如南明弘光、鲁王时期的一些内幕,就好比路遥刚去世,《平凡的世界》就卖火了,二月河、流沙河、金庸一死,有关他们的传记就会争相购买,传抄誊阅。查继佐也买了一套,刚看了几页就发现了问题,这书有问题,早晚会出大事,就和陆圻、范骧商量对策,大家认为必须向官府举报,才能免于灾祸。三人结伴到学政衙门控诉,结果官府给他们留了个口供,大意是此书我们并没有参与编订,而是庄廷鑨自己擅自加上去的,便让他们回去了。

有读者会好奇,清朝不是对待文字异常苛刻吗?是的,但是庄家的《明史》是官方许可的,原来出版前庄允城就把摘录好的《明史》送给礼部、督察院相关人员审查过了的,有正规的手续。按理说事情到此为止,奈何人间不乏宵小之徒,蝇营狗苟之辈。第一个登场的是赵君松,湖州府中的一名教授,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长,也购买到了这部书,觉得升官的机会到了,就跑到学政衙门去告发这本书,学政一听非同小可,连忙调查,岂料老庄家神通广大、手眼通天,此事被上头压了下来。
蝇营狗苟,驱去复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赵君松见告状无功而返,把这个事告诉了朋友李廷枢,一个刚出狱的前督粮道,他因为索贿被判了斩监候,恰好赶上了顺治的爱妃董鄂妃生重病,顺治大赦天下,以积功德,他因此而出狱。命是保住了,但已经被抄家,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要赶快搞钱,同时思量着要为顺治帝做些什么以报大赦之恩,为了使这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一边跑到庄家敲诈一番,一边跑到湖州知府衙门告发庄允城。
事情的发展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庄允城对他不理不睬,绕过李廷枢,直接花钱买通了湖州知府,湖州知府知道南浔庄氏钱多就狠狠地敲一笔竹杠,让庄家把母版销毁,已经发行的统统焚烧,此案又不了了之。
第三个可怕的人物来了,叫吴之荣,李廷枢的亲家,前湖州府归安县(今湖州市区)知县,他和亲家李廷枢一同入狱,一同因为顺治大赦而放出来,和李廷枢得了同一种病——红眼病。当官当惯了,就很不习惯那种没权没势的日子,吴之荣就想如何能够立下奇功,官复原职。《明史》是个到手的肉,不能轻易放过。有两种办法:第一向南浔庄氏要钱,拿到钱运作官位;第二种向朝廷举报,朝廷有规定谁举报谁受益,至少可以分得庄家一半家产。
鉴于自己亲家的经历,吴之荣决定拿庄允城的亲家朱侑明开刀,庄家在南浔属于贵族之列,根基很深,但是朱侑明是靠鼎革之际,南方战乱,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而骤然暴富的,在江浙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因为庄廷鑨在修订《明史》隐去了朱国桢的名字,只缀上“南浔朱氏”,吴之荣提笔添了“侑明刊”,即成为“南浔朱氏侑明刊”,因为大部分《明史》都被庄允城回购销毁了,吴之荣手里的《明史》便成为了有力的证据。

起先,他跑到杭州将军衙门满人松奎那里告状,谁知松奎竟置之不理,说:“我系武职衙门,不便参与文字之事。”这样的结果让吴之荣大吃一惊,他原本想满人应该不会像汉人那样对此等事情冷漠无情,不曾想松奎更加的冷漠无情。原来,朱侑明在囤积物资时,与曾解救南京之围(郑成功攻打南京)的苏松提督梁化凤有过来往,他们拜托梁化凤向松奎求情。
不甘心的斗士吴之荣回到南浔,便向庄、朱两家摊牌,你们就给一丢丢的封口费,我就把我手里的《明史》全交给你,不再告状了。庄允城与朱侑明自恃有杭州将军,这个比总督还要大的大人物撑腰,对吴之荣讽刺挖苦,又派出家奴狂揍一顿,把他“礼送”出去了。
气愤不过的吴之荣走上了进京之路,在北京城散播小道消息“浙江南浔朱氏聚众谋反,并私刻谋逆书刊”。当时,南浔确实有过叛乱,就是《明史》的原始作者朱国桢的孙子起兵造反,不过已经被清廷镇压下去了,经过吴之荣一散播,传到鳌拜耳朵里了,他以为浙江又有人起兵造反,刚平定张苍水(张煌言),又冒出来朱侑明?
经过鳌拜的过问,兵部、刑部的介入,《明史》案发,已经是康熙二年,被砍者七十余人,编书的,印书的,卖书的,买书的,藏书的,凡是年满十六岁的都会被砍头,不满十六的流徙为奴,发配宁古塔者更是不下千人。査继佐、范骧、陆圻这三人,本是关在了刑部大牢,后来经过文章开头的“大力乞丐”后为“大力将军”的吴六奇的营救,不仅无罪,反而三人与吴之荣平分了南浔庄氏的财产(首告之功),一夜暴富,“孝廉(举人,指査继佐)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

也就是说,海宁查氏因为此案,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得到清廷的奖赏,查家从此夜夜笙歌,过上了花天酒地的大康生活。其实,“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査继佐自己在家里同样在写一部明史,命名为《明书》,庄廷鑨明史案后,他把书的名字改为《罪惟录》,出自孔子的“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历史总会有人记载,希望大家以后读到这段历史后,不要怪罪我写的不好。
他在《罪惟录》的自序中写道:“此书之作,始于甲申,成于壬子,中二十九年,寒暑晦明,风雨霜雪,舟车寝食,疾痛患难,水溢火焦,泥涂鼠齿,零落破损,整饬补修,手草易数十次,耳採经数千人,口哦而不闻声者几何件,掌示而不任舌者几何端,已较定哀之微词,倍极辛苦。”原来查先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冒着生命危险,不,是九族被诛的危险,把这段历史留下来了。

庄廷鑨的《明史辑略》因高调失传了,《罪惟录》流传至今,不是《罪惟录》恭维大清,而是査继佐在成书后一直秘不示人,连他的家仆都不曾见过,一直等了二百七十年,辛亥革命后,查家后人才拿出来,得以刻板发行。不止如此,査继佐的其他三本书籍《东山国语》、《鲁春秋》、《国寿录》主要记载晚明与南明皇帝与大臣的事迹,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书写的,所谓的“长宵开宴,垂帘张灯”只不过是掩护而已。
《东山国语》记录了大量抗清义士的事迹,这些抗清军队打着打着就散了,一部分将士心灰意冷,或隐匿家里不出门,或暂居深山古庙,削发为僧,査继佐利用自己有利的身份拜访这些将士,由他们口述牺牲同伴的事迹,自己记录,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史料。
《国语》中随手翻开一篇,譬如《江右语》写一个抗清义士傅鼎铨,兵败后被捕留下绝命诗:“当年隆主眷,去国动人思。潜确龙为蜇,鸣高凤正义。文山起义日,止水殉身日。城堞今垂尽,屏公与道期。”又留下绝笔铭文:“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求仁,庶毕吾事。”写毕,他“请衣冠北向再拜,仍索肩舆赴市。北师义而许之。挺立不可刑,复呼小椅,端坐而受刃。”
这类的场景,我们是否似曾相识,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那么一段感人的故事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值得注意的是,査继佐在文中称清兵为北师,似乎要比庄廷鑨的《明史》语气缓和些,然而记载的这些内容没有一篇不是被大清明令禁止的。

不得不提的是《东山国语》记录了张煌言被捕始末,以及他被捕后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动人故事,并记录张煌言的两首遗诗。第一首是他行刑前向清廷提出想要再游西湖,清廷答应后,游览时作诗:“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想丹心借一支。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另一首为绝命诗“我年适五九,乃遇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这两首诗与流传版本略有不同,笔者认为查继佐纪录的应为张煌言的原作。
《鲁春秋》记录鲁王监国(不方便称帝成为监国)时期的历史,査继佐本人就在鲁王手下做事,这本史书更是详细记载了郑成功和张煌言的抗清事迹,他的门人钱起介绍这本书是“至于削笔是非,出于作者独鉴,不赞一辞”,没有夸大和贬低这些抗清义士,把最真实的南明呈现给了后人。
查继佐与庄廷鑨几乎是同时创作明史,应该算是文人的一种反抗方式吧,难道他们真的没有相互来往?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两大家族(庄家号称“九龙”,一门有九个有学问的人)一个被抄家灭门,一个有惊无险,因祸得福,两者相比较,让人唏嘘不已,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这次査家幸运的躲过了《明史》案,六十年后却再度遭受了文字狱,这次的对手更强大——雍正,查家命运如何?又是如何起死回生的?且看下回。


(文/伯虎,根据历史文献改编,比正史有趣,比小说有料,张伯虎为您讲述历史人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