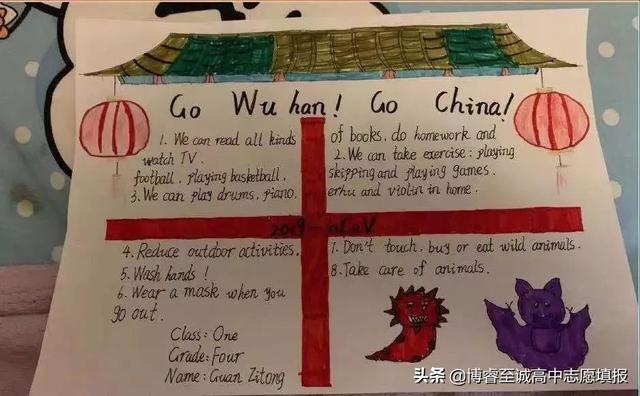“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威海话方言抬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威海话方言抬杠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自从“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国城乡各地公映后,解放军战士杨子荣打虎上山与土匪使用黑话对话的片段不仅扣人心弦,而且深入人心,经久不衰。一时间,不少的小孩都记住了那几句经典的对话,倒背如流,脱口而出。如果有谁不会讲上几句黑话,自己都不好意思在孩子群里混下去。
可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句黑话,已经不能满足孩子们对黑话的浓厚兴趣。在我们家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在孩子群里,偷偷流传开另外一种黑话,它比电影中那几句土匪黑话要复杂得多,不仅有趣,而且十分实用。
这种话又叫反话,反轨话,我们老家则叫“贼佬话”。它属于民间隐话,历史上主要用于帮会盗匪,起到保密作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贼佬话”开始流传民间,范围还比较广泛,在我们桂东南的岑溪、藤县、容县、北流、玉林等地也广为流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贼佬话”慢慢销声匿迹,特别在公共场合,基本没人使用。没想到电影中的土匪黑话,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沉寂多年的“贼佬话”,居然“死灰复燃”,悄悄地在小孩子中流传开来。在一些地方,孩子们不仅在玩耍时说“贼佬话”,到了学校,互相之间也用“贼佬话”来调侃或传递信息。
据我三弟回忆,当时他在浪水小学读书,小学生们使用“贼佬话”,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学校当然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作为校长的父亲,就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告诫学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神圣场所,不是土匪的山寨,也不是盗贼的老窝,绝对不能在校园里讲“贼佬话”,要确保校园教育环境的纯洁性。
虽然学生们在校园里不敢讲“贼佬话”了,可在私下玩耍的时候,还是经常使用的。毕竟一种语言能在民间流传开来,总有它的原因,开始可能是因为保密的需要,可一旦广泛流传,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它那种一般语言所无法代替的玩味添趣功能了。使用得当,不仅显其机智巧趣,还可增加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韵味无穷。
我是随父母下放回老家后才开始接触“贼佬话”的,算是“半路出家”,使用得不多,所以只是一知半解,加上小时候也没学好汉语拼音,连声母韵母都分不清楚。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打算,想把“贼佬话”的一些常识趣事介绍给读者,才忽然发现,这对我来说,基本上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两篇文章给了我启发,一是暾明写的《玉林话中的特殊音变现象—“反话”》,二是“旗哥有料到”写的《历史悠久的玉林贼佬话你知道吗》,虽然他们介绍的都是玉林的反话,与我们容县的“贼佬话”有所区别,但不少地方是相通的。有了这些材料的支持,我才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明知解释得肯定不准确不全面,可还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最初学的“贼佬话”,是最简单可又是最实用得那种,是单字反话,通过音变后,单音节会变成双音节,从而起到加密的作用,原来简单易懂的语句,会变得乱七八糟,不懂“贼佬话”得人听了,如同听外国人讲话一般,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这种音变很有规律,把第一个字的声母去掉,换成声母L,与这个字的韵母相拼,就得出第二个音节。比如“我”字,粤语拼音是“WO”,去掉W,换上L,就成了LO,读成了WO LO”我裸“。”地“字是DEI,去掉D,换上L,变成了LEI,读成了DEI LEI”地利”,“我地上山斩柴”(我们上山砍柴),就成了WO LO, DEI LEI, SOENG LENG, SAN LAAN,ZHAN LAN, CHAI LAI, 即:我裸,地利,上靓,山烂,斩蓝,柴赖。同样,如果说“晚上入屋偷鸡”就会说成是晚懒上靓入立屋碌偷楼鸡丽,如果从字面上看,还是有规律可循,可以破译,分析两个字一组,把第一个字都连起来就行了,可这不是文字,是语音,听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当然,这种变换方式,仅在我们村内使用,其他的地方,如浪水村,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听三弟和五弟讲了,我也弄不明白。还有玉林,变换的方法似乎更加复杂,他们使用的是li 型,将li破开或边音声母l和元音i,然后再变音,如“明”字,明Meg一legmi一铃眉,和原来的字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更复杂的另一种“贼佬话”,是以词为单位,转换后,原来的字都消失了,变成了新的词,所以更难破译,基本方法是原来字的声母不变,将两个字的韵母对调,组成两个不同的字。比如说“分离”,粤语发音是“fan 454 Li 232”,将韵母对调后,就变成了”飞轮”,发音是”fi 454 lan232”,“偷鸡”发音是tau gai,转换后成了tai gau,变成了“ 睇沟”,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原来的词义了。再比如:连队(雷电)、同志(地种)、修理(丝柳)、主人(准鱼)、柚子(夷早)、手指(史久)、手机(史沟)、风紧(分龚)、蒜头(秀团)、老子(李早)、吃粥(哭织)等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词都能转换。
还有三个字的词,转换时,一般只能选头尾两音节进行转化,收音机(史音沟)、柚子树(余子寿)、细佬哥(锁佬鸡)、红领巾(恨领公)、红花草(后花桶)、枸杞菜(盖杞套)等等,这种词受到的限制更大,所以用得最多的还是双音词。
“贼佬话”用途很广,它并不仅仅用于帮会盗匪,也可用于军事密码。
1917年,在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的一批军官,希望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马晓军在百色发动武装暴动,反抗旧桂系军官陆荣廷、谭浩明。但苦于和马晓军没有密码本联系,用明码发报又会泄露密,于是就决定用我们容县的反语给马晓军发报,电报全文如下:
“腊同蟹备统戚四羌苏半可理”。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字,即使被敌方截获,也根本无法破译。而容县人用反语来解读,就是”陆谭已败,请速相机宣布自立“,这里”陆谭“指陆荣廷和谭浩明,”相机”是“伺机“的意思。据说最后两字应该是”独立“,可一时找不到”独立“的反语,只好用”自立“二字替代。对这种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如此重大的事件,不应用其他的词义来代替,并且,对容县人来说,找到”独立“的反话似乎也不是太难的事。 独立——du lap——dap lu——耷录,所以估计电报的意思就是”自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贼佬话”并没有完全消失,还在民间继续流传,但使用的目的却起了根本的变化。
作为民间隐话,“贼佬话“可以起到警醒的作用。比如趁圩时,发现同伴身边有小偷伺机作案,想提醒同伴,又担心小偷会报复,就可以对同伴提醒说:身边有”嫂挑“,同伴一听就明白,”嫂挑”是小偷的反话,马上就会警觉起来,采取防范措施。
“贼佬话”也可以用来委婉表达某种厌恶别人的心情和用来嘲笑讽刺别人。比如有人的行为令你十分讨厌,你很想当面骂人,你就可以对他说:你真是只“狼毛”(流氓),你真是只“筮左”(傻仔),你真是条“否龚”(疯狗)。骂了人,出了恶气,被骂的人却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形容某人“佢好饮酒,日日饮得成斤”,单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表扬某人的酒量大:“他喜欢喝酒,每天都能喝一斤多酒”,实际上,”成斤“是”神经“的反语,不是表扬,而是嘲笑某人喝了酒后就胡言乱语,疯疯癫癫,是”神经佬“。
后来“贼佬话”还被人广泛用于山歌和谜语中。比如,有人出了这样一个案例,请你给出答案:
一男子被捉到派出所,问他犯了何罪,他回答说:“茅屋着火我泼水,一心只为我忧燃。”请问该男子到底犯了什么罪?
备选答案是:A.纵火,B.偷盗,C.杀人。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该男子说的似乎是这种意思:“茅屋着火了,我去泼水,因为我担心火会越烧越大”。所以不少人都会选A.纵火。其实关键词是“忧燃”两字,它是“牵牛”的反语,所以正确答案是B偷盗,他偷牛了。
从理论上来看,“贼佬话“或反语的各种切割转换,似乎十分复杂,没有相当的语音知识,很难运用自如。可实际上,能流利地运用“贼佬话”的人,都没有什么基本的音理知识,他们在转换的时候,甚至大脑都没有“分解综合,重换组装”的过程,而是瞬间就直接想到了结果,好像天生就具备了这种音变的技能,对某种语言,有着超人的天赋,生来具有,禀受于天。
我也算这种人吗?忽然,我都开始佩服起自己来了。
自得之余,却又有所担忧,这样一种特殊的语言,应该也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吧?政府是否可以出面加以收集、整理、利用?这种十分特殊的文化资源,一旦消亡或消失,就永远无法恢复和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