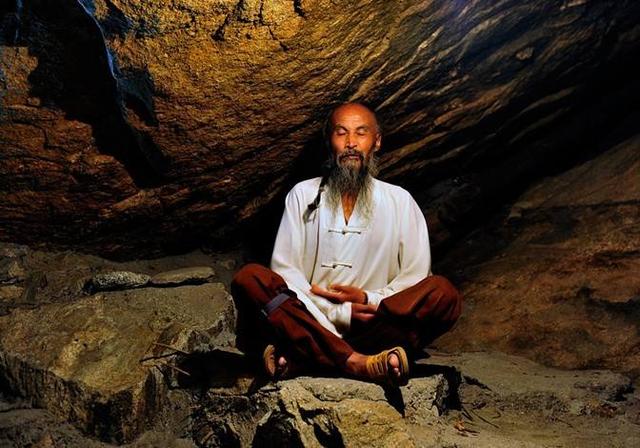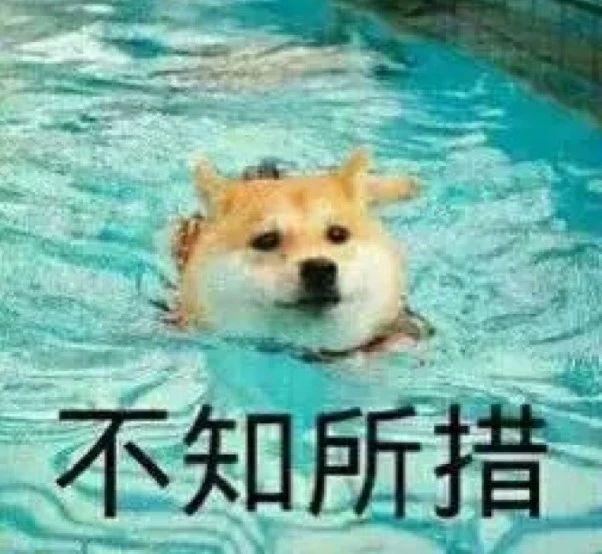一、什么叫“走西口”
“口”原是指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这些关口,当时称作“旱关”。此外,在晋蒙交界的黄河沿岸,当时还设有十六处“水关”,“水关”上设有“官渡”。走西口的人都必须从“官渡”过河,踏上去内蒙谋生的旅程。那时的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东的张家口为“东口”,大同以西的右玉县杀胡口(杀虎口)为“西口”,把长城以里的地区叫做“口里”,把长城以外的地区叫做“口外”,把内蒙古的西部地区叫做“西口外”,省称“西口”。这就是广义的“西口”。

走西口就是指长城以里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到长城以外的西部地区谋生的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明清中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在长城以里这一带的农民,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自然等原因,纷纷出走西口,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或经商做买卖为生。他们中大部分的人主要谋生手段是给西口外的地主“揽长工”“打短工”,其次是“下煤窑”或“跑河路”(指船夫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雁行客”(比喻他们像大雁一样春往秋归)。而少部分人在口外经商做买卖的,被称为“边商”“边客”或“族蒙商”。对上述外出谋生之路,口里人们称做“走西口”或者“跑口外”。
走西口前后经历大约三个世纪,在旧中国,走西口几乎成了忻州人一种共同的命运。人生代代无穷已,父亲走了,儿子又跟上了。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忻州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坐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他们用泪水、汗水、甚至血水,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创业悲歌!这场从内陆至塞外、从季节性至永久性的迁徙 ,从生活上解决了千百万移民的温饱问题 ,在艺术上产生了许多撼人心魄的艺术作品。这条本以生存为初衷的走西口之路 ,是一条成功者与失败者共同铺就的文明之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唱出了天下黄河第一曲,唱出了天下民歌第一曲《走西口》。
二、解读河曲民歌《走西口》
追溯河曲民歌的渊源,早在唐宋时就很流行。然而它真正盛行却在明末清初,缘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晋、陕、蒙三省交界处,东去的河水忽然向南折去,滔滔而下,河曲县因此而得名。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人俊音甜,到处可以听到动人的歌声,素有“民歌之海”的美称,真可谓“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
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内外交困,再加上连年遭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官粮租税重,逼的人跳火坑”“活活饿死人”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河曲民歌《走西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它通过一对新婚夫妇太春和玉莲缠缠绵绵、难舍难分的惜别,表现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丈夫被迫逃荒出走西口,夫妇那种纯朴、善良、火热、真挚的感情,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离死别的悲苦与近代忻州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走西口是对新环境的开拓,是对命运的挑战!
《走西口》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清朝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赔付外国列强的银两款项,加重税收,横征暴敛,大大加剧了对劳动人民的盘剥。人民要生存,要活下去,要么造反,要么就是出走他乡寻求活路。勤劳善良的忻州人选择了后者,他们只有走西口,去河套,开始前途未卜的生活。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出路,是最无奈的选择。正如河曲民歌中所唱:“梁头的狐子展不起腰,穷日子逼得哥哥走了河套”,“提起亲亲跑口外,泪蛋蛋流得泡一怀”,“你走西口我上房,手扳住烟囱泪汪汪”。这真挚而素淡的粗线条勾勒,给人们留下无限的联象空间,人们无不为这凄苦动人的惜别场面洒下同情的泪水。这是千千万万个走西口的哥哥与千千万万个留在家乡的妹妹心灵的撞击,是他们生死离别的千古绝唱!《走西口》以它极具自由洒脱的旋律和悠扬悲怆的歌声,倾诉了人生的艰难和离别的痛苦,从而使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民歌本身,成为记录一个时代民族生存状态的真实而鲜活的史诗。
《走西口》这首脍炙人口的民歌,以它那生活化的语言、苍凉而忧伤的调子、凄婉而缠绵的情思,承载着三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背井离乡的汉子们沉重的思念,也寄托着黄土高原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走西口的汉子们用这撕心裂肺的歌声,驱赶人生苦旅的寂寞,倾吐亲人离散的痛楚。这歌声穿越时空,向世人诉说着久远的悲伤。《走西口》吼出了多少黄土地上儿女们的辛酸,唱了几个世纪仍然长盛不衰,让多少铮铮铁汉泪水涟涟。这是黄土地上的儿女们用泪水和血水演绎的人生交响曲!
随着走西口历史的积淀与西口文化的成熟,民歌《走西口》后来逐渐形成了有清唱、对唱、男声、女声、表演唱、无伴奏合唱等多种演唱方式,并成为“二人台”的代表剧目。这首民歌广泛流传于山西、陕西、内蒙、河北、青海、宁夏和甘肃等地。各地流行的民歌《走西口》虽然在词、曲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所表达的内容和感情是一致的,都是以真实的社会内容、细腻的生活细节、精彩传神的表演、凄婉苍凉的唱腔、浓郁的乡土韵味,唱出了黄土地上贫穷儿女的悲欢离合,爱恨情愁,生存的艰难,人生的无耐,因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一曲河曲民歌《走西口》,当今已风靡了全中国,唱响了全世界的华人区。
《走西口》唱出了当年走西口者的艰辛与悲凉,但它没有唱出走西口者的成功与辉煌。走西口固然艰辛,但勤劳智慧的人们却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深刻地改变了山西与内蒙古地区的发展进程。过去人们对于《走西口》的主题多从“离愁别恨的爱情悲剧”角度诠释,这是片面的。《走西口》固然是歌唱离愁别恨的,但走西口的主题决不仅限于此。近年来随着对“晋商”的研究,走西口的拼搏精神才被挖掘出来。但我认为,走西口的拼搏精神也决不仅限于那些大起大落或卓有成就的“晋商”,而应涵盖所有的旅蒙商与雁行客,尤其是占走西口绝大多数的雁行客。虽然他们只是春去秋回或有去无回,只是干了些垦荒种地、掏草挖媒、揽长工、打短工等不起眼的营生,但他们为了生存,也经历了艰苦的奋斗和顽强的拼搏;虽然他们没有名气和大的业绩,但是他们这种不认命、敢闯荡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后人所敬仰的。
三、忻州独特的商贸交通要道
今忻州市,现辖东六县(市、区):忻府区(明清时称作忻州)、原平市(明清时称作崞县)、定襄县、五台县、代县(明清时称作代州)、繁峙县;西八县: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明清时称保德州)、偏关县,共14个县(市、区)。忻州地区位于山西省北中部,东隔太行山与河北省为邻,西隔黄河与内蒙、陕西相望,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 ,南部紧邻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原市,它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民族冲突的战场,文化融合的舞台,商贸交流的通道,精英辈出的沃土。忻州地区境内关隘险峻,河流纵横。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号称京畿外三关,忻口被誉为“晋北锁钥”,此外,还有石岭关、赤塘关、平型关等险关要隘。河流有黄河、汾河、滹沱河、桑干河等。
黄河从忻州的偏关老牛湾入境,流至保德冯家川出境,在河曲、保德、偏关境内全长200多公里。依赖这一水上通道,三县早在明朝时就有了水上运输业,至清朝时达到了鼎盛。据《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记载:这一带的黄河水运“可上达绥远特别区域之包头镇,上溯至甘肃之宁夏,有拟试小轮船之议。下游亦可达河南、山东”。[①]因此,在北京至包头的铁路(京包线)通车之前,这里的商贸活动相当活跃。尤其是河曲,是黄河流经晋陕峡谷段中河滩平地最多、水面最宽的地段,县城附近的几个码头,最利于人员和商品集散,可日停大船百艘,因此向来有晋西北“水旱码头”的美誉,是周边地区理想的商业贸易中心。据《山西通志》记载,由河曲娘娘滩而下的30多公里河岸线上,从明代开始就布列着数十个古渡,其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可想而知。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河曲县城每年的白银流量高达600万两之巨。水西门外渡口一带,每天都有三四十只大船穿梭往来。当时,忻州人所开商铺门店遍及九府十六州,票号钱庄辐射全国十五省区,富商巨贾横跨亚欧大陆。[②]

忻州的商业活动萌芽于商代晚期,经汉唐宋元历代发展,在明末清初达到鼎盛。在明朝中期,忻州人以黄河古渡等地为商旅集散码头,开始了口外经商创业之路。以忻州(今忻府区)为例,据1935年《山西大观统计》,在当时二十万州民中,商业从业人员近四万之众,而十之六七在口外经商。[③]忻州人走西口,饱尝了开拓与创业的艰辛。他们有的是白手起家,“杭盖掏根子,石河拉大船,高塔梁放羊,大青山背炭”,靠无比艰苦的劳动换取一枚枚铜板;有的倾其所有购置了驼马货物,行程万里跋涉于大漠荒原,白天炒米凉水,夜间沙地露宿,遇大风迷路,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遇土匪洗劫,遭杀身之祸者亦有之。无论客死它乡还是荒原埋骨,都阻止不了他们前行的脚步。他们不仅是经商创业的开拓者,而且是中原文明的传播者。
漫长的经商之旅,形成了忻州人开放开拓的理念,诚信务实的品格,勤劳勇敢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商界奇才、社会精英,忻商成为明清时期晋商大军中的一支劲旅。清代启蒙思想家徐继畲以一部《瀛寰志略》首次全面介绍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社会制度,“成为我国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④]他的关于华盛顿和美国立国宗旨的经典论述,被镌刻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在北大演讲开篇提到的就是徐继畲,而这位徐继畲就是我们忻州人。清朝末年忻州商人程化鹏,在当时朝庭视对俄贸易为非法的情况下,冒死上疏,力陈华茶出口之利,最终获得朝廷恩准,从此架设了中俄贸易的桥梁。忻州商人王廷相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16岁从商,后主持旅蒙商号“大盛魁”数十年,其分支遍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商务涉及大半个中国并远涉莫斯科。“大盛魁”鼎盛时有员工8000余人,骆驼2万峰,年营业额达1000万两白银,营造出当时中国商界一个庞大的经济王朝。[⑤]
忻州人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令后人敬仰,而他们在经商中一向恪守的“以德为本”“以信传家”的品德也为世人称道。明清时期,作为商业古城的忻州“绸布纸钱粮、铁木估药当”[⑥]业业兴隆,成为山西境内的繁荣地区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立业中“贵德立本”“尊贤使能”“举贤罢亲”;在经营中“宁折本,不输名”“宁亏损,不失信”;在频繁的商业交往中,不论是借款还是赊货,只要有忻州人担保,生意就能顺利成交。在当时,忻州人的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商业活动中最响亮的诚信品牌。忻州人创业的辛酸、创业的豪情、创业的辉煌深深沉积在忻州的民俗文化中,加之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孕育了“二人台”等民间艺术。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歌《走西口》,使黄河西口古渡的所在地河曲名播天下,也使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受到心灵的震撼,激发了他研究晋商文化的浓厚兴趣,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文化散文力作《抱愧山西》。
“走西口”虽仅三个字,却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衍生出一段千古传奇,缔造出一部名闻天下的移民史。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三百多年间,忻州人走西口者从未停止过:春去秋回打工谋生的“雁行客”,满怀希望发家致富的手工艺人以及辛苦奔波于草原各地的“旅蒙商”等等,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梦想中的财富,一代又一代地走出口外,经商劳作,繁衍生息,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他们中的经商者成为晋商的一部分,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到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又远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开辟出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来源文史艺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