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可订阅关注我们哦!
卢光盛 张添:中国周边学建设与区域与国别研究 ——不确定性与路径共商
作者:卢光盛,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张添,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周边外交研究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自2018年以来,国内学界兴起对“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新一轮探讨,内容包括理论体系、路径方法、学科链接和机遇挑战等。在学科建设上,“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中国周边学”的基础,两者同属区域类学科,但两者均有一些不确定性。“中国周边学”的不确定性包括其自身概念、目的和学科边界的不确定性,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不确定性又对“中国周边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学科名称、驱动力和跨学科性等问题。在面对上述不确定性时,应致力于体系化知识构建,率先推动实践,并通过建立学术圈子等集体智慧,来共商共建,化解难题。
【关 键 词】 中国周边学 区域与国别研究 不确定性
【基金项目】(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7ZDA042);(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澜湄合作研究”建设项目。
2018年年初以来,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的牵头组织下,一系列关于“中国周边学”的笔谈文章陆续推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世界知识》在今年第4期推出“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研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因素” ,第8期又推出“中国周边学呼之欲出?”的封面文章 ,更进一步引发了从事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实务工作和研究同行的热议,当然不可否认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值得深思的几个问题包括:“中国周边学”的学科范畴究竟是什么,其与目前同样备受热议和争议的另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什么关系?“中国周边学”究竟是要强调“中国”还是强调“周边”亦或是要缔造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这样的框架根基牢靠吗?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将强未强之际,以“中国周边”这样一个有“中心论”色彩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是否妥帖,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概念?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讨论,本着在学科建设初期与众多同僚商榷的出发点,本文力图结合“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探讨“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并试图与诸位同仁进行路径共商,以更好助力该学科的成长与发展。
一、“中国周边学”与“区域与国别研究”
(一)对“中国周边学”的既有研究及解释
较早提出并系统性论述“中国周边学”的石源华教授指出,“中国周边学”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和以“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的国际关系理论新体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战略、新路径,并系统性提出了中国周边学建设的时代使命、学科建设、地理范围、战略定位等等 。结合石源华教授与其他同僚的概念界定,笔者将“中国周边学”概括为:以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为特定研究对象,致力于改善和促进中国外交的周边环境并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国家崛起的一整套成体系的知识,其类属于区域类研究。
现有对“中国周边学”进行论述的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维度。第一,理论体系建构类,主要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周边学”可能的学科框架、研究视角、学科定位、研究重点、建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学科的理论及方法等进行论述。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石源华指出“中国周边学”的时代使命、战略定位、理念战略、路径课题、分支及关联学科等新内容,并提出6项比较中肯的建议 。李文则谈到“中国周边学”的研究对象、奋斗目标与宗旨,强调中国立场与中国视角作为其内在规律性所在 。陈奉林围绕建设“中国周边学”学科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结合中外历史与现实素材,探讨该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第二,路径依赖类,主要是从学科建设的方法出发,探究“中国周边学”可能的路径所在。马丽蓉、仇发华等强调“中国周边学”应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等中国外交体系中的关键概念紧密相连,并基于此来探讨学科建设的路径所在 ;石建国、王明星等则强调从历史和时代的逻辑出发,强调“中国周边学”既要继往开来,又要顺应时代潮流发展 ;周方银、祝曙光等强调从比较的角度来缔造“中国周边学”,包括从古代的东亚国际关系,从日本对周边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等“他山之石”来寻找合适的路径 ;蒋建忠则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提出应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周边学” 。
第三,学科嫁接类,主要是将“中国周边学”与其他学科相连,以探究相关问题,或者研究“中国周边学”范畴下的某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从参与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学”研究和新学科建设研讨会所提交的文章,以及复旦“中国周边研究”公众号所推送的文章来看,目前涉及的学科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军事)安全学、历史学、哲学、文化传播学、地缘政治学,涵盖的专业领域包括国际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人道主义援助研究、全球与地区治理研究、俄罗斯研究、中东研究、北极研究、水外交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
第四,机遇挑战类,主要是探讨“中国周边学”建设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机遇可以概括为:历史积淀,如中国历史上处理周边关系的丰富经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提供的各类既有概念、原则和规范,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历史传统积累等;现实结构,包括客观上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物质力量的提升,新型知识体系的构建,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等等;政策要求,主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对周边外交的重视,提出系列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命运共同体”等的建设要求;学术需求,包括学术界自身建设周边类学科知识体系的需要,以及当前相关学科的整合需求等 。挑战则包括:概念界定,包括关于“周边”、“周边观”、“中国周边”、“周边学”等几个概念内涵、外延与范畴的分歧;学科定位,包括对“中国周边学”独立学科构建的理论、方法、课程设置与价值意义的质疑;建设能力,包括对于学科建设所需要的学术话语权、学科地位、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语言人才的培养存在担忧等 。
(二)“中国周边学”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关系
“中国周边学”虽然在概念界定上仍存在分歧,但其基础还是应当首先建立在区域类研究之上,并在学科界定与发展时就首先遵循区域类研究的一般规律。找准“中国周边学”的定位,首先要找准其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关系所在。区域与国别研究(Area Studies) ,广义上指通过解译当地语言、历史文本挖掘、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等方法对特定地理位置、民族国家、国家联合体或共同体与文化地域的研究,是一门涵盖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多领域、多类别的跨学科研究;狭义上则指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语言或其他某一或几个领域的研究 。

2019年云南大学举办“第一届东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研讨会”
从概念上来看,“中国周边学”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范畴,如石源华、李文、蔡建等均提出,“中国周边学”可归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中国周边学”的基础 。但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赵卫华指出,“中国周边学”应当基于区域与国别研究,但又要超越区域与国别研究 。郑先武、李峰则强调以“跨境区域研究”作为“中国周边学”建设的路径,以规避其中区域与国别部分相互重叠的概念 。郭锐、王彩霞指出,“中国周边学”旨在融合贯通国别研究、地区研究与问题研究,以建立一个立体化、超地缘的研究视角 。林民旺指出,“中国周边学”不应当只是深度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而是“一定意义上恢复亚洲的‘中国中心主义’” 。肖阳则在其文章中则指出,“中国周边学”研究过程中既存在将其等同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现象,又存在习惯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等宏大叙事逻辑进行植入和填充的现象 。
从实践来看,“中国周边学”应当是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圈定在周边这个区域范围内,对与中国紧密相关联的地区问题、国别问题、边疆问题等等的一个系统性整合。结合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的现状与特点,“中国周边学”的特点包括:其一,边界与范围的模糊性。所圈定的“周边”无论是“大周边”还是“小周边”的边界与范围均较模糊;其二,目的的后置性。是在有了对某个区域和国家的研究之后,将其整合入“中国周边学”,而不是将某个区域和国家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周边”后,再去做研究;其三,研究对象的立体辩证逻辑。对中国周边对象研究范围包括跨时间、跨空间和跨文化的主体,具有立体性,但具体研究需要有问题导向性,即集中于某一个时空范畴内的某一类特定问题;其四,研究主体的多元性。虽然建设“中国周边学”更多是一项学术界的工作,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研究主体必然不限于学术界,政策界、商界等利益攸关方也有着不小的发言权。
二、不确定性——中国周边学建设的挑战
从“中国周边学”建设的诸多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拳拳之心,那就是推动周边研究——这个重要、特殊且前沿的区域——作为学科的发展,为崛起之中国尽绵薄之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消除笔者对于创设“中国周边学”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周边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中国周边学”作为区域类学科,与“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共有的一些不确定性。
(一)“中国周边学”自身的不确定性
首先,“中国周边学”概念、内涵与范畴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周边学”客观上来说是以“中国”中心,以“周(periphery)”为范围,以“边(boundary)”为界限的一个概念,可能会带着某种中心主义甚至“势力范围划定”的色彩,不利于其学科的推介发展和国际接轨。虽然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经常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姑且不论西方有没有“XX周边学”这一概念,中国的学科与理论崛起,是否还要重蹈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理论所带来的一系列覆辙,值得商榷。毕竟,以中心主义所建构的理论,往往在对接具体地区或国家时“水土不服”,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引发激烈反弹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和美国的“辐轴体系论”都或多或少有这种特点,即便这些国家也避谈“XX中心论”,但其所缔造的周边体系并无法避除其周边国家的警惕与怀疑。一门对周边国家进行研究的学科,肯定不能完全是自我中心、自说自话的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把“中国周边”或“(中国)周边外交”作为一个范畴去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学科(其核心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去建设,客观来说也难免会引发不同的意见和理解。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的英文翻译,没有采用“periphery”(有“边缘、外围”的意思)或采用“neighborhood”(有“邻里感情”“守望相助”之意)的翻译,而是用了“neighbor”(强调 “邻居”“毗邻”的中立色彩)的译法,也有类似的考虑。
另一方面,“中国周边学”内涵究竟有多大,这关乎其学科界定及发展现状。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中国周边学”的内涵就会出现不同的差异,从而其学科本身及其发展的界定也会产生差异性。例如,石源华教授提出“中国周边学”滞后于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及“中国学”的发展,处于“未成型”的状态,是基于对“中国周边学”服务于崛起中的中国处理周边事务所需的新理念为定位,因此也提出“中国周边学”的学科建设是“应运而生”的 ;李文研究员则提出“中国周边学”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特定的一部分(包括周边相关的国别研究、次区域研究等),已经初具规模,因此已经完成“十月怀胎”,就等“一朝分娩” ,更偏向于对既有学科或研究的整合和重构;周方银教授则认为,“中国周边学”需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历史经验出发,其起初不应仅是数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在强调“他山之石可攻玉”的同时,其也提到“中国周边学”目前还只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 。实际上,“中国周边学”与“亚洲国际关系”或“中国外交实践”既有嵌套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如果无法厘清与这些既有二级、三级学科的联系与区别,那么其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会打折扣。

走廊国家
其次,“中国周边学”设立的目的是什么?是学科导向还是专业导向?从目前诸位学者所畅想的学科建设来看,“中国周边学”的主要目标更多并不是为了在大学里新设专业,而是推介这个学科,使其如同美国学、欧洲学、日本学、俄罗斯学一样兴盛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助推“中国学”的发展。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学、欧洲学等所研究的对象,是地理学和国际关系学里约定俗成、有着明确定义和大致明确边界的区域,但这个“中国周边”的涵义和范围,则要模糊、笼统和可变得多,且其整体性与统一性,并不见得大于其多样性与差异性。一般而言,从“大周边”所扩充的过程来看,被界定为周边范畴的国家只会越来越多,很难说突然就把某几个国家“剔除”,目前“大周边”已经被拓展到64个国家 ,究竟应当平等、对等地研究这些国家(无论大小、无论重要性、无论是否与我建交),还是要分出优先级,例如所谓的“走廊国家”、“缓冲地带”这些强烈地缘政治色彩的概念,进行有优先度、有主次的研究?进行概念不清晰的研究并不利于学科的建设,而过于清晰的研究,是否有利于我周边外交的推进,值得商榷。从实践角度来看,外交讲究的是灵活应变的艺术,对“中国周边”概念过于清晰的界定在实际运行中反而难免会自缚手脚。另外,如果说“中国周边学”有发展“中国学”的色彩,那么是应当更强调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还是要适当继承历史上的“封贡体系学”,也需谨慎考虑。姑且不论“封贡体系”这个概念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连体系内的国家,是否愿意承认自己归属过这一体系,仍然存疑。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国周边学”为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前景至少是有不确定性的。
再次,“中国周边学”的学科边界何在。“中国周边学”基于其特殊的地域范围和相对广义的研究范畴,其涉及到不少既有学科,自提出就有较强的跨学科性。这里的“跨学科”不能仅仅是学科与学科的简单“做加法”,也不能漫无边际地进行跨界联系,比如虽然“植物学”也可以被纳入周边研究(周边国家植物研究)的范畴,但如果不联系相关学科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其是否合适纳入“中国周边学”还有待商榷。即便字面上“中国周边学”所囊括的对象无穷无尽,但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换言之,如果没有清晰的边界,其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就不确定性而言,“中国周边学”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和中国外交等相关学科的界限、区别与联系就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将“中国周边学”置于政治学研究之下,那么是不是中间应当还有一个应接性概念“周边学”?如果将其置于国际问题研究之下,那么其很大程度上会被归类于区域与国别研究,从而成为三级学科(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仍然未建立一级学科地位)。如果与外交学相嵌套,是否更应该以“中国周边外交学”为研究对象,但这显然无法涵盖“中国周边学”的内涵与外延,有违学科建立的初衷。
(二)作为区域类学科的“不确定性”
“中国周边学”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其所归属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本身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不少学者所述的,关于“中国周边学”是否可以严格意义上属于“区域与国别研究”,又再次增加了其中的不确定因素。
客观上来说,“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一些成效。2018年4月15日,云南大学在昆明举办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全国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近50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的一个主题是研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问题。会议期间,云南大学新增“区域与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也经专家论证会得以通过。而就在几天前(4月12日),北京大学举行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正式确定了“区域与国别研究”在该校的地位。实际上,清华大学在2017年7月的时候,已经低调地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院”挂了牌,清华大学著名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就放在这个研究院里。此外,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内的各高校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设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或相近名称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发展这件事早就在做了,只不过近两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个刺激因素可能是2017年教育部批准了一大批“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实际上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早在2015年1月就已制定),而获设基地的高校基本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加以建设。

2018年云南大学举办“区域与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全国研讨会
可以看出,“区域与国别研究”如果说还不是如火如荼,也至少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排除其不确定性所在,这些不确定性客观上也增加了“中国周边学”建设的不确定性。
一是对学科设立的名称的争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个概念,美欧各国设立这个学科至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尤其是美国,不仅经历了对有关学科的“大反思大批判”,还基于该概念缔造出了不少的新理论 。在最近几年里,国内也产生了多个与这个相关、相近的名称,包括教育部文件里使用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清华大学使用的“国际与区域研究”,以及社科院张蕴岭教授倡导的“国际区域学”等,不一而足。这些概念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区域”与“国别”孰先孰后,究竟是按照研究范畴来优先大的概念(区域),还是按照研究的基础性来优先小的概念(国别)?再比如,“国际区域学”的概念是否能够清晰表明研究的重点与对象,其与“区域学”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与联系?昆明会议期间,本来设计有一个议程是讨论《国际区域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的提纲研讨及工作分工,但因为条件尚不成熟,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还有待商榷。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名称尚未有定论之际,“中国周边学”应当与“区域与国别研究”有何种联系的问题也同样很难回答,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学科建设尚未成熟之际,两者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部分套用西方所铺设的“区域学”框架,或统称为区域类学科。
二是对设立学科的驱动力问题的异见。在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昆明会议期间,多个代表提出同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动力到底在哪里?”,引发了热议。对这个问题普遍有人提出,国家战略与大国外交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动力,但也有学者指出,要认识到学术的、学科内在的驱动力,才是持续的推动力。从历史上来看,在西方理论逐步支配全球国际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区域与国别研究为西方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持续、动态与多样化的知识元积累,为其理论学说的经验观察与科学假设提供了案例与数据支撑,为其外交政策调整与形势预测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美欧高等教育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不管知识积累、理论构建、外交政策还是人才培养,都明显展示出其发展动力所在。但遗憾的是,在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共识,也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点也是“中国周边学”所面临的困境。不过坦白说,不管对于“中国周边学”还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地位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之争,都是现实的驱动力之一。与此同时,阻碍设立“中国周边学”、“区域与国别研究”或其他新的二级、甚至一级学科的力量,也受到这种驱动力的影响。
三是对“跨学科”路径在学科建设中的分歧。昆明会议上,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否需要、以及是否可能有着“专享”或至少是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较为特定、集中的研究对象。部分观点认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天然的交叉学科,多学科是必然的、可行的路径,这也可能是一种研究范式的创新,其学科要点相对集中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区域经济学和地区主义等学科和理论上。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构建“区域和国别研究”时,应忌谈“多学科方法”,因为一提“多学科”,就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就会导致“区域与国别研究”成为一个“大筐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困境。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一种调和的观点,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学科划分机制,以一种“创新平台”的方式来打造“区域与国别研究”,而不应该仅仅是“跨学科”或者“创学科”,而是学科的融合与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新。这几种观点都有着各自的道理,任何一方均难以说服另一方。在“中国周边学”建设的上海会议上,对“跨学科”路径的认识也存在类似的分歧,这说明,对于“跨学科”应当是缔造学科本身的形式(如系统化整合或者有机融合),还是学科缔造的一种工具(如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己所用),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路径共商——中国周边学建设的前景
党的十九大强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明确“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实对我们研究区域尤其是周边区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笔者认为不管是“中国周边学”,还是“区域与国别研究”,抑或是其他名称的学科,面对上述不确定性时,还是应当积极找寻解决问题的路径。本着“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笔者认为用哪个名称是其次,首要的是真实有效地推动区域(以周边为首要)的研究,服务于国家大计。为此,我们不妨以开放的心态、持续的研究、合作的态度,共商共建共享这一公共产品。
(一)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化“横向”整合为“纵向”建构
一旦体系化的知识经过实践检验,能解决某个实际问题,其路径经调整后,便可作为其他问题解决的参考方式。随着解决区域类问题(尤其是中国周边问题)的某一种或几种路径被学者们自觉应用于理论与实践之中,学科便自然而然建设起来、甚至成熟化了。西方建构区域理论时,并没有首先界定其是“区域理论”还是别的理论,而往往是通过接触、了解、分析具体区域与国家的内部地理环境、国民性格、民族构成与历史互动等,与西方自有理论的生成与适用环境进行对比,进而形成某种体系化、逻辑自洽、可供改造的“理论范式体例(Practice)”,比如共同现代化理论、权力合法化理论与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等。西方范式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的理论建构,但其成熟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体系化的知识生产在国内是比较缺乏的,“中国周边学”学科的建设正是一个好的机遇。
从体系建构来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在西方早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其对区域类学科的重视,促其在社会经济建设、相关学科发展和对外政策研判中饱尝甜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及西方区域类学科固有的顽疾暴露,其政策依赖的下降、价值判断的单一与理论实践的脱节,束缚着其自我迭代发展,导致大量研究区域与国别的学者转去研究宏观理论范式,一度引发区域类学科“衰亡危机” 。
在体系建构初期,“中国周边学”的建设还是应当寻找相对规范的着力点。例如,可通过规范化解释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这里的“范式”并不一定要像西方语境下“范式”概念那么“科学化”,而是可更多结合中国传统外交哲学,但一定要讲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说别人愿意听的故事,使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道义合法性。当然,如何规避“中国中心论”的弊端是值得深思的一点。不管“中国中心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其名、其实如何,外交毕竟是一门讲究和解与协调的艺术,最大化规避“中心论”给学科本身带来的困境、以利于理论纳入实践轨道,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二)先解决“体与用”的问题,再讨论“文与质”的问题
在述清哪一个名称更为科学合理之前,更应优先思考的是,如何在一定的范畴之内,做实、做细、做到位相关的研究,讲好相关的故事、贡献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理论方法。或许在研究初期,“中国周边学”同区域与国别研究一样,会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研究存在这样那样的交叉之处,但笔者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间应有的界限会渐渐明晰,而学科间应有的融合不仅将助力新学科理论方法的诞生,也将惠及旧有学科的更新发展。
中国是大国,大国的区域类研究就应该有大胸襟、大视野、大关怀,中国未来兴起的区域类研究,应当吸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训,应当打造的是既具有中国视角,又具有世界关怀的理论。“跨学科”是学科自我更新迭代的必然要求,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多言必谈“跨学科”的内容,都不是理想中高质量的“跨学科”。或许将来出现的某种理论,既有区域类研究的属性,又具有国际关系学科属性,但我们没必要去辨析其究竟属于哪个学科,而是应当进一步思索这样的理论以怎么样的方式发展和更新了既有学科,这才是有效的、高质量的“跨学科”。
就此而言,也有一些路径可供参考。其一,有的学者谈“他山之石可供玉”,例如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美国和印度处理周边关系的方法,但我们何不在学科建设初期,就纳入我们周边国家的智慧,来达成最初的“共建、共商、共享”呢?可通过议题设置来形成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协同捆绑,促使“中国周边学”从一开始就有周边国家的学者参与,以逐步缔造可以与西方知识体系抗衡或者相对峙的学术话语权。不过,值得探索的是,是否一开始可“搁其名而行其实”,先以某种方式降低“中国中心论”的色彩,例如谈“中国东盟学”、“中国蒙古学”、“中国缅甸学”、“中国澜湄学”等等。
其二,重视学科的自我更新完善。虽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区域类学科因“大理论转向”而出现了衰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国等国家区域类学科的自我更新能力极强。美国一方面毫不避讳利用区域与国别研究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则又鼓励国内开展“大反思”来批判和改良旧有思路。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金会,每年斥资巨款资助美国高校“区域中心”的研究 ,而美国政府毫不避讳学者提出对美国区域研究中“美国例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 。区域与国别研究在“自我对抗”的过程中,知识体系源源不断被更新,又衍生出不少知名理论 。自我更新完善使西方理论被赋予新的时代性与生命力,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得以巩固。美国的思路虽然有其自身的国情特点,但不可否认其也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周边学”及“区域与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要敢于和善于接受各学科及不同领域的人士的批评意见,在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展现勃勃生机,并最终建设起更有质地而并非名头更加响亮的学科。
(三)如何有效化解学科资源的配置问题,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集体智慧
新旧学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往往难以启齿但却非常实际。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的会议上,就有学者坦言,如果“区域与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发展起来,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原有关于区域与国别内容的研究“怎么办?”在“中国周边学”学科建设的会议上,也有学者提出,建设“中国周边学”究竟如何处理其与原来外交学、边疆学、民族学及国家安全学相关内容之间的关系?“中国周边学”既需要各类学科作为其建立与发展的基础,又需要在这些诸学科之上建立自身的独立性,在短期之内如果不进行高效的资源让渡和资源整合,谈何容易!
对既有学科的失落感,也是比较正常的。但试想,国际关系学学科的兴起,不也是在与政治学学科甚至经济学、社会学学科“抢资源”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吗?实际上,区域类学科与国际关系学学科本身也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范式上的更新还曾经一度成为立于区域研究之上的“新星”。在上世纪美国行为主义兴起的时期,区域学受到了沉痛的打击,区域学的学者纷纷垂青于实证主义科学理论的建构,而不再关注区域学本身。不过,随着区域学“自我对抗”不断升级,实际上其生命力不仅没有丧失,反而以更加成熟的方式展现出来,甚至成为各高校的“显学” ,这固然有政策界的支持,但更多是学术界自我适应与自我进化的过程。
既然资源的分配无法满足所有人,那么有志建立“中国周边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诸位同仁,就要敢于分享自己原有学科的知识,笃信这样的分享不会牺牲自己在原有学科的地位和利益。结合新学科建立的需求积极建言献策,最终形成的集体智慧,既要包括推进学科成长的营养成分,又要包括防止因急功近利因素而致使学科跑偏的调适手段,更要有一颗愿意长期栽培、甘于寂寞、屡败屡战的热忱之心。集体智慧的建立,始于集体知识的积累,兴于集体行动的实践,旺于集体智慧的持久更新与完善。
有观点提出,区域研究应该建设一个“圈子(network)”,并由这个圈子来共享学科建设的资源。笔者认为,这样一个“圈子”的建设确有必要,诸位学者能够在数次“中国周边学”与“区域类学科”研讨会上积极讨论问题,这样的“圈子”实际上已经有了雏形。在希望诸位同行专家将自己原来领域学术资源不吝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同时,笔者认为这样一个“圈子”也有能力“共建”新的资源,甚至可以将这些资源反馈给其姊妹学科。当这个“圈子”越做越大,并且和其他“圈子”有机、平等地套合在一起时,或许我们原先孜孜追求的“学科边界”,或许也将没有那么重要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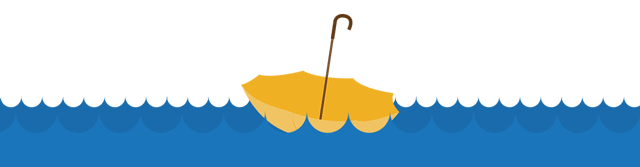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