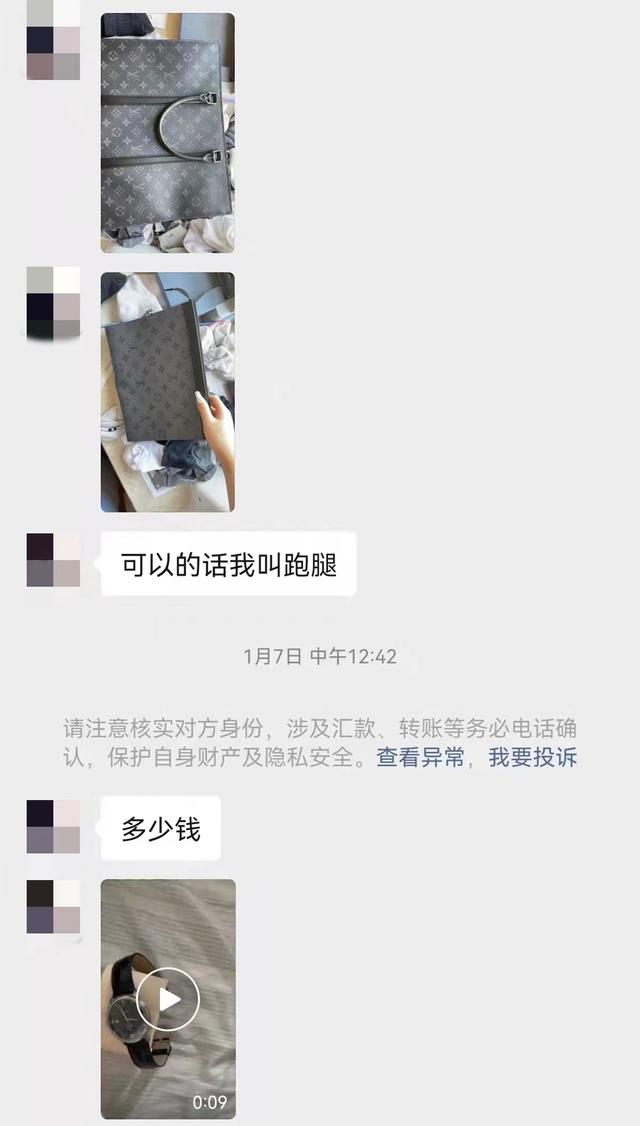家乡有一道菜,俘获了所有人的心,吃起来既有可口的鲜味,又有一股淡淡的黄浆水味道,它就是“干子烧猪肉”,有着人间烟火味与汤池人情结的美食。
小时候,住在汤池果树山区一个叫搓耳石的小山村,最期盼家里来客人,又能吃上干子烧猪肉的“洗筷汤”,等客人吃完走了,妈妈就将盆中剩菜加点“井罐汤”热一热,就是我们兄妹一顿饕鬄大餐,小小年纪也能“扛”上两大碗饭。
长大工作了,那个时候公家、农家来客人招待标准配置就是“干子烧猪肉”,即一个煤油(柴)炉、一个二爿锅、将烧好的干子、猪肉放入锅中炖着,直炖至干子起“孔”,满屋飘香。这小小的二爿锅好像永远装不满、吃不折(方言完的意思),因为这锅里可以加菜加油加汤,如青菜萝卜黄心乌粉丝、猪油、“井罐汤”等,我理解这道菜应该叫“干子炖猪肉”,也可能是现在餐桌上“锅子”的由来。
至于为什么叫“干子烧猪肉”,老家的一位大队书记是这样说的“干活就有肉吃”,他老人家虽然是大字不识一斗,但话糙理不糙,那个时代不干活饭都吃不上,何况吃肉? 乡下人对这道菜有不同的说法,公家烧的叫“猪肉烧干子”,农家烧的叫“干子烧猪肉”,一看就明白是不一样的。
不过那时候公家招待也是很节俭的,我刚工作是在果树中学,承蒙领导信任还兼任司务长。公务来人,就去老街食品站和豆腐店,用两张油渍斑斑的收条换回二斤猪肉、二十块干子,学校里有片小菜园,拔几棵菜,酒是从庐江酒厂批发的粮食酒或“八角冲子”酒。一顿饭能吃上一两个小时,下桌子时脸是红的,鼻孔是黑的,罪魁祸首是酒和煤油炉子。
那个时代,物质比较匮乏,农家来客人招待可能比公家“大方”,尊贵的客人来了,除“干子烧猪肉”外,还要杀只鸡,一般的客人来,增加两个时令蔬菜,是人之常情,也淳朴乡民的好客之道。
老家,一直在变,楼房多了、马路宽了、乡村美了,未曾改变的是干子黄浆水的味道。
老家,一晃三十年,不变的是那干子炖猪肉的念想。
说到现在,该普及一下这道美食需要的食材:土猪五花肉500克、豆腐干10块、调料生姜、葱花等适量。切记猪肉是土的,干子是手工磨石膏点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