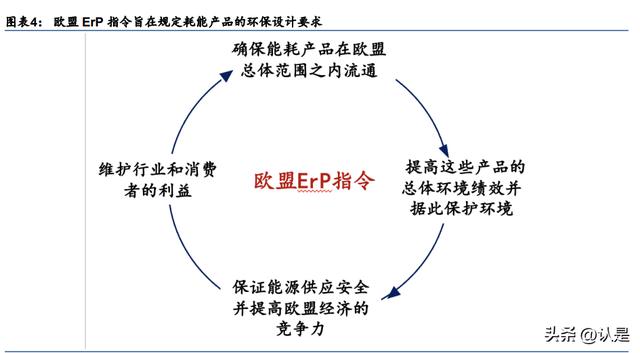明 董其昌 燕京八景图册之舫斋候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醉文明壹案头拾珍文?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醉文明壹案头拾珍文
明 董其昌 燕京八景图册之舫斋候月
中国是个“好古”的国家,“尊古法制”成了一句口头禅。黄宾虹:“唐画如曲,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近,加水愈多,近日之画已有水无酒,故淡而无味。”这是绝对的崇古论。米芾《论书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辙,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折言光尤可憎恶也。”也是以古为准。宋代郭若虚“论古今优劣”:“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所言正是唐宋之别,一语中的。这是画论中少见的客观评鉴。若以个人为言,传统的儒家教育,总是教人处世要温良恭谦,谦虚是做人的原则。从书画的创作,敢说自己超越古人,史上几乎难得一见,有之“两文敏一大千”。
赵孟頫:“自谓不愧唐人”
书画学习的过程中,取资于往古先贤,求得“古意”,往往被视为能出“新意”。“汲古润今”仍被高举为法门津渡。“汲古润今”,赵孟頫(1254-1322年)的画论,提出“古意”一语。对“古意”的诠释,已非新题。还是列举赵孟頫的自我题辞,以为论述。
赵孟頫自题《双松平远图》:“仆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盖自唐以来,如王右丞、大小李将军、郑广文诸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巨、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仆所作者虽未敢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少异耳。因野云求画,故书其末。”就此,以“至五代荆、关、董、巨、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为“古”。不满近世,跳跃过近世,取法更古的典范,赵孟頫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取古为意,超过时流,进而能胜古否?又说“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余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
更具体的学画经验表述,对学习唐人的成就,赵孟頫相当自负,《人骑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自题两则,其一:“吾自少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云。”其二:“元贞丙申岁(1236年)作。画固难,识画尤难。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故颇尽其能事。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世有识者,许渠具眼。大德己亥(1299年)子昂重题。”自道“自谓不愧唐人”,表示至少能与唐人比肩并席,当然是超越过宋人一代。更进一步,又题:“余自幼好画马,自谓颇尽物之性”。友人郭佑尝赠余诗云:“‘世人但解比龙眠,那知已在曹干上。’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
这固然是借他人赠言,却清楚地自许:“曹、韩固是过许,使龙眠无恙,当与之并驱耳”。《人骑图》拖尾有赵孟頫之弟赵孟籲跋:“当今画马,真得马之性,虽伯时复生不能过也。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八日子俊书。”这句话,或可视为弟代兄言。赵孟頫是见过李公麟(1049-1106年)的《五马图》,有诗:《题李伯时元佑内厩五马图,黄太史书其齿毛》:“五马何翩翩,潇洒秋风前。君王不好武,刍粟饱丰年。朝入阊阖门,暮秣十二闲。雄姿耀朝日,灭没走飞烟。顾盼增意气,群龙戏芝田。骏骨不得朽,托兹书画传。”见过此画,赵孟頫之自许,当是有所自信。
又有赵孟頫自题《红衣罗汉图》:“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善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与罗汉像,自谓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如何也?庚申岁(1320年)四月一日, 孟頫书。”是画此《红衣罗汉图》,又是自许超过“五代王齐翰”辈。《人骑图》来自学唐人“古意”,画马能与李公麟抗衡,画人物超越五代北宋。古意与新情,字面上是相对的,古意可以生新情,新情借古意表述。“古”所指也未必有一定的时段。赵孟頫之学古,“古”是隔代,或者说,南宋代山水、人物,非他所能满意。单纯地说,风格发展到极致,又重回到转寻更早的源头,所谓“风格循环”。
“自豪”又“自省”的董其昌
后赵孟頫三百年,同样谥号“文敏”的董其昌(1555-1636年),于书画高自标许,更具体地喜与赵孟頫、沈周、文征明对垒。整体的书法史发展,董其昌自豪地说出:“吾书无他奇,但姿态高秀,为古今独步耳。心忘手,手忘笔,笔忘法,纯是天真潇洒。”具体地置身于时代长流,即便是率尔酬应的书写,“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微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无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董其昌自信是一个变局的引领风骚人物。“虽然余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人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者,必能知其解者。”这“亦复一变”,该如何说,有明一代帖学,无非笼罩在赵孟頫及实际科考书写的馆阁体。董其昌的书法以“生”以“润秀”,乃至于“平淡天真”,跳脱了此一传统。当然董书经过清圣祖康熙的钟爱,影响成风,该是他生前所未能料及,却也应验了这句话。“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以语此窍也!”书写用墨,墨沈本以匀整为主,董其昌却注意到书写时从醮墨的由湿到干,再醮墨的整篇变化。
古来论书都重用笔,殊不知笔须托墨,才能留笔迹。怀素《自叙帖》:“初疑轻烟澹古松”、“古瘦漓骊半无墨”、“驰豪骤墨剧奔驷”诸语即是。“多见古人真迹”才能知墨色,而非墨拓本的黑纸白字所能见。董其昌的用墨观点,也开启后来者如王铎(1592-1652年)一辈的书风特色之一。
对董其昌书学的历程研究,已是车载斗量,众所周知,董其昌自述其所以发奋学书:“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专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这段话,充满着“自豪”又“自省”。
对于赵孟頫,具体地道出:“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相关于“生”与“熟”,董其昌解释:“余素不学赵书,以其结构,微有习气。”因技巧熟练,而有习气的俗。又有相同的说法,“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画则具体而微,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赵与董,都曾致力于学习李邕(678-747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杂书册》上,董自跋:“学李北海书五十五年矣!初时专习,颇为近之,近复忘其旧学,然时一拟,书亦不落吴兴后也。”又“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这些名言,也一样地充满着“自豪”又“自省”。
董其昌:“恨古人不见我也”
相对于书法、绘画一面,董其昌于赵孟頫并无微词。万历癸未(1583年)见《鹊华秋色图》于项元汴家。董其昌于《鹊华秋色》赞美:“吴兴此图。兼右丞北苑二家画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故曰师法舍短。亦如书家以肖似古人不能变体为书奴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晒画武昌公廨题。其昌。”于跋《宋高宗书七言律诗册》:“思陵书杜少陵诗,赵吴兴补图,乃称二绝。赵画学王摩诘,笔法秀古,使在宋时应诏,当压驹、骕辈,为宗室白眉矣!甲辰六月(1604年)观于西湖画舫。董其昌题。”
于画,董其昌也未必尽信古胜今,也有今胜古之处。故宫藏明顾正谊《云林树石轴》,董为题跋:“仲方此画,自李营丘寒林中悟得,故于迂翁有夺蓝之趣。其昌观于玄赏斋题。”就原画水平所见,疏树修篁顽石,顾自题款也仿倪瓒(1301-1374年)书风。董氏此跋难免为友朋相互揄扬之语。钤印做“太史氏”,当在董氏年四十以后。做于丙申(1596年)的《燕吴八景册》(上海博物馆藏),时年从三十八至四十二,此册有一段重跋,写道:“重一展之,总不脱前人蹊径,俟异时画道成,当作数图以易去,以当忏悔,即余亦未敢自谓技穷耳”。自省之中还是以“道成”自期,“道成”所以独步古今。
早年董氏普遍学习各家,加以阅历丰富,归结出:“画平原师赵大年(活动于1070-1100年),重江迭嶂师江贯道(活动十二世纪初),皴法用董源(十世纪初)麻披皴及《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将军(653-718年)《秋江待渡》及郭忠恕(活动十世纪)雪景,李成(916-967年)画有小幅水墨及著名青绿,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征明1470-1559年)、沈(周1427-1509年)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董其昌试图用来超越前辈的信念,“再四五年,文(征明1470-1559年)、沈(1427-1509年)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妙方是集各家优点而大成的方法。
元 赵孟頫 双松平远图(局部)
万历癸巳(1593年)董其昌在北京见黄公望《富春山居》,万历丙申(1596年)收得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于前隔水裱绫,大呼此卷“吾师乎!吾师乎!”
就中何以如此,从实际画技论,以今日能见董其昌曾收藏董源画如《潇湘图》诸作,所见的画法是五代北宋时(十世纪)董源的密实作风,恐非董其昌个人画性与技法所能从容驾御,反而松秀恬和的元四大家画,才真正让董其昌画性都所发挥,尤其是黄公望。就董氏见闻年代序,他是先见王维、赵孟頫、黄公望,后见董源。因此《富春山居图》入董其昌收藏后,能朝夕相随。此卷的笔墨,固然“披麻皴”笔法是“吾家北苑”,然而“墨法”的蒙养,该是给董氏更多的启发与实际应用。董氏自谓“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于画、书,用墨之讲究,故宫藏董其昌《仿黄公望山水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题云:“大痴画法超凡俗。咫尺关河千里遥。独有高人赵荣禄。赏伊幽意近清标。董玄宰画。”董于幅后又自跋:“余得黄子久所赠陈彦廉画二十幅,(脱一字)及展临,舟行清暇,稍仿其意,以俟披图相印,有合处否?丙辰(1616年)九日毘山道中识。董其昌。”在意于对黄公望“有合处否?”所指虽非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目前也不知《黄子久所赠陈彦廉画》二十幅是何面目,但从本卷的笔墨气息与《富春山居图》比较,并无两样。可见《富春山居图》于董其昌笔墨发展之关键。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用墨: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秾肥。董其昌之擅用墨,其得来自黄公望,上两卷所显现的墨“润”可为说明。张庚论述董其昌用墨:“麓台(王原祁)云,董思翁之笔,犹人所能,其用墨之鲜彩,一片清光,奕然动人,仙矣!岂人力所能得而办?”董其昌巨轴《夏木垂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因水墨的交溶,画境爽朗潇洒,生机处处,而这种特征成为董其昌的的特殊风格,然而,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局部相比对,则知其所来自。
以董其昌之心境,岂能臣伏于人。他颇多与古对话,表现出争胜古人。常为学者引用的是:“余与文太史(征明)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针对着黄公望,董其昌的《江山秋霁》(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藏)董自跋:“黄子久《江山秋霁》似此,常恨古人不见我也。”这用词典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案例。“(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云:‘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
董其昌在中国山水画史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将山水画“墨”之美,表现得淋漓至尽。董其昌也建立了抽像的山水空间之美,如《江山秋霁》即是代表作,难怪,董其昌自信满满的写下“恨古人不见我也”的心情。董不愿当“书奴”,又岂可能当“画奴”。董屡屡高呼“吾家北苑”,但真正的落实于作品上,也是如他自己本相的书法、画法,某某家云云,祇是意有所指,还是自我的董其昌。董氏59岁(1613年)有名的《论书》亲写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他参禅的领悟用之于书法,或者说为他的临古说法。《论书》中写道:“哪咤拆肉还父,拆骨还母,须有父母未生前身,始得楞严八道之义。”要的是自我本相。是以看董书董画都作如是观。
张大千 临《唐杨升峒关蒲雪图》
张大千:“老夫自擅传家笔”
后三百五十年出现了张大千(1899-1983年),一样集书画家、鉴藏家于一身。张大千对其部份收藏,曾有两次著录行世,一是癸未(1943年)之《大风堂书画录》:一是1954年于日本东京出版《大风堂名迹》。
《大风堂名迹》之序言,以自信的口吻写道:“余幼饫庭训;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临川衡阳二师所传,石涛渐江诸贤之作,上窥董巨,旁涉倪黄,莫不心摹手追……其后瞻摩画壁,西陟敦煌……一解纸墨,便别宋元,间橅签贉,即区真赝……世推吾画为五百年之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1525-1590年)推诚,清标(1620-1691年)却步,仪周(1683-1744年)敛手,虚斋(1864-1949年)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这序文,简略地说到,他个人涉猎的古代名家,宋元以来无所不包,更有古人所未及的魏唐敦煌。此书其后于1978年再版于台北,大千重序此书,又明言收藏的目的是:“挹彼菁华,助我丹青。”他也清楚地表达,以一己的力量网罗前代名迹,要的是为己所用,大千自己是此中豪杰。
历史的累积愈来愈深厚,后来者欲居上,大千的学习是追寻走过历代画家的步伐,来壮大自己,雄心伟志是以“集大成”的理想为志业。
1920至1930年之间所画《二叟赏梅图》,人物的造形应是从任伯年与陈洪绶画风交融得稿。画成时即题:“此画当非任渭长(1823-1857年),辈所能梦见。世无赏音,且以予为妄人矣!掷笔三叹。婉君(1917-?)保之。爰记。”庚辰(1940年)再题,“老莲画出阎立本历代帝王像,上溯六朝,未落宋元人一笔。近见曹望禧造像,益知其源流所自也。”本幅第一题有此自负的口吻,显然是上溯陈老莲(洪绶1599-1652年)的风格,所以说是任渭长,任伯年这一系脉,张大千自认已不为然,因此可以超越任渭长。曹望禧造像是北魏正光六年(525年),正是陈洪绶追随的六朝古风。
1967年画《定林萧散图》题:“龙眠居士有《定林萧散图》,盖为王荆公居金陵定林陵寺所作也。此图见之著录,而墨迹不传,每欲追橅,以目翳为止,近顷目力稍胜,遂想象为此。效龙眠人物者,以赵鸥波(子昂)、张叔厚(?-约1356前)为嫡传,此图虽不能方驾二公,亦未肯与仇、唐作后尘也。丁未春,爰。”画中的王安石(荆公),以李公麟(龙眠)贯有的玉箸篆白描为之,流畅不失工整,这是正宗的白描法,必与古人争胜,自信不输唐寅、仇英,看出大千的自豪。
对于十六世纪所产生的“没骨山水”,张大千更直接对垒于董其昌。《临唐代杨升峒关蒲雪图》指出:“峒关图董其昌临本甚多。”这也说出张大千在此时已注意到这种色彩意农厚的“没骨山水”。本幅与他后来的“没骨山水”更忠实于董其昌或晚明所有的色彩式“杨升山水”,这可见于树干与点叶,基本的山水树石勾勒,还是一般的山水画法,没有他后来画此路风格的强烈敷色。题临此幅《唐杨升峒关蒲雪图》:“青绿没骨出于吾家僧繇,董文敏数临之,此又临文敏者,丁亥(1947年)二月张大千。”左方又题诗一首“华堂一代老宗师,瘦树枯山淡逾宜。谁信峒关蒲雪起,却从绚烂出雄奇。”好一句“却从绚烂出雄奇”。这是对色彩的礼赞。1963年《秋山红树图》题:“精鉴华亭莫漫衿,误将蒲雪许杨升。老夫自擅传家笔,如此秋山得未曾。董文敏盛称杨升《峒关蒲雪图》,而吾家僧繇《秋山红树》,实为没骨之祖。此图约略似之,癸卯(1963年)六月既望。蜀郡张大千爰。”
这首题诗,说出个大千本人对青绿没骨的见解是超越董其昌。1949年作,一样取名《峒关蒲雪图》,画的题款,可以说是大千对青绿没骨山画的总结表白。“此吾家僧繇也,继其法者,唐有杨升,宋有王希孟,元无传焉,明则董玄宰,戏墨之余,时复为之,然非当行。有清三百年遂成绝响,或称新罗能之,实邻自郐,去古弥远。余二十年来,心追手写,冀还旧观,斯冰而后,直至小生,良用自喜。世之鉴者,毋乃愕然而惊,菀尔而笑耶。己丑(1949年)润七月廿七日爰。”得意之色溢于言中,更巧妙的因与张僧繇同姓,引用唐代李阳冰(721-722年)对秦李斯(?-前208年)的篆书继承,自诩成就,视董其昌、华岩(1682-1756年),不足观也。受到董其昌笔下每每说“吾家北苑(董源)”的意念,姓张的大千则是两个:“吾家张大风(飌)”、“吾家僧繇”。唐之“吾家僧繇”,比董之“吾家北苑(董源)”更古了,连追溯祖先也要调侃一番。
张大千的见闻极广,见过张僧繇和杨升的画作或传称的作品,吾人不必置疑,然就今人容易得见的诸作,一是和存世的董其昌《秋山红树》对比,而更令人想起的是敦煌320窟盛唐《日想观》山水,必是大千所熟悉的。董其昌虽云“没骨山水”,画来还见树干有勾勒圈叶,山有皴法,赋彩犹是清雅,张大千更是浓重,直接施朱敷白,涂青抹绿,已然如壁画的重厚,已然非“没骨”一法所局限。
大千晚年的泼墨、泼彩为世所重,甚至是被认为臻至化境旷古未曾有的自我创作。对此,张氏强调来自唐人王洽(四世纪前半)的泼墨法,《云山图》自题“元章(米芾1501-1107年)衍王洽破墨为落茄,遂开云山一派,房山(高克恭1248-1310年)、方壶(约1301-1378年后)踵之,已成定格。明清六百年来未有越其藩篱,良可叹惜。予乃创意为此,虽难远迈元章,当抗身玄宰。”又是与董其昌对垒。
结语:
清代诗人赵翼(1727-1814),名句(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文敏一大千”隔世交锋,还是如是观。有为者,不必叹“既生瑜何生亮”。
(作者:王耀庭 系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原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