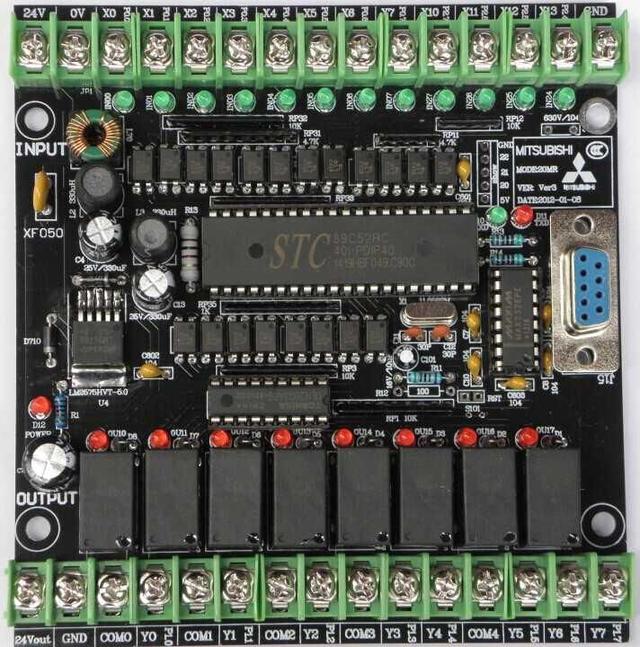据传王羲之学书自述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浥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处见张旭《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书笔阵图后》)《晋书》王羲之 “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别传》云:“羲之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其所措意,皆自然万象,无以加也。” (陈思《书苑菁华》)

王羲之
如上所述,王羲之的书艺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成就首先得力于卫夫人的教导,继学诸家,尤其是向篆隶方面取法颇多。他所借鉴的李斯、曹喜,就是秦汉时期的篆书大家。曹喜所擅长的 “垂露” “悬针” 之法,对后代的楷、行书体很有 “滋阳” 的作用。蔡邕三体石经中的隶书对王羲之有很深影响。其书 “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袁昂《书评》)”、 “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 (张怀瑾《书断》)。而三体石经 “字画谨严”,也正是王羲之所以心仪的。在他自述中所提到的张旭,是草书大家张芝之弟,所写隶书、章草颇有 “妍华” 之致。这些都对王羲之书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到他手中,东晋时期王谢大族所爱好的 “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演变成 “安详严肃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终于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爱好”(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从而传之千古。
卫夫人
正因为王羲之学书的根底厚,路子广,转益多师,尤其借鉴了篆隶的笔力、笔势、笔意、才形成了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 的雄强风格。概而言之,王羲之书风既妍丽又雄强,而历来学书者都夸大其妍丽之致,忽视了雄强之气。宋代的黄庭坚感叹:“世人但学《兰亭》面,欲换骨无金丹。” 清 何绍基更以讽刺的口气说:“怀仁《圣教》,集山阴棐几面成,珠明鱼贯,风矩穆然,然习之化丈夫为女郎,缚英雄为傀儡。” (《跋张荐山藏贾丘壑刻阁贴初扩本》)他们正在针对俗书姿媚,还自诩为得右军法乳而发的感叹。这种俗书,就衍化为后代帝王所推崇的 “院体” 书,扼杀了王字生气勃勃的命脉。

黄庭坚
一般来说,贴学的源头只上溯到王羲之父子,特别是他们 “妍丽” 的一面正是顺应了书法发展的趋势所取得的成就。时至今日,要正确理解其 “雄强” 的意义谈何容易。而写碑的,大多上溯到篆隶,强其风骨,而成为不同于贴学流美之风的书体。其实与王羲之的源头是一致的。所以,若求他的 “雄强” 之气,也当如王羲之那样精熟篆隶,才能脱去凡骨,这也许就是黄庭坚所向往的 “金丹”把。另外,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美之极,即雄强之极。”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就是对王羲之书风 “雄强” 的又一个解释。

王献之
作为 “书圣” 王羲之,也如孔夫子一样,是一位集大成者。后世学者也只能得其一体,具体而微。孔门七十二贤人,能学到和强化其老师某一方面即可称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后代书坛的虞世南、欧阳询、米芾、蔡襄、赵孟頫、鲜于枢、文微明、董其昌、王铎、刘墉、王文志、何绍基、翁同龢等,虽基本同出一源而风貌各异,也如孔门弟子一样各有成就,给后代如何学习传统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虞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