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封建王朝一项重要的国策,自秦始皇北征匈奴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末年停止,共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史。漕运是指将征收的田赋通过水路运输到京师或是指定的地点,清代的漕运十分发达,其制度也最为严谨。本章节就具体讲一讲清代的漕运。

漕粮被称之为“天庾正供”,朝廷向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八省征收漕粮,额定400万石。除去改征折色及截留他用的部分,实际征收一般在300万石左右。漕粮是宫廷及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因而漕粮的征、运受到清政府的高度重视。
江、浙、皖、赣、湘、鄂六省所征漕粮为征米,是漕粮的主要部分,作为八旗旗人兵丁饷米和王公百官的俸米。其中22万石为糯米,又称白粮,从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太仓州,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征收,供应内务府、光禄寺,也作为宫廷和紫禁城兵丁、内监与王公官员俸米等。
小麦主要征于河南,供内务府宫廷之用。豆(黑豆)征于山东、河南二省,作为京师官兵畜养马、驼的饲料。
每年这大批漕粮,都是由水路,主要是大运河北运至通州,在通州卸船以后,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师,分仓储存。其中输送京师粮仓的部分,称为“正兑米”,供八旗兵丁饷米;留储通州仓的部分,称为“改兑米”,是供王公百官的俸米。王公百官的俸米,须自行前往通州领取。以上几项,以入京仓的八旗甲兵之米粮数额最大,每年约240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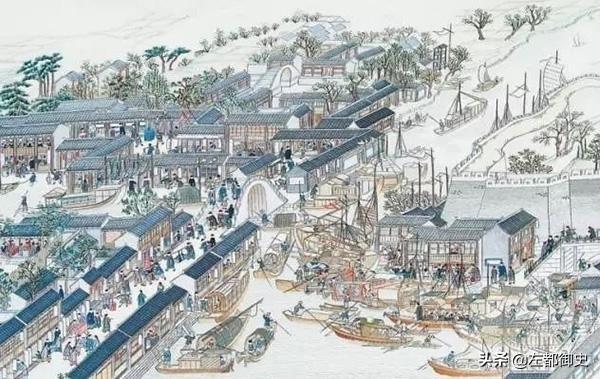
清代漕运较之明代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将所交漕粮交给运漕粮的运军称为“兑”。所谓军民交兑,是指交漕粮之户将粮运至本州县码头,交兑给运军,由运军代为北运,但漕粮纳户须贴给运军耗米(补贴费)等。
清初也曾沿用这一旧制,不久,因运军借机向漕粮纳户随意勒索,此项费用大增,民不堪其苦,遂于顺治九年改为官收官兑,即纳户将漕粮交与所在州县官,与各省运军互不相见。
这一做法,引起了清代漕粮征收、运输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漕粮从征收到交兑、起运、督催、稽查、交仓等一系列过程中,事务繁巨,涉及的机构、官员、兵丁甚多。漕运中的弊端也以新的形式出现,征收漕粮的州县官往往借机向纳户多收,此外,有些地方州县官还趁机刁难勒索运军,运军也借此要挟州县官,关系十分复杂。
漕粮征收运的机构、官员及其职掌负责漕粮征、运的官员,既有专职官,又有征漕、运漕相关诸多兼职官。中央的总负责机构是户部云南司,地方上的总负责职官位为漕运总督(设一人,正二品),驻江苏淮安府山阳县。
漕运总督掌漕粮运输,督理直隶、山东、江南等七省兵丁运漕。其下还设有直辖的“漕标”绿营,兼辖淮安城守。有漕粮的八省及直隶省的文武官员凡有漕务职掌者,都归其管辖,咸丰十年后又兼南河事务。

粮道。也称督粮道、粮储道,有专职粮道,也有兼守、巡道或其他事务的粮道。各省有设粮道的,也有不设粮道的。有漕八省所设粮道,每省一人,掌督催州县征收漕粮及各项随漕钱粮,监察兑粮,督押运漕,统辖军卫以及佥选运丁和修造漕船,并管用于漕运的钱粮经费。
监兑官。掌州县漕粮监兑上船,验米色好坏,稽查兑运之迟速,并查禁运军苛求、衙役需索及奸商包揽、掺和等事,以本省府同知、通判担任。运漕帮船开运之前,监兑官须查验,若兵丁与州县官因米色等争执,则监兑官将现兑米样封存,送漕运总督、巡抚查验。
各漕船领运者为军丁,称为运军,或称运丁、旗丁,每船一名。另配水手九名,由运军自己雇充。漕船分帮起运,每省数帮至数十帮不等,每帮漕船数十只不等。每帮以守备或千总一人为领运官,另置随帮一人,专司押运。
此外,还设巡漕御史,乾隆二年定为四人,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于运河分段巡察,稽查漕船粮米、旗丁夹带私盐及各种违禁品。此外还巡视河道,稽查河道之疏通,以及巡视仓储等。
运漕的终点是京城以东四十里的通州,设有户部仓场衙门,置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总掌漕粮之接收、储藏、保管及转运等事。下设坐粮厅,置户部司官,专掌漕粮之验收、转运输仓等事。京城、通州两处共有粮仓十五六处,每处有仓廒数十至一百多不等,每廒贮米万石。

各省漕粮的征兑截至限期为每年十一月,届时,各监兑官须坐守码头,验明米色,将各船米数兑足,面交押运官。漕船起运日期,各省不同,根据路程远近而定,南方六省的漕粮称为“南粮”,南粮定有运过淮安的时间期限,称为“过淮之限”。
漕粮由征收到运抵通州入仓,手续繁杂,运费繁巨。道光年间,关心国计民生的包世臣曾总结说:
“南粮三四百万石,连樯五千余艘,载黄达卫,以行一线运河之间,层层倒闸,节节挽牵,合计修堤防、设官吏、造船只,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虽不能知其确数,所费岁皆以千万计矣!”各种漕耗、漕费与漕粮一起征收,由漕粮纳户负担,而纳户的实际负担,要超出额定之征。各州县征收漕米之时,利用淋尖、踢斛、划削斛底、改换斛面、取样米、取斛面余米,以及利用米价的变化折征等手段,盘剥纳户。
贪官污吏利用浮收勒折中饱私囊,道光以后“浮收中饱由来已久,官民习以为常,故每办一漕,额多至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漕务败坏,是清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至道光年间,漕政败坏已是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失败的漕运改革
道光时期,漕运发生的另一大问题,是运河淤塞浅阻。道光四年,苏北一段大批漕船搁浅,不仅运输需要大量资金,而且严重影响漕粮的如期如数运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关心国计民生的官员,力图通过变河运为海运,来革除漕务中的各种弊端,并解决庞大的运河治理费用问题。
道光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任命陶澍、贺长龄等试办海运。道光六年,陶澍在上海督办海运,招集商船兑运江苏漕米160多万石,结果商船海运顺利,安全抵达天津。
由于省去了河运中各地机构的诸多规费、开支等,海运运费大大少于河运,每石漕粮运费不到一两,运期也缩短,减少了中途船耗,所雇商船也得到了利益。
海运利国、利民、利商,本来可以扩大推行,但却遭到了以河运为利益的漕务官及一些保守官员的反对。道光帝是典型的保守皇帝,行政一贯以率由旧章、谨守祖制为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变革祖制。另外,他还担忧一旦扩大海运,原以河漕为职业的大批沿河贫民、运丁水手等,将成无业之民,影响社会治安。
在试行海运之时,道光帝就把它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同时又拨款疏浚运河河道。更兼有些官员又极力反对海运,因而当改革者们正积极筹备来年海运诸事之时,道光却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为由,停止了海运。
二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由于财政拮据,又曾再次实行海运,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由上海雇商船海运至天津。咸丰初年以后,由于太平军攻占了江苏、安徽等地,加上黄河决口,改道入海,河运已极端困难,所以大部分漕粮逐渐改为海运。
河运漕粮制度的废除洋务运动兴起后,海运漕粮开始由轮船招商局承运。同治十一年,轮船招商局商人以轮船运漕,盈亏自负,每年海运漕米约二十万石。不久,南方省份的某些地区漕粮改折征银,统一在上海等地购买本色漕米,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运。
光绪四年后,轮船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进一步扩大,约为六十万石,占全部海运漕粮的一半左右,其余为人力商船办运。至光绪末年,人力商船经营海运漕粮者已所剩无几。江北的运河漕粮,同治末年以后也试办海运,但江北、山东及河南始终有少部分漕粮保留着河运,直至光绪二十二年,清廷仍在江北办理河运,其目的是“留此一线运输,以备不虞”。
随着漕粮官方军运向商运的不断转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漕粮改折并废除漕运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光绪朝,由于全国商品粮食市场的发展,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废除漕粮的征运实际上以成为可能,于是一些关心时政之士纷纷提出建议。
开始,由于钻营于漕务之利的官员们阻挠未能实行。庚子赔款后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多方开源节流以度危机,于是想废除征漕运漕,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廷宣布:
“漕政日久弊生,层层剥蚀,上耗国库,下抑民生。当次时势艰难,财用匮乏,亟宜力除靡费,逐加整顿。着自本年为始,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责成各督抚等认清厘,节省局费运费等项,悉数归公,听候户部拨用。并查明各州县向来征收浮责,责令和盘托出,悉数归公,以期汇成巨款。”谕旨下达后,有些官员提出应在江苏、浙江两省保留一百万漕粮的征收,与白粮一起运解京师,获得批准。此后,除这两省外,其他有漕省份,基本废除了漕粮的实物征收。
次年,清廷宣布废除各省的漕运屯田,裁撤所领运官及服务于运河的各河道官员。光绪三十一年,又将漕运总督一职取消。至此,历代相沿的河运漕粮制度彻底结束。只有少部分漕米仍保持本色折收,实行海运,与清王朝相始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