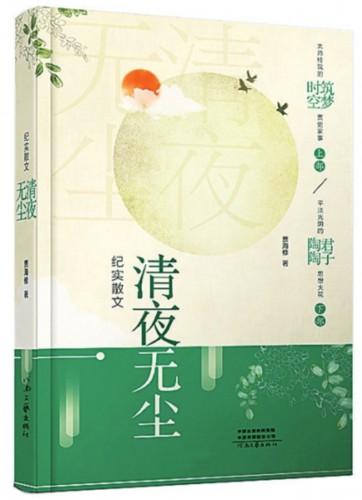
□张劭辉
作家贾海修的新书《清夜无尘》是一本纪实散文。读着书中邙山地坑院的故事,恍若自己也回到了农村老家的庭院,与故乡亲朋围炉夜话,促膝长谈。
该书以家族为切入点,从祖父祖母到兄弟子侄,从老宅旧物到乡愁乡思,从衣食住行到民俗风情,从家风家教到家国情怀,涵盖了几十年来的“贾”史家事。书中人物命运的交织、故土乡愁的情感宣泄,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作者摘下了社会赋予的面具,回到了童年的精神原乡,感动于每一个平凡生命活着的不易以及中国乡土社会的坚韧质朴和道义温情。
放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来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或许只是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但又是各自家族里的重要成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任劳任怨、身板瘦小的母亲,刚直不阿的五叔,喜欢剪纸的民间艺术家五婶,出家的堂弟……贾海修用谨慎谦卑的姿态重现着家族曾经的繁衍生息,写苦难不做强调,谈幸福不事夸张,所有的议论和修饰都被恰当地克制,记述的是流畅的生活和乐观的精神,有温度、见情感、通义理。
这些小人物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光”,支撑着中国农村几千年的文化延续,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比如《时空筑梦》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家风家训,但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家事告诉我们,为长要慈、为子要孝,为事要实、为人要真,为兄要友、为弟要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前行,正是依托于无比坚实的民间和绵延不绝的优良家风。
亲情的主线,贯穿了本书的始终。如《父亲的自行车》一文,写的是和父亲相伴多年的自行车,真正想说的则是记忆中温煦的亲情:“我坐在自行车横梁上,趴在车把上,往前能看清楚车轱辘在土路上曲折前行,看到父亲右手灵巧地摁动车铃,听到车铃传出的清脆铃铛声,在我的背后就是父亲温暖的怀抱。”
在四五十口人的大家族里,磕碰争吵在所难免。难能可贵的是,无论艰辛还是通达、公平还是不公,作者都没有丝毫责难、宣泄和评判,只是用平润的笔调把时光对成长的打磨、社会底层的艰难、人性的光辉和粗鄙等进行了客观展现,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如大伯在大家庭正困难时背弃承诺、分家另过,导致众叛亲离,但这并没有影响“大伯在我的心目中形象高大”,作者在文中一一列举了大伯的能干和贡献,认为“他焦虑的心情,我们作为晚辈是无法感同身受的,大伯应该有他的难处。”
当贾海修用文人的家国情怀去审视一个家族的过往之时,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被再次擦亮,折射出时代的光辉。《我的“履历”》中,脚上鞋子的变迁反映出我的“履历”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襁褓人怜知冷暖》通过祖孙三代坐月子不同境遇的对比,感慨“我们庆幸也欣慰我们的后代正享受着改革红利,欣欣然花枝招展地开枝散叶,过着我们从没有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回顾往昔、映射当下的精神气度。
《清夜无尘》一书,大多采用通俗的白话,甚至夹杂着中原乡村特有的俚语。但朴实并不代表平实,作者还擅长探寻日常生活里的幽微诗意,常常在自我的出走与回归之间找寻着精神的皈依之地。正如他在《站在十九楼窗前》中所写的那样,在办公室工作劳累之余,他经常推窗南眺,把映入眼帘的龙门山改叫“南山”,为什么?“看到那强势凸起而又谦恭匍匐的山脉,往往会有五柳先生的诗句在心田流淌……那时的我,进入了与五柳先生既相同又相通的十分鲜明的悟境”。
放下书本,掩卷沉思,亦有了新的感悟:家的珍贵并非源自它的纤尘不染,而是它如呼吸般绵长。绵延不绝的家风、细水长流的家事,源源不断地为人提供着对抗“西西弗斯式”人生的精神力量。
(《清夜无尘》,作者:贾海修,出版单位: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