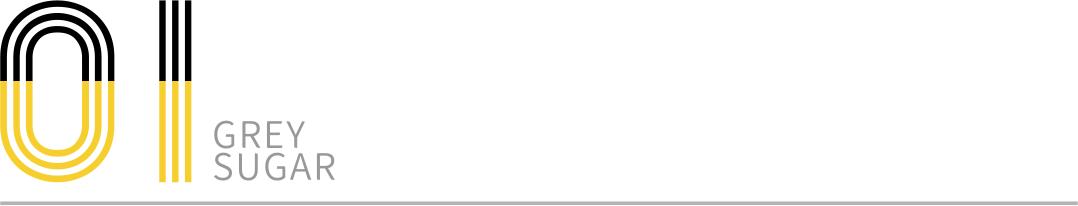阖家欢乐过大年,媳妇们燣臊子,娃娃穿新袄,男人咥干面,老汉们谝闲传。“燣”“谝”“臊”“咥”“爨”……宝鸡话中,有许多年味十足的字,这些汉字背后,有的是一段跟年有关的风俗,有的是一道独具宝鸡特色的美食,有的是一种家人团聚的年节情怀,让我们品尝汉字里的西府年味。

彘 备好年猪过大年
“咚咚锵,过年呀,猪( zhī)杀下,面打下,桌子上放个猪( zhī)尾巴,一咂一咂油啦啦。”
西府人把猪念“ zhī”,听起来好像很土气,“ u”“ i”不分,其实不然,这里说的是一个很雅的古汉语字——彘( zhì)。在《说文解字》中有解释:“彘,猪也。”宝鸡民俗专家、市民俗博物馆特邀顾问李福蔚解释,“彘”是象形字,本义指大猪、野猪,下方的“矢”字和两边的“匕”表示箭射中了野猪,现在说的彘范围扩大,泛指猪。
图片来自网络
爨 媳妇淋的醋真美
爨(cuan),简化字中笔画最多的汉字之一。《广雅》中记载,爨,炊也;《说文·爨部》载:“爨,齐谓之炊爨。臼,象持甑;冂,象炊门口;廾,推林纳火。”它的本义为烧火做饭。
其实,爨还是一个姓氏,其作为古乌蛮、白蛮的大姓,魏晋南北朝时,由今云南东部地区统治集团爨氏大姓演变而成。东晋至隋唐时,爨氏分为东爨、西爨两部 (均在云南东部 ),大抵以曲靖至建水为界,而宝鸡地区也有爨姓后裔。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宝鸡地区爨姓有近百人。在宝鸡,有不少寸姓和炊姓是从爨姓改姓而来,读音还是念 cuà n。
但对西府人而言,爨还多了一层含义:油锅一热,巧妇把切好的肉放入锅中慢慢翻炒,待文火将肥油炼出后,一勺陈醋顺着锅边滑入,一股香气扑鼻而来……这种味道,被形容为爨香爨香。
齐己《寄山中叟》诗云“紫蕨红粳午爨香”,韦庄《西塞山下作》中也留下了“爨动晓烟烹紫蕨”的佳句。这里的爨与西府方言中所表达做饭时的香味相合。
你若问,爨到底是何种味道?这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这种味道伴着年节发酵出无限的吉祥。俗话说,“二十六,来剥肉”。这一天,老百姓杀猪宰羊,根据食用需要,将肉切剁成大小不同的块备用。忙碌一年的西府人,无论在哪,烹调这些肉块时,都忘不了那一勺醋和辣椒。“不管走得多远 ,也忘不了妈妈做臊子面的爨味。”这是一位异国游子岁末之际留在微博上的感慨。爨,是一种复合的味道,淡淡的,西府人离不开,也戒不掉;爨,是一种发自秦人骨子里的味道,浓浓的,如同秦人的性格一般,血性、豪迈、坚毅……
新春里,食物的香味弥漫在每一桌年夜饭之中。年年岁岁,历经时间的洗涤,爨也成了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和生长的人们习惯的味道。

臊 难忘娘的臊子面
恐怕没有人比宝鸡人更能理解“臊”字的含义了。在宝鸡,几乎家家户户过年都要燣臊子、做臊子面,“臊”已经成为独具宝鸡文化特色的字符。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臊”字共有两个读音,一为 sā o,义为像尿或狐狸的气味;二为sà o,义同“羞”。“臊子”指肉末或肉丁。其实,“臊子”的“肉末或肉丁”之义,早在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出现。《水浒传》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写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鲁智深为助渭州潘家酒楼的金氏父女,找到状元桥下卖肉的“镇关西”郑屠,故意刁难他说要十斤精肉、十斤肥肉、十斤软骨,都要“细细地切做臊子”,继而激怒郑屠,最后打死郑屠。北宋时的渭州,就在今天的甘肃平凉一带,距离宝鸡很近。
与词典和古文中略有不同的是,如今的臊子,多指已经做熟的肉丁。在宝鸡,人们习惯把做臊子称为燣臊子,燣,即用火炒或用火加热的意思 臊子的大概流程是:猪肉切丁,锅中倒少许油,姜末和肉一起下锅,开始用中小火炒肉;炒到锅中的油变清时,加入五香粉、葱段和干辣椒;稍炒一会儿,肉吸收了五香粉后,加入较多陈醋;经过均匀搅拌,待肉熟后,加入盐、辣椒粉,搅拌均匀即可出锅。刚出锅的臊子可以用来夹馍,放凉后的臊子可以用来炒菜、拌面。而臊子的最主要用途,当然还是用来做臊子面。
在宝鸡,尽管不同县区臊子面的做法略有不同,但公认最正宗的臊子面是岐山臊子面。岐山臊子面被誉为“神来之食”,以“薄、筋、光、煎、稀、汪、酸、辣、香”的特点享誉华夏。岐山臊子面用臊子调汤,辅以黄花菜、鸡蛋、木耳、豆腐、蒜苗等多种配菜,食用时只吃面不喝汤,相传这一习俗源自周代。一日,周文王在渭水之滨猎获一条大蛟龙,用其肉做成臊子,祭祀完毕,用臊子烹汤大宴将士。由于人多,便在汤中加入面条,规定只吃面,不喝汤,剩汤回锅,以保证人人尝到此珍馐,臊子面也因此被称为“蛟汤面”。从此以后,臊子面成为岐山人节日庆典的主食。
经过三千多年传承,如今臊子面品种越来越丰富,食俗越来越简约,回汤陋习已被摈弃,但其中的文化意蕴却历久弥新。
不论走多远,在西府游子的心目中,天下最美味的饭食,就是妈妈做的一碗臊子面。

咥 咥碗干面说丰年
过年离不开吃喝,对于西府人而言,更喜欢把“吃”叫作“咥”。
单从“咥”字的结构来看,由“口”和“至”组成,也就是说,口到的时候就是“咥”。翻阅字典,“咥”有两种解释,一是“笑的样子”,读音为 xī;二为“咬”,念 dié。西府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咥”,更偏向于后者,但也融入了前者的意思,是将两种解释有机结合起来描述的一种情景,那便是高兴地吃。
“咥”是西府人吃饭的一种方式,从字面来解读,就是吃到极致的那种状态。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都会被热情地招待一番,臊子面、花馍馍、荤菜素菜一大桌,“好好咥”自然是少不了的。
西府人待客,臊子面是少不了的。当薄如蝉翼、筋道光亮的面条从滚沸的锅里捞出来时,旁边锅里的臊子汤也早已翻滚不停,浇一勺汤,油花就能“嗖”地一下冒上来,这个时候,别说是吃了,看着都馋人。端上桌的臊子面,要趁热的时候吃。西府人吃饭,不是细嚼慢咽,而是狼吞虎咽,并且能发出让旁观者馋涎顿生的“吸溜”声,这样酣畅淋漓,自然令人神往。一餐咥罢,不但浑身是劲儿,而且心里特别舒坦,这种境界,谁不向往呢?
“说起‘咥’字,那可形象着哩!它是西府地区的动态方言,一个字,就浓缩了西府人吃的一种方式。”民间学者解释说,“咥”这一姿态普遍存在于西府农村,尤其是在农忙时节,这种情景比比皆是——男人们干完活,媳妇们早已擀好了面,不用坐席,也无须规矩,随便在墙根下、槐树旁、大门口……三五个人一堆,或蹲或站,闲谝着这一年的庄稼收成,手中端着大老碗,碗中盛的是裤带面,油泼辣子红似火,挑起一筷头,连吞带咽就下了肚,那声音、动作和表情向外传达的就是一种豪情和粗犷,而这种豪情和粗犷正是西府人与生俱来的。
“咥”,在西府人看来,不是作秀,也不是表演,而是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所养成的生活习惯,通过吃展现出了一种豪迈性情。

屋 放置温暖的家园
屋,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字,西府人对屋更是有着不一样的情感。离开家去了某地,会说刚从屋里过来;邀请亲友来家里做客,会说有空来屋里坐坐;有朋友上门拜访,会说赶紧往屋里走;让媳妇给客人准备饭菜,会说让我屋里人给做几个菜;特别是每逢年关,西府人要扫舍的时候,会说把屋里“打折”(打扫)一下。
其实,屋在刚出现的时候本义是幄,后来“屋”专指房屋,另造“幄”字。《说文解字》中,徐灏曰:“古宫室无屋名。古之所谓屋,非今之所谓屋也。”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屋,属于会意字。从尸,从至。尸指“人体不动”,至表示“最终落地(处)”。“尸”与“至”联合起来表示“来到最终落脚处后身体躺下不动弹了”。从字形结构也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印象中,屋里,才是人们最舒服、最安心的地方,这就与“舒服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的俗语相互印证。
除了“屋”字本身外,房屋建造和宝鸡也有着莫大的渊源。
生于宝鸡姜水的炎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因此有了今天的炎黄子孙。他的八大功绩中有一项——台榭而居,安居乐业。其中的台榭而居,安居乐业,说的就是炎帝教族人建造房屋,使他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与如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瓦房、小洋楼不同,在原来的宝鸡农村,除了坐北朝南的正房供主人和老人住宿之外,在正房的前面还有靠墙而建的厦房。这种房子三面为土墙,只有朝向自家院子的一面开窗,能够最大限度地少使用木料等昂贵的建筑材料,有一句很久之前的俗语曾这样说:“陕西的房子半边盖”,便是这种房屋结构的写照。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土墙老房屋逐渐减少,房屋样式也越来越新潮,但藏在屋里的乡情却从未改变过。

(文章来源:宝鸡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