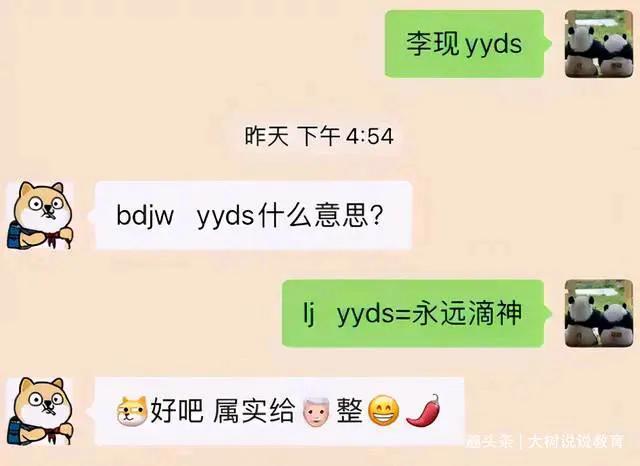未到部队之前,我们扎实羡慕军人的飒爽英姿,还非常向往部队里那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沸腾的军旅生活,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对部队按部就班的生活便有了单调枯燥乏味之感,单是那一日三餐就叫人不太适应。
开饭时间到了,排长吹哨后叫道:“开饭!”民以食为天,吃饭的事是不可或缺的,可他这里不但先要以班为单位列队站好,还要报数。一班人有理有数的就是那么几人,时时刻刻在一起,谁在谁不在,那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还报哪门子数!报数之后,得装模作样地作跑步状,至近在咫尺的集合地。瞬间各班到齐,排长又稍息、立正、向前看一番后,方带队呼喊着口号,齐步向饭堂走去。

饭堂转瞬即到,却是轻易进去不得的,各排在门前站定后,刚刚才喊过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的值班排长,又如此这般了一番,见大家屏住呼吸立正站定了,他自己则来个标准的立正、向右转,又作跑步状至连长对面,站定后,立正抬头挺胸,两眼对着连长并行举手礼,一字一句地铿锵道:“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所谓指示,一般说来当是领导机关对下级布置工作的用语,它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政策性,比如省委指示、县委指示,部队里的团长政委也就相当于地方的县级;营长、教导员相当于区科级,说营长指示也还勉强凑合,连长、指导员乃至排长,原本就是被指示的对象,也要发指示。初始,想着连长会谦虚客气一下,孰料这连长竟不客气地指示起来,原来在部队里,不但连长的讲话可以称为指示,就是排长乃至班长的讲话也是可以称之为指示的。
那连长分明就站在队伍一侧,与排长相距不过就是那么三五米的样子,排长还要屁颠屁颠地再作跑步状。好在这连长也还够意思,让排长叫大家“稍息”。于是那排长再跑步来至队前转达了连长的指示道:“稍息!”
大家刚变立正为稍息,刚喘了一口气,心里还想着“这排长也够辛苦”的事,连长已来到队前。这连长的套数也不少,他有话不忙着讲,在每次开口时总要来个“同志们好!”这一声不打紧,却轮到全连犯贱了,不用谁发口令,一个个都立马变稍息为立正,而且都作收腹、抬头、挺胸、两眼目视前方状……如此这般方立正站定了,那连长又立即回礼道:“请稍息。”然后大家长长出了口气,再次变立正为稍息。
“逢年过节天天战备,一日三餐唱歌列队。”一连之长指示完了,总该吃饭了吧,不行,还得放声歌唱。这部队里的唱歌,岂止是三餐前唱,他要求起床后唱,集会时唱,出营唱,回营唱,列队走在路上时唱,劳动时唱……总之没有可唱之处不唱的。

“人是铁饭是钢,到时不吃就心慌。”人生天地之间总是要吃饭的,为了吃饭,饭前无论你要怎样唱都可忍受,只要唱完了能心无旁骛地吃饭就行。
终于唱完了,谢天谢地,终于可以进餐厅坐下吃饭了。哪知连吃饭也不得安稳,首先他有吃饭时不准讲话的规定;其次,你必须洗耳恭听别人喋喋不休地读报,或念表扬稿、批评稿,念自己班的批判文章。总之,就是吃饭他也不会让你有半点的消停。
好嘛,这是公共场所,都得听你的,饭后回到宿舍,那是私人空间,你该管不了了吧。
先哲有言“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躺着不如睡着。”用贫下中农的话说就是“爹亲娘亲不如床亲”。被折腾了许久,回到宿舍,大面朝天地往床上那么一躺,原本就是我们在大学时养成的非常惬意的习惯,哪想到,这连里还真有一个不近情理的规定,叫做“不到睡觉时间不准躺着!”宁可让自己的床白白空着,也不准你躺在上面。太霸道了!

连里的规定数不胜数:不准男女生相互往来、不准串联、不准压马路、不准留长发……这不准,那不准,在宿舍里坐着总是可以的吧,可是连坐他也有规定:不得坐在床上。理由是坐在床上会把内务搞乱了。“班副班副,专管内务”,部队是十分注重内务的,仅仅为把那床破被子叠成左看一条线右看一条线像一豆腐块就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当然自己也不忍心将自个的劳动成果糟蹋了。那么就入乡随俗,就按你的规矩办,就让那豆腐块做摆设吧。不准床上坐,那就坐在马扎上以床当桌写封家书如何。
即使这样你也不得安身,排长、连长、指导员为体察民情,常到寒舍访贫问苦。你来嘘寒问暖,上级关心下级原本是件好事,可是他们一旦大驾光临了,你还得立马跳将起来,立正站好,嘴里还不忘:“报告x长,X班战士xxx正在给家里写信。”那日是排长进来,我这里如法炮制地程序化了一番后,末了还来了个“请排长指示”。排长道“请坐下”,他那态度可是相当的和蔼,笑容也是相当的可掬,临走前还说道:“写吧写吧,不打搅了,给家里报个平安,代排里向你家人问声好。”霎时一股暖流涌心房,这话多有人情味。但你让我忽而坐,忽而站,终日叫人手足无措,起坐彷徨,我就不爽。

这部队动辄就要排队,出操排队,劳动排队,就餐排队,开会排队,晚点名排队,就是周末去孟定邮局取个包裹寄封信,他也要你“俩人成排”,三人或三人以上必须“成行”,不得嘻嘻哈哈搂肩搭脖或手插裤包。
小学生都知道,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可是他就要求你必须走直线拐直角!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所为何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插秧时节正值雨季,一天下来,连裤腰带都是湿漉漉的,于是便学着贫下中农去孟定供销社卖了件蓑衣遮风挡雨,他竟然不准,还文绉绉地来了一句“雨不披蓑、雪不穿裘”。他拉大旗作虎皮,说这也是部队的规定,还反问一句:“你在哪里见过当兵的披过蓑衣?”他要你讲究军容风纪,穿戴干净整齐。这里是热带,我们恨不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还要你把那风纪扣扣着,脖子被紧紧地箍着,那是怎样的滋味?
部队还有个叫你铭记在心且必须身体力行的规定,叫做“时时处处都要讲作风”。什么是作风?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挖条沟必须笔直,垒田埂必须横平竖直,做块田要方方正正,尤其那菜地更是要精雕细刻整齐划一……总之他们是管天管地,就是如厕的时间也要统一。当然这里说的是学生连的事,在我们那男女混杂的学生连外出劳动时,到了一定的时候,排长会把男生带到一转弯处,瞅着四周无人叫道“排除大小便!动作快!”
“劳动创造财富”是一至理名言,但有些劳动就纯属无效,连排长们始终持“不争论”的对策,不愿把精力时间花在耍嘴皮子功夫上,他们抱定了对我们的奇谈怪论均不予理睬的态度,只是严肃地正告你“必须这样做!这是部队的纪律!”你若胆敢有少许违反就要叫你难堪!他们的“不争论”,看上去虽似一种强权,但也是一种无奈,因为跟我们争论可能就无宁日,索性来个“理解的你要执行,不理解的你也得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

不以规矩,何成方圆。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你既然来部队“过战士生活”,就得按军人那样生活,按军人那样训练,执行军人那样的纪律,你得按人家的规矩办。因为事情不能等达成共识才去做,你不愿做他就逼着你、拖着你去做,就是要你服从:服从命令、服从军号、服从哨声、服从班长、服从排长、服从连长,闻鸡起舞,闻风而动……总之,逼着你去习惯,等你习惯了就好了。
但是,对人来讲,又有什么是不可以习惯的呢?
开始我们都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地勉强地去做,长期的勉强、不断的实践终于升华为习惯。而一旦习惯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忍受、适应的了。许多时日过去,待一切都习以为常、驾轻就熟了,这习惯竟如影随形了,不用扬鞭自奋蹄,不用你再多说什么,就能自然而然地按照连队的规矩行事,而且不这样做倒反不自在了。
连中赵三爷,素与我善。他后来去高中当娃娃头,举凡他带的班,高考成绩就常居那个地区的前列,而且自打端起教书匠这饭碗以来,竟无人能出其右,以致但凡提到他,在他那个圈子的人都会竖起拇指,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就连未进过学校大门的引车卖浆之流也不禁会啧啧称赞。聚会时他带着他那乡土气息甚浓的老伴村花前来,我就着做东时问他:“三爷,把你的绝招妙法说来听听,让我也长长见识。”

他微微一笑道:“我哪有什么绝招妙法!还不就是部队狠抓作风那一套,依葫芦画瓢而已。”他说学生刚进校读高一时最是关键,对学生的要求近似苛刻,真要有“慈不领兵”的狠心,是一点都不能心慈手软的,就好像一匹马过沟,第一次就要逼着它过,而且非过不可!若第一次过不去,你迁就了它,那就是一锅夹生饭,以后它见到这沟就害怕,你就别再奢望它能过去,要让它养成凡是沟你都得给我过的习惯。对学生亦然,凡是我要求的你都得给我做到,做不到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磨刀不误砍柴工”,高一形成了习惯,到高二时就是坚持习惯,高三时习惯成自然,即从必然王国进入到了自由王国,此时的学生心无旁骛,一个心思就只有怎样把学习搞好的事,不用老师多说,皆能按习惯去运行,按老师教给的学习方法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自个去题海中刷题遨游。
学生的学习是任何人都无法包办和代替的,老师不能代替学生上考场,老师的职责在于让学生养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教给学生受用终生的学习方法,最终就是要让学生摆脱对老师的依赖,自个去觅取食物。此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用前辈叶圣陶的话说就是“教是为了不教”。坊间有“当今教师武艺高,不是做题就是考”之说,原来想着我们的三爷也就这些套路,殊不知竟也离不开作风、习惯。
有道是“习惯决定命运”。习惯造人,习惯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的任务就是要让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此前指导员曾多次说过作风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却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着……“有了好的作风即使不下命令不临时督促事情也都能搞好;没有好的作风即使下了命令又加临时督促也搞不好。”这话说得多好,多中肯,多透彻!
据考证:当年北洋水师的规模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甲午战争之时,中国海军完全有彻底击败日本海军之实力,结果大清吃了败仗,这就是败在了作风上。战前一个日本军官代表团参观了中国海军的舰船,武器都是从德国进口的,其先进、其气势都让日本人胆怯,可他们看到舰船上的一些水兵穿着邋遢,服装不洁,船舱里被褥凌乱,想着内务这般乱,军容风纪这般差,量必战斗力也不至强到哪里,于是他们发起了战争,在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大清。
当年,老人家在谈到对学生进行军训的必要性时说过一句话,叫做“训与不训大不一样。”用部队里的话说就是全训与半全训不一样,训练好与训练差也不一样。"苦练出精兵",这是用生命和鲜血证明了的真理。比如打仗,有的土匪骁勇剽悍,枪法出众,常年在山里神出鬼没,摸爬滚打,单兵作战的能力很强,但他们终究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的训练,只是一乌合之众,终究是成不了气候的。
兵来自民,但民在未成为兵之前充其量不过是一块璞石,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打磨,璞衣磨尽后,方能成为一块有价值的和氏璧──兵。

我们当年在锻炼期间,部队不厌其烦地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诸如稍息、立正、排队、唱歌、整理内务等方面,事后方知其目的原本就不是这样做的本身,而是意在养成良好习惯亦即他们所说的培养过硬的作风。乍看去这些东西好像和打仗无关,但雄壮之师、威武之师却是靠这些水滴石穿练就的。说得直白一点,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平时养成了过硬的作风,一旦国家有事,当兵都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在战场英勇杀敌,刺刀见红,浴血奋战,视为是自己的本分,是自然而然的事,做到了不算崇高,做不到则是耻辱。
当年国家把我们撒到部队去过战士生活,可能是在当年没有办法的办法,哪想到我们竟在这“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得到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设若我们这批人没有了在部队那段弥足珍贵的生活经历垫底,我们的人生或许会减色不少,许多人或许会像以前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会样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
如果说,从学生连中走出来的人,在与同龄人相比时还少有孬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在部队锻炼时养成的那种注重纪律讲究作风和不屈不挠的习惯。正是有了这段弥足珍贵的生活经历,我们方能有世间没有跨不过的坎,上不去的坡的胆略,而再苦再累的活在我们看来都不过是寻常之事。
当然,我们毕竟不是战士,连里对我们和对他们的战士还是很有一些“内外有别”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许多时候还表现出不愿与我们一般见识的大度,只要彼此大面上过得去就行,但他们对战士的要求就是钉是钉铆是铆那是相当的严格。
我们所在的这个130师是建国以来唯一的一支三次出境打满全场的部队!抗美援朝有它,对印自卫反击战有它,在后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当时已改编为160师)仍然有它。放眼全军,对一支部队而言,这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但是130师做到了,而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像铁锤一样,砸到那里,那里就碎。国家信任,人民放心。
当然,任何事物的最终结果都来自一个积累的过程,威武之师,压根就不是靠耍嘴皮子功夫就能说出来的。若无平素无数次看似简单乏味的诸如稍息、立正、正步走的训练,哪来在战场上静若处子,动如猛虎的威风?130师所以能获得如此殊荣当然跟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平时练就的过硬的作风相匹配!这都是我们亲身体验了的。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战前的排队、唱歌、整理内务等,乍看去这些东西好像和打仗无关,但雄壮之师、威武之师却是靠这些水滴石穿得来的。有当年的参战者回忆说,在越南高平,他们营去接手54军某营的阵地,见该军修筑的指挥工事上铺有圆木培土,内里宽敞曲折,设置非常规范。54军在野战中的这种作风给他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使他们大为感叹!
孔子曰“过而知之”,只有经历过才能知道,幼时没有玩过撒尿拌泥巴的孩子,他不会知道什么是童年。很多人都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但是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都是在离开部队以后的事。今天,当我们的子孙大都成人时,在我们看来若实在没有条件,他们大可不必刻意地去海外追求什么硕士、博士,何必将生命在无休无止的考试的路上耗尽。一个人存身立命的本事大多不可能在学校里学到,人生的许多道理也不会从老师的谆谆告诫中批发得来,平心而论,实在没有几人上班后还靠着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来建功立业打天下,学校里学到那些知识,大都是派不上用场的。真正的本事都要靠自己在沉浮中去领悟。若有可能最好也让我们的后代到部队去呆上三年两载,去从那些最平凡、最简单、最烦琐、最枯燥、最不起眼的事情做起,因为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课,是比拿到文凭获得学位更重要的事。

前些日子听一老兵说道“当兵前,死都要当兵;当兵后,死都要退伍;退伍后,死都想部队!”我们亦有此同感。说白了,这也是我们这一批人与部队始终难以割舍的情结。
当然,这都是在历经了几十年风雨之后的所谓感悟了。至于有的人至今还在捶胸顿足喋喋不休挠挠不服地纠缠什么悔不悔,其实只要自个平心静气地想想那段岁月,不论是对你是激励还是让你反感,甚而至于还将它诅咒,但是,只要一提起那段岁月若在你心中便会掀起波澜,就说明你没有把它随便遗忘,就说明岁月留痕,这就够了。
【欢迎读者朋友点击下方“助力”,为我们参加头条生机大会加一把油!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肯定与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