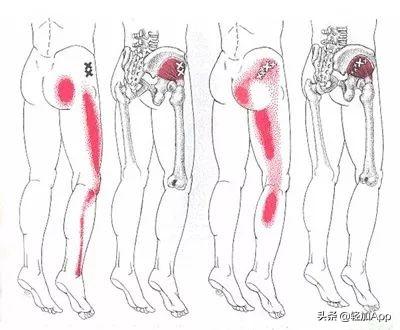臊子面第一次进入生命时,那还是在我的童年。
童年的记忆里,虽然日子过得很紧巴,但每来客人或是过年过节,母亲都要做臊子面,把客人款待得笑容满面,把节日过得喜气洋洋……
母亲能做多种地方美食,唯做臊子面一直被我认为是她最高超的手艺。
这可能是因为她做臊子面的次数太多的缘故吧!

母亲做臊子面是有程序的,总是按照一贯的流程,有条不紊地来演绎美食如何诞生。
首先是和面:放入碱水,由黄色面絮搅拌成半个枕头大小的面块。而后,盖上一个大碗,让其慢慢醒。
接下来她开始制作臊子肉:肥三瘦七的猪肉切成丁,葱姜切末,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和小茴香放碗里备用;刷净大铁锅,倒入自家产的菜籽油,灶坑里点燃劈材。等油冒起青烟,倒入肉丁快速煸炒。煸至肉吐油时放入葱姜和八角、桂皮等,继续煸炒时依次加入盐、生抽和五香粉,直到煸干肉中的水气后,再加入半勺醋与足够的温水,盖上锅盖用小火慢慢熬制。
大约三十分钟后,揭开锅盖,这时的肉已经熟透,油汪汁厚,水气已彻底散发出去。只见母亲打开瓶盖,把平时精心焙制的辣椒面倒进肉中再次煸炒,直到出现红油即可撤火盛出。
盛出的臊子肉在大碗里红灿灿的,非常地诱人;五香味裹着醋香味,在低矮的窑洞里肆意弥漫,给那个岁月添加了无尽的欢乐,给少吃无穿的日子涂抹上一道道亮丽的彩虹……

开始柔面了。
柔面是个力气活,本来手腕风湿的母亲每次都得忍受着疼痛与劳累,一脸疲惫地最少柔三遍。母亲说醒三柔三,这样做出的面条才能“薄、筋、光”
柔好的面放在案板中央,母亲开始擀。只是几分钟的功夫,一大块面就被母亲擀成了大圆饼。
紧接着就是切面。
母亲的刀功极好,手中那把黑色的长刀运用得出神入化,切出的面条不但粗细均匀,而且还非常的长,码放得也是形整不乱。

切好面,母亲又开始准备“漂菜”
打几个鸡蛋,在锅里摊成薄饼,切成菱形小片;割一把自家种的韭菜,摘洗干净切末;有时间的话再用土豆、胡萝卜和豆腐炒一碗素菜。
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就可以煮面了。
煮熟的面用凉水冲凉,一小把一小把地码放在案板上,等待“浇面”
浇面前先“煎汤”:
锅烧热加油,放入葱姜蒜爆香,烹入香醋后添水,随即放盐、酱油、五香粉烧开。汤烧开后舀两勺臊子肉,再放入备好的漂菜;如果喜欢吃辣,再加入一勺辣椒油——油红、菜绿、蛋黄……这时,一锅翻滚着“翡翠”的臊子汤就做好了!

开始浇面!
浇面是每个人都期待的时刻。
过去的碗分粗瓷和细瓷。粗瓷碗大,便宜,通常都是贫困家庭使用;细瓷碗小,昂贵,一般都是富裕家庭使用。我们家肯定是粗瓷的大碗,虽然端起来有些笨重,但用它盛面心里踏实,吃得安逸。
尽管母亲知道我等着急了,但还是不紧不慢地先拿来家里仅有的一个细瓷小碗,用筷子挑入一些面,浇上臊子汤,端出窑洞,站在院子里淋三筷子汤汁、洒几根面条,再端进窑洞,恭恭敬敬地放在日常供奉的佛龛前,方才罢休。
她说,这是“泼洒”后来才明白,母亲是在祭奠土地爷、仓神和灶神。弄完这些,无论是宾客还是主人,才能端起粗瓷大碗进入饭局。在此之前,所有人都必须竖起敬畏,怀着一颗虔诚的、自觉的心跟随母亲去遵守这个神秘规则。
只要我在家,吃第一碗面的非我莫属,这是肯定的。
家里有一个红色的小方桌,每到开饭的时候不是放在院子里就是放在炕头上,大人们围坐在一起,不让孩子靠近。而我却不理会,把一大碗面往那儿一放,摇头摆屁眼地就“呲溜、呲溜”吃起来。
吃一碗不够,“妈……再浇一碗面!”
母亲做的臊子面,说简单,的确简单;说复杂,的确复杂,其间有很多学问。
其实,家乡的臊子面百家百味,基本都遵循骨架不变、主旋律不变、灵魂不变,都是一个形式、一个目标、一个追求。
由此可见,这是传承的力量。
比如,母亲做的臊子面是跟外婆学的,外婆又是跟太婆学的,太婆又是跟太太婆学的……她们虽然不知道这就是继承传统,虽然不知道她们为祖国的餐饮文化做出了贡献,但欣慰的是,做为她们的子孙,我已深谙其道……
——11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