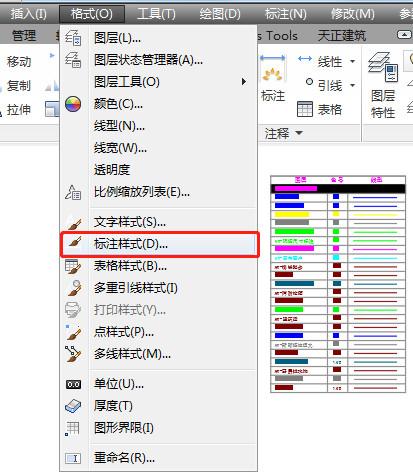徐 旭
早就想为李强写篇短文,腹稿也在脑子里晃荡了一个多月,然而,真到了要把想说的话变成白纸黑字时,我却犯难了。无论被评论者本人,还是读者,谁愿硬着头皮去看一篇毫无新意的评论呢?于是,我只好把落笔时间一再延宕了下去。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在2018年里,我既与李强面对面交流过三次,也近距离凝视了其书画创作过程,此外还出席了两个与他有关的展览。第一个,是由李强等人策展并有他参展的洛阳龙门阵现代书法展;第二个,是北京中国书画杂志美术馆举办的“妙笔生花”李强个展。

我为何要写李强?因为他在我眼里不惟是书法家与篆刻家,而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事实上,我也从未给任何一位单纯的书法家或篆刻家(即便是成就再大、造诣再高的书法与篆刻大家)写过文章。有所为、有所不为,乃是作为艺术批评工作者的我的一个为文准则。
本来,任何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滋养的为艺者,都应把书、画、印这三种艺术表达形式视为一个整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去,至少在并不遥远的1950年代以前的那些艺术大家那里,他们都是如此要求自己,也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比如,距我们较近一些的齐白石先生,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话又说回来,并非每个艺术家都能像白石老人那样达到书画印三项全能的高度,但希图用一生的努力钻研与实践,最终能在这三方面都有所成就,却是无数代以中国书画艺术作为生命与灵魂之寄托的为艺者毕生追求的理想。

然而,自中国大学从前苏联那里照搬过来了过于精细的分科教育制度后,我们的美术院校便有了中国画、书法、篆刻科系或专业的划分,而这种看似科学实乃机械刻板的学科专业划分法,却导致了自1950年代以后,以中国传统审美形式为艺术表现对象与手段的为艺者普遍变成了一条腿的跛行者;故而,多年来,鲜有如李强这样能在书画印各方面能全面发展的艺术家浮出水面。而在那些当代著名国画家与书法家们的作品画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缺憾,比如毫无章法的题款或粗糙别扭的钤印等败笔,无不说明了书画印之于中国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在此方面的修养与修为存在着极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从相反的方向来证明了:

我们时代的书画艺术,断然不可缺少如李强这类具有综合修养的为艺者。
单纯仅是因为李强在书画印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综合素养,批评家就应为他撰写文章?我以为,这样做显然缺乏对艺术本身必须保持尊重的严肃态度,具体到本人自己来说,我不能因对今天绝大多数为艺者综合修养的欠缺感到不满意,就必须为具有书画印三方面综合修养的为艺者而不吝夸赞,因为我只能为既已具备三者皆能打通之能力,且能在书画印三个领域达到较高造诣者撰写评论。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廉价赞扬式的艺术批评,而是具有责任感意识、对艺术思潮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艺术评论,后一种评论的作者应通过其批评活动把出类拔萃且具超越性的艺术家推到读者面前;与此同时,还应在文章中如实交代出此类艺术家为何应被肯定的靠谱理由。
在我眼中,以书法为出发点走上艺术探索道路的李强,的确是个舍得耗费生命中大量时间与精力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追溯中国书法史各个时期最素朴、最有力度的佳作之来龙去脉的为艺者。但凡李强能经眼到的各种率真、大气与高古之气的碑帖,莫不被他在纳入到刻苦研究、揣摩与学习的视线范围中后,再博采众家之长以滋养并成就自己独特之书风与印风;继而,再把他在书、印两个领域里的探索与实验成果,借助水墨与陶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一步步延伸或拓展到他的绘画创作中去。

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将向读者交代为何要写作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书法与篆刻,绝非两条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路径,它们在李强的脚下,是以时而并行不悖,时而交叉重叠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当这两条道路呈并行状向前延伸而去时,书法与篆刻的各自艺术特征便在各自的道路上得以显现;而当这两条道路趋向于交叉重叠之际,书法与篆刻便在交集之处发生了能量交换与互补,这种能量交换与互补的结果,便为两种同为汉字母体孕育出来的艺术形式刷新各自审美面貌带来了契机。从李强若干件极富视觉张力的书法与篆刻上乘之作中,我们可清晰透视出作者对这两种借助不同媒介呈现出来的汉字艺术形式如何在平面空间上予以创新与超越的积极思考。而基于这种复杂思考而创作出的作品,自然便是既尊重书画艺术各自在其发展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在的基本审美特性,同时又大胆越过二者之间的壁垒,把某一方的造型营养输送到另一方身上去,于是,最终使得自己的书法与篆刻因此而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情趣与视觉陌生感。而这些被李强所创新出来的面孔陌生的书法与篆刻作品,因其刷新了陈旧的审美经验,故而获得了能折射出一个时代艺术特征的功效。

在李强的“妙笔生花”个展研讨会上,石开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颇有一定道理,他说:“如果抛开时间的因素,李强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古代的大家抗衡”。
石开对李强的这一高度评价,之所以被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其理由应是,天资再高、后天再勤奋的李强,他都无法抛开时间的因素来证明他自我艺术价值的存在。如果抽离了“时间”这一至关重要因素,我们今天就无法客观评价包括李强在内的一切对中国书、画、印这三种最具民族文化精神表达形式的艺术作出鼎故革新之贡献者的功绩。

事实上,人类任何一部艺术史的书写,都是基于某一固定的垂直空间轴对某一地域范围内的艺术现象所作出的历时性叙述或描述,而一代代优秀艺术家之所以能为艺术史作出刷新记录或添砖加瓦之贡献,也都是凭借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能够给他提供的各种物质(媒介)条件,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得以实现的。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的动物。时间,赋予了人对过往历史的认知、求知与超越的欲望和能力,抽离了时间的维度,人便非人也。所以说石开先生的上面那句话,既是对李强的一种较为客观、公正与积极的肯定,同时它又是一个悖论。李强之所以能在书、画、印、瓷等领域抵达前人的艺术高度,正是如今这个科技、交通、传媒高度发达而且人类已然地球村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对一个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艺术家合力发功的结果,时代造就了李强,李强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节奏。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今年,距1898年那场惨烈的“戊戌变法”发生的时间,正好是两个花甲之年,120年来,东西方文化彼此隔绝的屏障早已被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拆除了,生活于今天这个已被数字化与网络化压缩成扁平的地球村中的以水墨为艺术表现媒介的东方艺术家,如果真能谨记明末清初时代石涛老人“笔墨当随时代”之教诲的话,那么就应当自觉从传统文人书画趣味的囚笼中挣脱出来,从而把中国书画这种地域性的艺术改造成普世性的艺术。当满目青山绿水已经因过度现代化开发而变成残山剩水之后,任何还沉浸在宋元山水画幻境中不能自拔的刻舟求剑者都是艺术的无出息者。笔墨,或水墨,如果依然停留在重复古人趣味之中,不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那么“笔墨等于零”(注:这是吴冠中先生生前的警示名言)。要想笔墨不等于,甚至无限大于零,那么,今天以水墨为媒介的书画家们,就应当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扭转传统的方向,进而,如同日本20世纪伟大的书法家井上有一、手岛右卿那样,给我们东方古老的水墨与书写性艺术带来新的生命。唯有这样,才无愧于我们今天的时代。

今年(2018年)七月底,我在威海石岛镇牧云庵书画村访问时,曾亲眼目睹了李强、邵岩、曾翔这三位以书法见长的艺术家与著名油画家程晓光的艺术跨界合作创作过程。当我站在他们四人合作完成的一幅绘画作品前作凝视状时,那并置于作品左右两边的东西方建筑符号与其它文化符号,在若干种温暖、明亮的色块的衬托下,释放出了令我无比感动的奇异光亮。我对他们的此一艺术实验成果,当然是肯定的。
于是,上面这段文字,便成为了我为何要为李强撰写此文的个重要理由之三。

不知我的读者朋友注意到了否,我的这一文本,几乎没使用一个中国传统书论与画论的关键词。其原因不是我不能,而是我有意不为之故。
为何不为?因为今天的时代要求艺术批评家必须从那些虚无缥缈、隔靴搔痒、模棱两可、悬浮在半空中的语词与不及物的语言表达模式中挣脱出来,从而走向一个澄明的言说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