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读者,我一直试着让自己的阅读口味尽可能地驳杂,以至于要读的书太多,而我却很少有时间去重读某本书,尤其是重读某本新出版的书。而林东林的这本书是个例外,作为一本刚刚上市不超过三个月的书,已经被我重读了两遍。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这么一个还算是挑剔的读者去重读这么一本既非名家又非所谓经典的书?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和林东林一样,我也是一个对普通人有着极大兴趣的人。这或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小时候是被我姥姥和姥爷带大的。我姥爷喜欢看热闹,街坊邻居但凡有点儿动静都会抱着我去看。这种看热闹的心态一直影响到我现在,以至于我对那些所谓大人物几乎从没产生过兴趣,反而倒是那些每天都能遇到人,总是会时不时地将我的目光吸引过去,以至于每当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们的生活展开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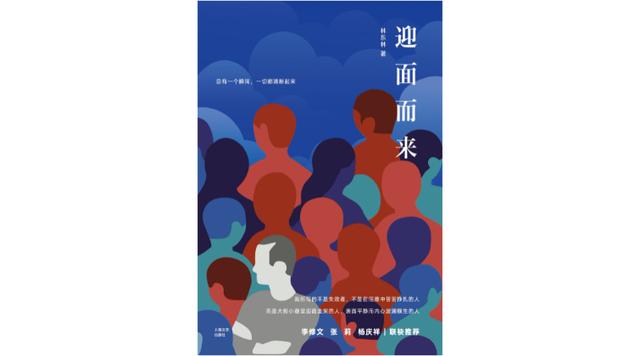
《迎面而来》,作者:林东林,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
1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通常只有两种小说能激起我重读的欲望,一种是可以为我提供新的视角,还有一种是可以加强我原有的视角。林东林的这部《迎面而来》属于后者。作家李修文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一个作家就是在发明一种观世的维度,说到底,这才是作家的根本面目。东林的小说,在常素平和中发见别情异景,在大河滔滔中探寻残流呜咽,冷静节制,又一击即中,重新唤醒读者的共情能力。”
这种“观世的维度”虽看似大巧不工,一击中地,但是同时又内在包含着一个大的技术。这种技术不完全是写作的技术,而更多是一种“看”的技术。约翰·伯格在其著作《观看之道》中写道,“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正是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地位,我们用语言解释那个世界,可是语言并不能抹杀我们处于该世界包围之中这一事实。我们见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二者的关系从未被澄清。”同样,林东林小说中的“看”,其中既有像儿童一样单纯的一面,还有老谋神算的一面。这种看,既是“好奇”,又充满了“疑惑”和“同情”。难得的是,林东林出色的语言能力将这几种不同的“看”拧成了一股力,并试图用这股力去凿开那平静生活表面上的坚冰。
2
在阅读这本《迎面而来》之前,我刚读完了美国后现代大师巴塞尔姆的《巴塞尔姆的个故事》,这两本连起来读颇有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熟悉巴塞尔姆的读者都知道,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之广泛在整个世纪几乎无人可以比肩。而林东林则不同,和文风张牙舞爪的巴塞尔姆相比,他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肯定相对要“拙”许多,“拙”到一本书读完,他想要讲的故事我全都能读懂,换句话说,就是写得很老实,每一句都能落在实处。但是,林东林的“拙”不是那种平淡得像白开水似的“笨拙”,在看上去“偏拙”的叙事过程中,时不时地会有一个近似于“突然加速”式的细节,从而让整个小说突然间变一个调子,这点让我想起了很多老派小说家,比如莫泊桑,比如欧·亨利。
以《象拔蚌先生》为例,里面的艾勇为了偷象拔蚌而差点儿丧命,这就是该小说的一次变调也是一次高潮。一个在生活重压之下的中年男人的疲惫,对平淡生活的倦怠,全都在这突然间的“纵身一跃”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纵身一跃”在故事里并不是那种直上直下似的,进去就出不来,而是像打水漂一样,跳跃在故事的湖面中,一不小心,还跳到了另外一个湖面上去,而这个湖面就在小说主人翁——“我”的心里,正如小说中写的“大海慷慨地给了他那个机会,他得到了,同时也分了一份给我。”
打过篮球的朋友们都知道,篮球场上最难防的不是那种除了快还是快的人,而是那种可以在动静之间自由切换的人。林东林虽然是一名小说界的新手,难得的是,他已经具有加速后的减速能力,这种能力经常体现在他会在加速过后,突然将情感灌注在某个事物上,用一种近似于“托物言志”的方式来为他的抒情踩刹车,无论是《遍地钟声》中的结尾处的洗碗场面还是《烈士巷》里对于小茹的黑裙子的特写,都展现出了一种良好的踩刹车的能力。而这种踩刹车虽然在语言层面上意味着一段叙事的中止,而在感受力层面上,则是一种新的感受力的开始,也就是一种“后劲儿”。我们常喝精品咖啡的人往往讲究一个“回甘”,而林东林的这种“托物言志”的方式也使得他的小说有了一种“回甘”,以不至于“小说到故事为止”。
傅雷先生曾以“讯雨”的笔名发表过一篇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的文章,说“每句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我想同样的话来形容林东林的这本《迎面而来》也毫不过分。和林东林的散文以及诗一样,林东林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调,也是那种既有肉感,又简洁的语调。在这里,我指的这种肉感,是他语调的元气都很饱满,弹性很足,不紧不慢,没有一丝的慌张。而这种饱满的语调,使得林东林的“极简”式写作和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类似于海明威式的新闻体式的“极简”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海明威为代表的新闻体式写作更多的强调一种语言的“骨感”美的话,那么相比而言,林东林则强调一种语言的“肌肉”美。这种语言的“肌肉美”并不完全是一种技巧上的处理,而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体系。
李敬泽曾说莫言、苏童还有余华这样的作家“都把各自语调完全地赋予他们笔下的世界。”我想林东林的语调和他笔下的世界,也是非常吻合的。他笔下的世界既没有任何挣脱出他的语调的意思,同时,他的语调也没有脱离开他笔下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贴合状态。以《有人将至》里的一句话为例,“就在我差不多快对宝叔产生依赖的时候,有人来到了这里。一个女的,一个跟我一样的女的。”这句话来自小说中的女主角周芸,一名被“宝叔”囚禁的当性奴的女性。从语调上看,这句话特别平静,特别拉家常。她用“一个女的”来形容“宝叔”的“新宠”的时候,就像在说家里新买了个垃圾桶一样平淡。然而,这种“平淡”甚至“冷漠”是建立在极大的绝望之下,也就是“在我差不多快对宝叔产生依赖的时候”。而这个“前提”为整个小说情节的推动增加了某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暧昧”,这种“暧昧”就是我上文中提到的那种语言的“肌肉美”,它是有弹性的。有弹性就意味着可能性,意味着周芸在此刻还没有完全屈服,并为后来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3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我还以为《迎面而来》是这本书里面的一篇小说的题目,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指这本小说的主题,也就是那些迎面而来的人。我和林东林一样,虽然都同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写作者,但是我们都不是“书斋型”的作家,而是“广场型”的。我们都喜欢四处溜达,漫步在大街上,因此我们每天都要遇到无数个“迎面而来”的人,而这些“迎面而来”的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困境。我不认为这本小说能给任何人提供某种意义上的解决之道,但是它的存在能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能否引发我们的共情?
从写作风格上讲,这部小说可能更接近左拉所提倡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力求尽可能地“客观”,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过多的道德干涉。但是同时,它又不完全是冷冰冰的记录,它又有温情的一面,像《有人将至》的结尾处,就很能体现出这种温情。虽然,林东林在这十篇小说中都以第一人称在讲述一个故事,但是即使如此,这里面的“我”对应于里面的其他人也都是“迎面而来”的“另一个人”,代入感极强。很多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小说,其视角都在“天上”,以一种近似于“摄像头”的方式在观察世界。林东林不同,他把视角直接就放进了他的口袋里,跟着他与这些“迎面而来”的人直接发生关系。这放在他口袋里的“视角”,不仅有温度,有肉感,而且还很稳。最可贵的是,它不仅对着别人,也还同时对着自己。
撰文|杜鹏
编辑|张进
校对|陈荻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