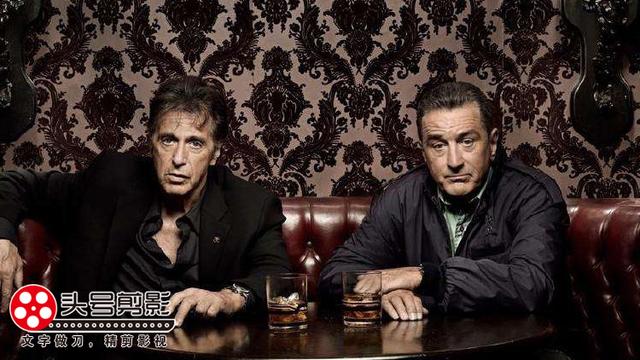小儿子
195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阳光明媚,桃花灼灼。位于洛水河畔的杨家村里,一户院子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紧接着,屋门推开,接生婆兴奋地喊道:“生了个大胖小子。”守在门外的杨老头一听,眉开眼笑,他已有了六子二女,长子已经娶妻6年,前年生了个大胖孙子,没想到他年过五十,竟又得到一个老来子,高兴地直搓手,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转眼小儿子周岁了,杨老头高兴地宴请亲朋好友与乡邻,还摆出托盘让小儿子抓周,看着摆满一盘子的各种物事,小儿子忽闪着萌萌的大眼睛,只看一眼,就左手抓起了笔,肉乎乎的右手翻动着那本厚厚的书。众人一看都高兴地说道:“了不得呀,将来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你就等着享小儿子的福吧。”朋友中有一人会看面相骨相的,他直言这孩子有富贵相,前途不可限量。杨老头一听笑得合不拢嘴。

其实杨老头的几个孩子都挺争气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大儿子勤劳能干,长得高大壮硕,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生产队长。二儿子读书好,已经学成毕业,在省城工作。那是他们村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三儿子读书一般,但是字写得漂亮,过年时村里家家户户的对联都是三儿子写的,村里小学聘请他当教师,四儿子和五儿子上初中,六儿子还在上小学,小女儿刚上一年级。可是如果能有一个更有出息的小儿子也不错呀。
从那天起,杨老头特别宝贝这个小儿子,走哪都带着。对他寄予厚望,生怕别人带不好磕着伤着。也不管那么小的孩子能不能听得懂,就开始天天按照老爹给自己启蒙的方法给才一岁孩子念叨《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那小儿子果然不负厚望,三岁时就能跟着杨老头一起背三字经,五岁时已经背了好几十首诗了,字也认了好几百个。而同村别的同龄孩子这么大还在玩尿尿泥呢,整天脏得跟个泥猴子似的,更别说什么背诗认字。杨老头乐得逢人便夸。
杨老太太更是对这个小儿子极其上心,都两岁了也舍不得给孩子断奶。尽管接下来这三年自然灾害,物质极度贫乏,她也没舍得亏待小儿子。全家人都喝稀粥,小儿子一定是白米饭拌菜,家里的第一口肉必然是小儿子吃,其他人喝野菜拌面糊糊,小儿子则吃擀得细细长长的白面条,衣服从不让小儿子穿长孙剩下的,都是买新布做新衣。
哥哥姐姐们对这个小弟弟也甚是疼爱,这个才放下怀,那个又抱起来。年节走亲戚,不管远近,小儿子几乎没走过路,都是哥哥姐姐们轮流抱着的。一直到十多岁了,农忙时节去地里干活,哥哥们拉着架子车,空车时他坐车厢里;车上装满麦子或者玉米时,一个哥哥前边拉车,其他哥哥后边推车,而他坐麦垛顶喊加油。倒不是惯坏了他,而是哥哥们太疼惜他。
不怪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实在是他太招人喜欢。
小时候长得白净圆润,眉清目秀,又聪明伶俐。6岁上小学后,一直到高中毕业一直成绩优秀。村里最有学问的一个老先生曾经断言,他将来妥妥地拿笔杆子的命,前途不可限量。
等到18岁高中毕业时,他已经成长为高大挺拔,眉眼俊朗的大男孩,又因为读书较多(杨老头祖上家底殷实,有些积蓄,虽然后来落魄了,又因为土地革命被分了田,但他父亲有先见之明,早些年兵荒马乱之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装了两大箱子埋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以备不时之需。其中一个大箱子里都是祖上藏书,杨老头趁黑偷偷翻出来给小儿子看),言谈举止,文雅又不失幽默,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来。

哥哥家的侄儿侄女们众多,读初中的,小学的,有不会的题问他,他讲解的比学校老师还清楚。
即使旁人家的孩子问他题,他也耐心解答。
他又极喜干净,常用家门口那棵大皂角树上的皂角把头发洗得干净蓬松又清香,每天衣服穿的平整熨帖,一脏就立刻换了,那么多嫂嫂侄女,有的是人给他洗衣服。每顿饭后都要漱口,和人说话,总是笑眯眯地,一口洁净白牙晃人眼。
十里八乡,再找不出比他更耀眼的少年郎。
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家里人喜欢他,乡邻们,老人艳羡杨老头有这样一个可心的儿子,青年人羡慕他风采夺人,小孩子们佩服他学识丰富,见天地想缠着他给自己讲故事。他就如一颗瞩目的明珠,被那么多人捧在手心里。
只是可惜,1976年,那个动乱的年代,上大学靠推荐,杨老头的富农身份,使得他们家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的资格。只能回家务农。
别的儿子倒还罢了,可是小儿子不能继续读书,杨老头心里就有点堵。但是看到小儿子因此有些失落,每天都闷闷不乐,却也不愿儿子就此颓废。
年近70的杨老头坚信小儿子命中注定是贵人,他用自己一辈子的人生经历劝导:“清政府变成民国,也就是一夕之间,山河日月,此消彼长,且耐心等一等,只要书装进你的脑子里,不怕没机会。”
小儿子读书多且广,想想老父亲的话,很快便内心通透了,跟着五哥六哥去参加公社集体劳动。

杨老头虽然开解了儿子,但到底心里不舒服,想想自己一大把年纪了,来日不多,还是早些把小儿子终身大事给安顿好才能安心。便给小儿子张罗起婚事来。
他们家小儿子的条件,头脑清醒的人家,但凡有个姑娘,都是上赶着想嫁的,但是杨老头不想委屈了自己心头肉般疼爱的小儿子,千挑万选,一要模样好,二要品行端,三要女红巧,四要有文化。这条件在农村可不好找,整整一年了,杨老头才在十里开外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个满足他所有条件的姑娘,但是那姑娘家里人也要求高,需得两人见面再说。没成想一见面,只聊了几句,小儿子和那姑娘都对彼此很中意,总算把亲事定下了。小儿子这年才19岁,于是两家商定,明年满20了就结婚。
定亲后,小儿子再去公社劳动,更上心了,总是用自己的知识想方设法地让大家能省力气地干更多的活,很快便被公社书记注意到了,对他另眼相看,大有锻炼提拔之意。他想既然没有机会走出去读更多的书,有更好的前途,那就做好现在的事情,也能干出名堂。他喜欢那个姑娘,特别喜欢,想给她更好的生活。
1977年10月21日,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全国各地,那就是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了。小儿子高兴地拿着报纸一路飞奔回家,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父亲,杨老头听到这个消息眼泪花都笑出来了。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儿子还年轻,没耽误多少时间,一切都还来得及。
返回工地时,小儿子把自己的高中课本都带上,准备白天干活,晚上好好复习。还让老父亲托人给他未过门的媳妇带句话,让和他明年一起参加高考。

眼见美好前途就在眼前,他白天干活更卖力,晚上读书更用功。
公社那一年的劳动任务是去邻县山区修水利工程,十几个人住一个工棚,每天晚上点灯看书影响别人休息,大冷的天,他就晚上去帐篷外披着棉被就着油灯看书复习。
这样熬了一个多月,又累又冻,一下子就病倒了,嗓子干疼,嘴唇干裂,头晕脑胀,发起烧来,中午干活时竟然晕倒了。五哥和六哥吓得要带他去医院,他觉得自己身体一向很好,便说休息一下午出一身汗烧退了就好了。工地劳动任务紧,农村人都皮糙肉厚,也没把感冒发烧当回事,五哥六哥就把他送回工篷盖了两床棉被,让好好出一身汗,自己出去干活了。晚上下工,给他带吃的,他头晕晕地摇了摇说不想吃。摸摸额头,不太烧了,便没在意。第二天早上起床上工时,五哥发现他的被子已经蹬掉,满脸通红,额头尽是豆大的汗珠子。一摸,烫得吓人,一下子就慌了,赶紧叫人,用工地的拖拉机送去县医院。
这一去,就是大半个月,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高烧持续不退,医生说,已经烧成脑膜炎了,即使治愈了,也可能有后遗症。果然,等到出院的时候,不光人瘦得脱相了,眼神也不似从前神采飞扬,看起来有点呆滞。大哥问话,他反应好半天才回答。有时候事情能说清楚,有时候一句话前言不接后语,一着急,就拿拳头直砸自己的脑袋,说一想问题就头疼。一场高烧,把脑子烧坏了。
等出院回家,杨老头看到小儿子时而清醒,时而痴傻的样子,顿时瘫在地上。等再清醒过来,只是躺着老泪,拿擀面杖打老五老六,骂他们没照顾好小七。还没打骂几下已经双手颤抖的没一丝力气,抱着小儿子痛哭。
杨老头不甘心,又打发老大老三,带着小儿子去省城找二儿子,找省城最好的医院,做好的医生,一定要治好小儿子,花多少钱都不怕,他不缺钱,他还有一箱子的古董家底,他只要他聪明可爱的小儿子好好的。
可是省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大脑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得到这个消息,杨老头一下子病倒了。
定了亲的女孩家里人得到消息,前来探望,没过多久,便打发媒人过来,委婉地提出退亲,退还了一应彩礼。
杨老头一口气出不来,自此卧床不起,杨老太太整天以泪洗面。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几个月后小儿子去南坡钩洋槐花时,一脚踩空,从半山坡翻下来,撞破了头,还摔断了腿。
休养了大半年后,外伤全好了,但是右脚不知怎么,走起路来有点跛。杨老太太用传统方法——艾灸,给小儿子治脚腕,灸的热度有点高,把脚腕的皮肤烫伤了,动不动就流脓水水,肿得厉害,还散发着阵阵臭味。
小儿子也被自己的脚腕和身上臭味给吓着了,不停地洗脚腕,换衣服,本身就流脓,水越洗越严重,最终成了伴他一生的顽疾。
发现脚再也好不了,臭味再也轰不散,他疯了似的哈哈大笑,又哇哇大哭,拿头撞墙。
杨老头死命地抱住他才慢慢平静下来。
那个冬天,把小儿子捧在手心里的杨老头含恨走了。走之前,他把六个儿子叫到跟前,把箱子里的物件一人一件,包括两个女儿,然后郑重地把小儿子托付给他们,要他们一定要照顾好小儿子,给他娶亲,哪怕山里领个丑媳妇,有点残疾的也行,让他有个伴,衣食无忧。
杨老头一走,大一点的几个儿子们就分了家,只剩下老五老六和老太太小儿子一起生活。
三年后,杨老太太也走了。老太太发现只有老五和媳妇为人忠厚老实一些,便想把小儿子托付给老五照看。可是老五一直忙着盖新房,她几次托人叫老五到她房里去,老五不是没顾上,就是房子里有人,不好话说。她又不放心把那一箱子家底交给老五媳妇。老实的老五始终没明白老娘频繁地叫他,去了却又没说下个啥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终,杨老太太只能含泪告诉小儿子,院子里的大枣树下有一个箱子,还有半箱子的物件可保他一生衣食无忧,日子过不下去了才能用,没人的时候再挖出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有事可以找五哥拿主意。
杨老太太走了之后,不到两年,老五老六也分别盖好新房搬出去单住,那么大的老院子就剩下小儿子一个人。
从小被宠溺着,做饭这样的活,他是不会干的。几个哥哥轮流叫他去家里吃饭,可是他走路一瘸一拐,慢慢吞吞,腿上还散发着阵阵臭味,时间长了大家都受不了,哥哥们再怎样,还是心疼他的,可是嫂嫂们却无法忍受。最后就打发自己孩子每天去给他送饭,这些曾经无限喜欢他的孩子们,现在一个个地嫌臭,饭碗在门口一放,喊一声“吃饭了”就跑了。
不会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也干不了,没过多久,家里脏得不像样子。孩子们送饭时,连院门都不想进了,直接放在大门口。
长姐已经五十多岁了,有自己的儿孙一大家子人,顾不上管他。比他大五岁的幺姐已经出嫁了,放心不下他,每个月过来一次给他拆洗棉被,换洗衣服,打扫卫生,做做饭,边干活边哭边骂他。后来就变成了三五个月来打扫一次,渐渐地,成了一年过年前来清扫一次,到最后,再也不来了。
有几个精明能干的嫂嫂倒是早早来给他翻箱倒柜地整理过衣服被褥,不过没整理出个啥就不再来了。
兄弟们始终记着老父亲的嘱托,商量给他张罗亲事,找个媳妇,有人给他做饭洗衣,他们也就解脱了。
可是他现在这情况实在是不好找,好不容易有一户邻村人家寻了来,说是远在外省山里的一个姑娘,是她媳妇村里人,穷得很,愿意嫁过来,啥都不嫌弃。
兄弟几个立刻同意,彩礼钱大家均摊。
一个月后,一个水灵清秀的姑娘来到杨家大院。兄弟几个一看姑娘这样子,觉得这事要黄了。可是那姑娘却收拾了一间屋子住下了,并没有嫌弃的意思,只说相处两个月时间先看看,如果行她就不走了,过年时候结婚。兄弟们都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两个月,是小儿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那姑娘勤劳能干,不怕吃苦不怕累,每天给他按时做饭,衣服被褥换洗干净,白天陪他去地里拔草,晚上一块灯下聊着天剥玉米粒。小儿子眼见着胖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笑容,眼睛里也有了光彩。脑子清醒的时候就给这不识字的姑娘讲书上的故事,常逗得她哈哈大笑。
姑娘不是一般的勤快,她把家里每个房间都彻底打扫了一遍,每个衣柜的衣服被子都翻出来洗洗晒晒,厨房也彻底清洗了一遍,比过年大扫除还尽心,不放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眼看快到寒冬腊月,兄弟们相约来到老院子找姑娘说结婚的事情。却只见大枣树下突然出现一个大土堆,走近一看,土堆边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深坑。小儿子蹲在坑边一副呆滞的模样。那个水灵清秀的姑娘早不见人影了。
杨家几兄弟想追回那半箱东西,未果。
之后再没人给小儿子说过媳妇,他又变成以前那个又脏又臭的样子。而且比之前还不如,现在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了,但凡谁要问他事情,他就捂耳朵说人家是骗子,大骗子。
总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外村有不少人去外地打工,日子渐渐过得好起来,杨家几兄弟中年轻的也带着几个成年侄子们去省城建筑工地打工挣钱。

渐渐的,哥哥们有的老了,有的常年不在家。那些个侄子打工的,上学的,都忙起来,他常常好几天也没人送一碗饭。实在饿得不行了,也去过几个哥哥家,可是只要哥哥们不在,嫂嫂们虽然也会赏他一碗饭吃,但都不搭理他,以前像仰望星星一样望着他的侄儿侄女们,也都冷冷淡淡,偷偷捂鼻子。他看到孩子们数学公式有错误,给讲解,那侄儿竟然一脸的不相信他。后来,他就不再去哥哥家了,饿得很了,他就自己一瘸一拐地门口摘点野菜,厨房胡乱弄点吃的。再后来,他也出去给村里其他人帮忙干活,不要工钱,就给一碗饭吃就行了。他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地过了余下二十年时间。
四邻八乡的,一个个都喜欢叫他干活,他多廉价呀,别人砌一天墙,要管饭还要给钱;他,只管一顿饭就行。
那些以前仰望他的人,曾经对他有多艳羡,如今就有多鄙夷,同情也是有的,但他现下实在狼狈不堪,又脏又臭,一瘸一拐,脑子又不好使,自家人都嫌弃他,别人鄙夷的神色藏都不用藏。
他只是脑子有些犯糊涂,自理能力差一些,并没有傻掉,他能听懂别人话里话外的嘲讽,亦能看懂别人脸上的神色,常常干活主动远离别人,带自己的碗,吃饭远离人群,基本不和别人说话。到后来,很多小孩常说,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他是疯子。其实他自语的,不过是早些年在爹爹怀里听过的《三字经》《千家诗》而已,他在说给爹娘听。
五哥过年回来了,会来看看他,顺便训他一顿,嫌弃他把房子弄得又脏又臭,然后给他给点钱,每天送饭吃。其他哥哥们早都不大来了。
再后来,哥哥们的日子一个比一个过得好,他们的孩子们也都争气,大多数都读书上大学,脱离了这片土地。即使没上大学的也都混得风生水起,在城里买大房子过舒适日子。哥哥嫂子们去城里哄孙子去了,好像已经没人记得他了。
只有五哥还偶尔记得过去看看他,给买点挂面和菜。这么多年,他早已学会自己做饭吃了,只不过做的不那么好吃和干净罢了。
2018年一个春天的早晨,天空阳光明媚,半山坡桃花灼灼,山脚洛河水流清澈婉转。
杨家大院那棵百年老枣树早已不再随春吐露新芽,当年院子里那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儿子,在他60岁生日那天死在了自家厨房。是村里去河边伐树的村民发现的。据说,当时,电饭锅里正煮着面,飘着几片洗得不太干净的菠菜叶,已经干在锅里。他趴在地上,着地的半边脸磕得乌青,手里拿着一双筷子,正朝向电饭锅。身上已是瘦骨嶙峋。
他活着的前二十年无限风光,中间二十年尝遍人情冷暖,后二十年鲜有人管。他的葬礼倒是来了很多人,那些近在县城,远在省城的侄儿侄女们都回来了,呼啦啦一大堆人,哀嚎着情真意切地为他送葬。
已是六旬老人,可是遗像却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照片,还是黑白的。那是他高中毕业那年的毕业照,在老房子的镜框里夹着,里边还夹着好几张他更小时候的照片,再找不到一张他18岁以后的照片了。
60年一甲子,60年一轮回。若有来生,他定不愿再世为人。可成为一棵松柏,亦或是一只飞鸟,看遍风景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