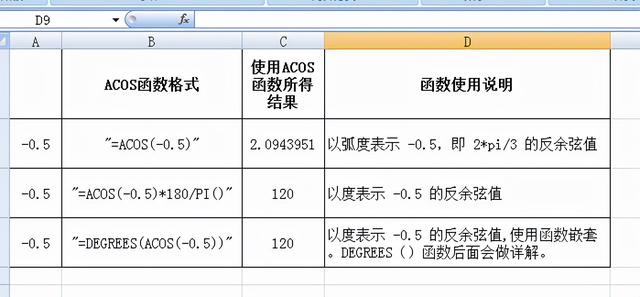导读:黄春明(1935年2月13日~),台湾当代最重要的乡土作家之一。生于台湾宜兰县罗东镇“浮仑仔”,于1962年步入文坛,其作品曾被翻译为日、韩、英、法、德语等多国语言。他的小说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亦颇负盛名。
青番公的喜悦漂浮在六月金黄的穗浪中,七十多岁的年纪也给冲走了。他一直坚持每一块田要竖一个稻草人:
“我又不要你们麻烦,十二块田做十二身稻草人,我一个人尽够了,家里有的是破笠子、破麻袋、老棕蓑;不一定每一个稻草人都打扮着穿棕蓑啊!这样麻雀才会奇怪咧。为什么每一个农夫都是一模一样呢?所以说啊!你们做的稻草人,他们头上每每都堆满鸟粪,脑袋的草也被麻雀啄去筑巢。你们知道,现在的麻雀鬼灵精的,没有用心对付是不成的了!看看我做的吧。阿明,去把稻草抱过来!”全家十几个人,只有七岁的阿明和他有兴趣去为扮十二身的稻草人忙整天。
从海口那边吹皱了兰阳浊水溪水的东风,翻过堤岸把稻穗摇得沙沙响。青番公一次扛四身稻草人,一手牵着只有稻秆那么高的阿明在田里走。
“你听到什么吗?阿明。”
“什么都没有听到。”阿明天真地回答。
青番公认真地停下来,等海口风又吹过来摇稻穗的时候又说:
“就是现在,你听听看!”他很神秘地侧头凝神地在体会着那种感觉。阿明茫然地抬头望着他。“喔!有没有听到什么?不要说话,你听!就是现在!”
“没有。”阿明摇摇头。
“没有?”青番公叫起来。“就是现在!”
阿明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随便地说:“打谷机的声音。”
“唉!胡说,那是还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深信这一季早稻,歪仔歪这个地方,我们家的打谷机一定最先在田里吼。阿公对长脚种有信心。”停了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的听见吗?”
“没有。”阿明很失望。
又一阵风推起稻浪来了。
“你没听见像突然下西北雨的那种沙沙声吗?”
“就是这个声音?”
“就是这个声音!”老人很坚决地说。“怎么?你以为什么?”当阿明在注意金穗摇动的时候,老人又说:“这就是我们长脚种的稻粒结实的消息。记住!以后听到稻穗这种沙沙声像骤然落下来的西北雨时,你算好了,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割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就是经验,以后这些田都是要给你的。他们不要田,我知道他们不要田,只要你肯当农夫,这一片,从堤岸到圳头那边都是你的。做一个农夫经验最重要。阿明,你明白阿公的话?”
小孩子的心里有点紧张,即使跻起脚尖来也看不到堤岸和圳头那边。这是多么广大的土地啊!他怎么想也想像不到这一片田都是他的时候怎么办。
“阿公,割稻的时候是不是草螟猴长得最肥的时候?”
“哼!在早稻这一季的收割期,才有草螟猴。”
“啊!真好,我又可以捉草螟猴在草堆里烧来吃。”
“草螟猴的肚子里不要忘记塞盐粒,我知道你们小孩子不愿吃盐巴,塞盐巴的草螟猴吃起来又香又不腥。到时候我会再用稻草秆做许多笼子给你关草螟猴。你要跟阿公多合作。”
风又来了。阿明讨好地说:
“阿公,我听到沙沙的声音了!”
“是,是,多好的消息。从现在开始,每粒的金谷子里面的乳浆,渐渐结实起来了。来!趁这个时候麻雀还没有来以前,快把兄弟布置好。”
“麻雀什么时候来?”
“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快把兄弟布置起来。”
“阿公!”阿明落在后头,手拿着笠子叫:“稻草人的笠子掉了!”
“嘘!”青番公马上转过身停下来说:“这么大声说稻草人,麻雀听到了我们岂不白忙?记住,麻雀是鬼灵精的,以后不要说稻草人,应该说兄弟。做一个好农夫经验最要紧,你现在就开始将我告诉你的都记起来,将来大有用处。”
他们两个蹲在田埂上,把稻草人一个一个都再整理了一番,准备从堤岸那边放回来。
阿明看看稻草人说:“阿公,兄弟怎么只有一只腿呢?”
“一只够了。我们又不叫他走路,只要他站着不动,一只脚就够了。”
当夕阳斜到圳头那里的水车磨房的车叶间,艳丽的火光在水车车叶的晃动下闪闪跳跃,他们祖孙两人已把最后一个稻草人放在那头的最后一块田里。阿明每次来到水车这里就留恋得不想回去。
“这水车磨房以前就是阿公的。”阿明兴奋地抬头望着老人。老人又说:“曾经有一段时期,歪仔歪这地方的人都不叫我青番,他们都叫我大喉咙。那时候我一直住在水车磨房这边,每天听水车哗啦哗啦地响,说话不大声就听不见,后来变成了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说话都是很大声;所以他们就叫我大喉咙了。”
“你怎么不要水车?”小孩子的眼睛注视着一片片转动的车叶,火红阳光从活动的湿湿的车叶反照过来,阿明像被罩在燃烧着的火焰中,而不受损伤的宗教画里面的人物。
“有一年我们的田遇到大洪水,整年没有收成,后来不得不就把磨房卖了。唉!歪仔歪这地方的田肥倒是顶肥的,就是这个洪水令人泄气。噢!当然,那是以前的事,现在不会了,浊水溪两边的堤岸都做起来了。从此就不再有洪水了。你放心,要给你的田,一定是最好的才给你。”
“我要水车磨房。”
“你和阿公一样,喜欢水车磨房。我们的磨房跟庄尾的不同,他们是把牛的双眼蒙着让牛推,我们用水车转动就可以。”
“为什么要把牛的眼睛蒙起来呢?”
“不把牛的眼睛蒙起来,牛一天围着磨子绕几万圈不就晕倒了嘛!水车磨房最好,不教我们做残酷的事。”
那天晚上,老人照常呼呼地睡着了。到半夜里阿明却两眼圆溜溜地听着圳头那边传来的水车声一直不能入睡。在他转换睡姿的时候把老人碰醒了。阿明赶快闭眼装睡。
“啊唉!这孩子着了魔了!怎么这么晚还不睡?不要装睡了。你不真正睡,我就把你赶回去和你母亲睡。”
“人家睡不着!”阿明说。
“我们天亮还有工作,你怎么可以不睡?一个好农夫一定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阿公,我听到那声音。”
“什么声音?”停了停:“噢!稻穗的声音吗?傻孙子,把这结穗的消息留到白天去兴奋吧。快睡了!天一亮我们就要到田里去看看兄弟。”
“阿公,那水车晚上不睡觉吗?”
“呀!原来你是在想水车的事,憨孙哩啊!老实告诉你,有一个这样比房子还大的水车是够麻烦的了,不但叫你喉咙放大,到台风季节的时候,见了无尾猴爬上海口那边的天上,就得发动十几个男人来把水车卸下来,装上扣车运到州仔尾五谷王庙的后院放下来避风,等风过了,又得请那么多人搬回去装上,为了水车,每年都被人吃了好几大桶的白米饭,和几坛绍兴坛的米酒咧。哇!什么事像你的小脑袋瓜里编的那么简单?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还是快睡吧。不早了,别人家的小孩子都正在梦见庄子里做大戏呢。”老人轻轻地笑了笑:“嗯——小孩子满脑子大锣大鼓的声音。快了,差不多割稻后两个礼拜就是我们歪仔歪谢平安做大戏的时候。但是你不睡怎会到那一天呢?”
在昏暗的八脚眠床里,老人还可以看到小孩两只出神的眼睛,像是人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那样。老人又说话,他心想总得想办法把小孩子哄睡啊:
“阿明,阿公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只有一个,听完了你就睡觉好吗?”小孩很高兴地转过身来听老人说故事:“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国王。他瞧不起老人……”说到此阿明就嚷着说:
“这个阿公早就说过了。”
“什么?这个说过了?”岂止说过了,不知已经说了几遍了,只是老人一时记不起来了。
老人特别喜欢说这一则故事给小孩子听,他觉得故事的教育意义非常正确。这故事的大意是说:一个年轻国王曾经下一道命令,把全国所有的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统统送到深山里准备把他们饿死。因为年轻国王认为老人根本没有用,他们活着只有浪费粮食。当时有一个孝子朝臣把年老的双亲偷藏在家里奉养,恰巧这时候国家遇到困难没办法解决,而这位朝臣的父亲想出了办法替国家解决了难题,年轻的国王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知道年老人经验重要,于是马上收回成命,使全国的老人又回到家园与子女团聚。
“听过了就算了。睡觉吧,再不睡觉叫老鼠公来把你咬走。”
阿明最怕老鼠,一听说是老鼠公,身体缩成一团地挤在老人的怀里。不一会的功夫,小孩子已经睡着了。老人轻轻地把小孩子的脚摆直,同时轻轻地握着小巧的小脚丫子,再慢慢地摸上来,直摸到小鸡子的地方,不由得发出会心的微笑;此刻,内心的那种喜悦是经过多么长远的酿造啊!那个时候,每年的雨季和浊水溪的洪水抢现在歪仔歪这地方的田园时,万万没想到今天,会有一个这么聪明可爱的孙子睡在身边,而竟也是男的。
他心里想:人生的变幻真是不可料啊!谁知道五六十年前那时的情形?棺材是装死人,并不是装老人啊!年老有什么不好!
年轻那一段最悲惨的经过,也是现在最值得骄傲的生活,虽然被洪水打败了,但是始终没有屈服。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在园里工作只要一挺身休息,就顺眼向大浊溪深坑一带的深山望去,要是在云霄上的尖顶,他们叫做大水帽,一连一个礼拜都被浓密的乌云笼罩着看不见的话,他们的心就惶恐起来,再看到兰阳浊水溪水比往常更浑浊而汹涌时,下游的人就开始准备搬东西了,这是歪仔歪人生存的经验。再等到深山里的雄芦啼连着几天,突然临时栖息在相思林哀啼,就开始将人员和畜生、货物疏开到清水沟丸丘上,又将横在屋檐下的竹筏放下来待用。尖顶的大水帽的失踪和雄芦啼突然的出现,是山洪暴发前几天的征兆,它的灵验性是绝对的,因此歪仔歪人才有信心生活在浊水溪的下游。
但是,有一次,半夜三更的时辰,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被突发的轰轰隆隆的像千军万马奔腾的声音吵醒了。
“阿爹,大水!”青番提醒被这声音吓呆了的父亲说,“大水来了。”
但是青番的祖父很不以为然地说:
“憨孙,大水是我们歪仔歪人最熟习的,今天我在田里还看到大水帽的全貌,同时这几天我们又没听到雄芦啼来相思林叫,这怎么会是大水呢?”
“就是。”青番的父亲附和着说。
这时轰轰隆隆震天动地的声音越来越感到逼近。老人也开始怀疑起来:
“是啊!这是大水啊!”当老人这么说,家里所有的人,把内心的极度惶恐都表现在行动上慌张起来。跑啊——,跑啊——,大水来了——外面已经有人惨绝嘶声地叫喊着,青番的老祖母和母亲都散着发跪在大庭的红色的八仙桌前天公啊地公啊地呼神叫佛。小孩子畏缩在屋檐下哀叫母亲。“阿成!快把小孩子背走——青番,你快到猪圈里把猪放生,还有牛、鸡、鸭都放了——快!女人不要哭了,快跑呀!看哪里稳就往哪里跑。”青番的祖父疯狂地喊着。
“阿公,你呢?”
“我你不用管,你还年轻快点跑!”
“阿公我带你。”
“跑!跑......”老人手拿着一根手杖,每说一字“跑”就往青番的身上狠狠地打过去。老人把手杖都打断了,青番还是没跑开。老人手拿着半截的手杖又连续打着:“你不跑我就打死你!”后来老人口里说些什么都听不清了,因为他们都哭得不成声音了。青番的眼睛被阿公打破头皮的血淹得有点模糊,但神志还很清楚,他强背着想留在屋子里的祖父往外面冲出去。外面暗得天和地都分不开,只听那已经逼上来的洪水声和人畜混乱的哀号声,当青番在稍做方向的判断的时候,水就冲到了。
青番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他躺在庄尾人的竹筏上,旁边还躺着两个肚子胀水鼓得很高而断了气的村人。
“大哥,这个年轻人还活着哪!我们撑到岸边救救看。”那个庄尾撑竹筏的年轻人说。
他们把青番运到陆地上,那个被叫大哥的人看到附近园里有人驶牛工作就喊:
“喂——把牛牵过来救人哪——”不一会儿,那人把牛牵过来了。他们把瘫软的像一条棉被的青番,面向下地横披在牛背上,然后牵着牛在原地打转,这样牛走步的震动就使青番肚子里面的浊水都吐出来了。他们还把青番放下来,用树枝拨出鼻孔里的泥沙。
“真凄惨啊!整个歪仔歪都在下面了。”那三个人望着茫茫的洪水叹息着。
这次的洪水是歪仔歪有史以来所遭受到的空前浩劫,所有的土地和那上面再迟半个月就可以收获的番薯和花生都流失,人也丧失了一大半。青番这一季五千株番薯和五大斗的花生种子的收成,都是拿来向罗东街仔人借钱盖房押青的,前几天他们在园里除杂草的时候,阿公才说:“去年我们已经把祖公的风水修起来,今年把房子盖了,明年就应该给青番讨个番婆了。”那时青番羞得猛挥着铁耙,不小心的把硕大的番薯都耙了出来。老人见了就说:
“阿成,你看你的孩子,说要给他讨个番婆就气得把番薯耙了出来。”
“管他!他不讨老婆我们省花钱也好。”
“对!对!”他们家里几个人在番薯园里乐得哈哈笑。这些,现在都随波逝去了。
祖父的尸首,第三天在下游的地方被发现,但是身上已经爬满外壳黑亮的螃蟹,而那螃蟹被抓起来摔死在地上的时候,两只毛茸茸的钳足,还牢牢地夹着将要腐化而灰白的肉丝,有的摔烂的螃蟹还流出油亮的蟹黄,这正是兰阳地区俚语所说的“春蟳冬毛虾”的初冬。青番是从那尸首的黑衣服和他右手紧握着的半截手杖认出祖父的。这样,吴家就只留下青番一个,和他二十一岁的年龄。
五六天以后,大水才算全部退掉,这时,再浮出水面的歪仔歪竟变成了一片广瀚的石头地,这比见了洪水淹没时的情景,更显得绝望。青番在石头地上抱着一颗大石头哭了整天,口里喃喃地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这次的水灾,所有的歪仔歪人都怪秋禾这个人惹来的天祸;在发大水的前一个月,很多人都看到秋禾从山上捡柴回来时,还捉了两只雄芦啼回来,当时有很多人劝他放生,但是秋禾不但没有把芦啼放生,还将芦啼杀了烤来吃掉。雄芦啼是歪仔歪人忠实的报信鸟,每年不管是大小洪水要暴发之前,雄芦啼每晚一定都在相思林那里啼叫;因为那声音很像芦竹做的芦笛声,所以歪仔歪人就叫这种鸟为芦啼鸟。村子里的人一听到芦啼的叫声,就知道提早防范洪水的来临。要是这时候作物还勉强可以提早收的就提早抢收。秋禾这次虽然在大难中得到生还,但是在歪仔歪人公愤之下,双手被绑着准备把他带到浊水溪里淹死。一个叫福助的老人对大家说:
“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我们还是问问青番和阿菊的意思看看。因为这次他们两家遇害最惨,只剩下他们两人。”
当时阿菊并不在场,她是比青番大六岁,丈夫和三个小孩也都被大水冲走了。老人又大声问在场的青番:
“青番,你的意思怎么样?把他淹死呢?或者是把他赶走?”所有在场的人的目光都落在发呆而颤抖着的青番身上。青番无意接触到秋禾的那种绝望而哀求的目光,一时禁不住地放声哭着说:放走这条狗吧——
秋禾终于被歪仔歪人把他驱逐出这块石头的荒地,听说当晚他就翻过草岭路到淡水跑帆船了。
重建这种石头荒地为田园,确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但这并不是歪仔歪人第一次的遭遇,前人来这里开垦的时候,就一直和这里的洪水抢土地,后一代的人同样地有坚强的能够化开石头的意志和劳力。他们还想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首先大家想尽了办法,勉强筹集了够请一棚外台戏的钱,在荒地上演了一场《大水戏》压水灾。那晚除了几个负责人之外,没有其他歪仔歪人去看戏,来看戏的人都是邻村的人。
戏做完了,一段漫长劳苦的日子,都掷在一层厚达三四尺覆盖泥沙土的石头上。新插植的番薯藤吸取洪水携带下来的沃土的肥汁,又带给他们生机和希望。等到番薯藤在畦间爬绿了歪仔歪的一个早晨,青番和阿菊备办了清茶四果,和金烛响炮,用谢篮装着提到顶厝仔的土地公庙烧香。他虔诚地跪在案前,手捧着圣筶,闭着眼睛口里喃喃地向土地公说:“土地公,我就是歪仔歪的吴青番,大水后新种的番薯受您的保佑已经长得很好,今天我夫妻俩特地备办清茶四果来答谢,以后我们有收成的时候,我们一定用三牲酒礼来答谢。土地公,我们还有一件事想请您给我们指点,我们想养一头母猪,不知您是不是赞成。土地公,您一定给我们指点,要是土地公赞成,请示圣筶。”说完就睁开眼睛,将圣筶拜了拜,移到右手,很慎重其事地掷在地上,圣筶卡拉清脆的一响,马上显出一阴一阳来。青番脸露出笑容,口里小声地叫着“寿杯”!他往阿菊看了看,她还跪在案前没有祷告完。青番很快地俯身拾起圣筶,又捧在手中对着土地公念念有词地说:“土地公,您要真正赞成我饲母猪,请您再现一个寿杯。”说完,又把圣筶掷在地上。这次又是一阴一阳寿杯。他虽然心里十分高兴,但是为了要饲养一头母猪也得花四五十块,这笔钱使他有点不大放心,于是又捧着圣筶说:“土地公,您真的赞成我们饲猪母吗?这关系着我们生活很大啊!我为了慎重,祈求您再应我一个寿杯。”圣筶一落地又是一个寿杯,青番乐得把阿菊的祷告岔开:
“阿菊,土地公答应我们饲猪母了,掷了三次圣筶,三次连连都寿杯咧!”
当天他们就在顶厝仔花了四十五块钱,赶一头猪母走了五里路回歪仔歪。果然没有错,饲养猪母他们叫做“土地公钱”,只要是土地公答应了就万无一失。猪母一到青番家小猪一窝一窝地生,田也一块一块地开垦起来了。所有的歪仔歪人都一样。
虽然后来洪水曾经再连续来了好多次侵扰这个地方,而歪仔歪人的意志,和流不完的汗水,总算又把田园从洪水的手中抢回来。现在每一块田都变成了良田了。老人越想越兴奋,原先的睡意全消了,对过去奋斗过来的那段生活,从没有像此刻想起来的更感到骄傲。这时他禁不住要把刚才好容易才哄睡的阿明叫醒过来,急着想告诉他这些令他骄傲的经过。
阿明被老人叫醒过来时,恼得几乎就哭出来。青番公一开头就说:
“傻孙子!哭什么?这些好田都是阿公早前用汗换来的呢!这些,都是你的了。哼!你还哭什么?”
阿明还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根本就没把阿公的话听在耳里,他梦呓地喊:“我怕!我怕!老鼠公来了,我怕……”
老人很快地把小孩子抱紧在胸前,笑着说:“阿公也真是神经!你还小嘛,我把话扯得太远了。”他装着赶走什么的,“嘶——嘶——老鼠公走开,阿明很乖的睡觉。嘶——嘶——快点跑到别地方去咬不乖的小孩子吧。”他又慈祥地对着已经睡着了的阿明说:“不用怕,阿公把老鼠公赶跑了。来,阿公摇,阿公惜,后壁沟仔三顶轿,一顶铺竹叶,一顶铺草席,一顶金交椅。阿公摇,阿公惜,前面山顶三间庙……”他一手轻拍着阿明,一边口里哼着,声音越来越小,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也安静下来了。
早起是老人的习惯,天刚要亮,青番公就悄悄地起来,拿着大杓子到牛栏里去给牛诱尿;准备浇菜。然后拿着大竹扫,把厝前厝后打扫一番。大媳妇阿贵也早就起来在厨房里忙个不停。老人看到阿贵还是很节省地将枯草送进灶肚里,每次再用火卷猛用力地向灶里吹气,而被浓浓的白烟熏得眼泪流个不停。
“还俭省什么草?下个礼拜就割稻了,到时候你用也用不完。”老人又看到阿贵拿在手里的火卷说:“呀!火卷烧得这么短了怎么不叫我再做一枝?这么短用起来太危险了,火舌一下子冲出来的话包你烧到脸,今天我就做一枝。”
“都是阿明这孩子,他看人吹火卷也要学,结果就把火卷烧去了半截。”
“噢,这个小孩子,昨晚很晚了还没睡,后来哄他说老鼠公来了他才睡了,但是他睡了我却睡不着。”
“爹,你再去睡一会儿吧。”
“噢!怎么能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哪。”说着就要踏出厨房,但突然又停下来回过头向阿贵说:“草你尽量烧吧,老是这样吹吹熄熄也不是办法。”
当他回到他的房子,阿明已经醒过来坐在八脚眠床里面呜咽地哭着。“嗳呀!这小孩子倒颓了,这么大了睡醒还哭什么?”老人一面伸手去探探被褥:“偷尿〔偷尿〕指尿床。了没有?没有偷尿你哭什么,快点下来解小便。”
太阳的触须开始试探的时候,第一步就爬满了土堤,而把一条黑黑的堤防顶上镶了一道金光,堤防这边的稻穗,还被罩在昏暗的气氤中,低头听着潺潺的溪流沉睡。清凉的空气微微地带着温和的酸味,给生命注入了精神。青番公牵着阿明到田里去。
“阿公,稻草人……”
“嘘!你又忘了。应该说兄弟,不要再忘了!”
“我们去看兄弟吗?”
“看看兄弟有没有跑去看别人的田?”
“要不要到水车那边?”
“当然要去。”
“真好!”阿明一高兴轻跃了一下,一滑脚就滑出细瘦的田埂跌倒在田里了。田里虽没有水,但是稻穗上的露水都落到阿明的身上。
“阿公,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没有,那是露水呀!阿明你看,要割稻前,露水这么重是一件好现象。这一季早稻的米粒一定很大,并且甜得很。看,多可爱的露珠哪!可惜你刚碰破了几万粒这么可爱的露珠啊!”老人显得很陶醉的样子。因此使阿明无形中觉得碰破了贵重的东西似地犯罪感而愠愠于怀。“阿明你舔舔看,露珠好甜呀。”老人轻轻而微微发颤地用手指去蘸了在稻叶脉上的一粒露珠,然后用舌头把它舔掉。“来!像阿公这样。”
太阳收缩他的触须,顷刻间已经爬上堤防,刚好使堤防成了一道切线,而太阳刚爬起来的那地方,堤防缺了一块灿烂的金色大口,金色的光就从那里一直流泻过来。昨天的稻穗的头比前天的低,而今天的比昨天还要低了。一层薄薄的轻雾像一匹很细长的纱带,又像一层不在世上的灰尘,轻飘飘地,接近静止那样缓慢而优美地,又更像幻觉在记忆中飘移那样,踏着稻穗,踏着稻穗上串系在蜘丝上的露珠,而不叫稻穗和露珠知道。阿明看着并不刺眼的硕大的红太阳,真想和太阳说话。但是他觉得太阳太伟大了,要和他说什么呢?
“阿明,你再看看太阳出来时的露珠,那里面,不!整个露珠都在转动。”
阿明照着老人的话细心地观察着露珠:
“阿公,露珠怎么会转动呢?和红太阳的红颜色在滚动一样。”
“露珠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啊!”
当他们再度注意太阳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到用晒衣杆打不到的地方了。这时候,突然从堤防那边溪里传来了两声连续的枪声,击碎了宁静,一时使阳光令人觉得刺眼和微度发烫。老人烦躁地叹了一声说:
“不会又是杀雄芦啼吧!”
“什么雄芦啼?”
“你不知道,现在没有这种鸟了,从浊水溪的堤防做起来以后,就没有人见过芦啼了。以前歪仔歪那一片相思林就有芦啼,但是它不常在那里,大水要来的时候老会出现。怪!真的都没见过芦啼了。”
“阿公谁杀了芦啼鸟呢?”
“唉!这个说来话长,以前有一个日本人来歪仔歪猎鸟,他杀了芦啼,歪仔歪人杀了那日本人,后来到法院,唉!这些你不会懂,说了也没有用,原告,被告,律师这些名词你都很陌生,我怎么讲呢?什么叫做日本人你也还不懂嘛!”青番公真想把这一段现在想起来仍然义愤填膺的经过告诉阿明,但是有这么多小孩子不能明白的名词,即使一个个都解释了也不能了解,他心里有点急。堤防那边又传来枪声。青番公听起来就像打他胸膛,他气愤地说:
“阿明,你要记住,长大了绝对不能打鸟,尤其是芦啼。”
“你不是说没有芦啼鸟了吗?”
“说不定以后会出现。还有白鹭鸶,乌这更不能伤害。就是说你不种田了,也不能伤害这些鸟。阿明你会种田吧?”
“阿公麻雀打不打?”
“也不要打,吓跑它就行了。”
他们已经来到第一块田了,稻草人斜斜站在田里,老人走过去把他扶正说:“脚酸了吗?喔!插得不够深,我还认为竹子不够牢。这样行吗?好!麻雀来了赶跑它们。”
“阿公,你和谁讲话?”阿明在田埂上这边喊着。
老人慢慢地走过来说:“我和兄弟讲话,我叫他认真赶麻雀。”
阿明感到莫名其妙地问:“稻草……”
“嘘!你又来了,这么小记性就这么坏,以后长大怎么办呢?”
“阿公,兄弟怎会听你的话?”
“怎么不会听我的话?不会听我的话就不会赶麻雀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的兄弟会不会赶麻雀,一粒稻子麻雀都不要想碰它。”
一切正如青番公所预言的,歪仔歪这地方的早稻,是他们的最先熟,他们家的打谷机最先在田里吼叫。青番公整天笑眯眯地在田里走来走去,他告诉来帮忙收割的年轻人,说长脚种的稻子只有一点坏处,就是稻秆高怕风,别地方的人不敢种,其实歪仔歪这个地方倒很适合,尤其是堤岸附近的田更适当,两三丈高的堤防长长的把海口风堵死了,强风一翻过堤防都变成柔风,那是最好的了,稻子弄花的时候,花粉传得最均匀。长脚种的稻子比其他的种早半个月熟。结穗率高,稻草打草绳、打草鞋最牢最软,牛也最喜欢吃,烧火煮饭烧茶有香味,煮起来的饭茶特别好吃。厨房烧草的烟熏房子,屋梁木柱都不会生蛀虫。
当青番公他们的田已经翻土了,稻根都朽黄了,田也放水了,附近的田里还可以听到打谷机的轰轰声。家里的大人都跑去帮别人农忙,家里只留着老人、女人和小孩,而大一点的都去上学了。阿明无心再吃草螟猴了,已经吃得腻到极点,他坐在晒谷场赶鸡。青番公把收音机里的歌仔戏节目开得很大声,他手里拿着梭叶苍蝇拍,在屋子里找苍蝇拍。阿贵走来向他说:
“老爹,中午要不要温一瓶酒?”
老人得意的,但看都不看阿贵一眼,眼睛盯在一只停在三界公灯的苍蝇说:“我正想喝一瓶哪!”
“我想中午炒了土豆,把土豆臼碎了你就有酒菜了。”
老人将媳妇的话听在心里十分高兴,一方面他在找一个适当的角度,想怎么打才不至于打到三界公灯的灯罩,而把苍蝇在空中击毙,他绕了过来说:“这只苍蝇也够狡猾了。对啦,有土豆松等一会我就去菜园拔一点香菜来和。”
“我拔回来了。”
“好,好。就温一瓶酒吧。”说完就将提得高高的苍蝇拍子猛一挥下,因为太离开三界公灯的关系,没打着了苍蝇。他很快地又在日历上发现一只,这次很轻易地连着日历打下了苍蝇。
收音机里十二点对时一过,接着就是播报地方新闻;第一条新闻就很吸引青番公。新闻称:宜兰县政府为了改善农村的生活,积极辅导农村副业,第一步已经拟就了整套的养猪贷款办法,从今天起公布实施。陈县长说,为了配合养猪计划,县府将三千多公顷山坡地开放给农民种猪菜,并特别指派专家及各地农会合作。深入农村调查......
老人心里想,那不坏啊,盖一间猪舍贷款五百块,养一头菜猪贷款两百块,养种猪猪母一头贷款九百块。那就盖一间猪舍,养一头猪母才好呀,多少年没养猪母了?不能算了,太多年了!那时候要是不养猪母,恐怕也没有今天的生活,看它生了多少窝的小猪啊!那个顶厝仔牵猪哥的猪哥文,他总要沾一点光,到处向人说他的猪哥多好多好,像青番的猪母都是叫他的猪哥来牵庚,才生出那么多小猪。这已经很久的事了,猪哥又到阴间里不会再牵猪哥了吧!不然他就要和那些年轻的专门搞人工授精的指导员,争辩热精冷精的问题。青番公想了想,决定要再养一头猪母。
土地公又赞成他养猪母,贷款的手续也办妥当了。老人带着阿明到浊水溪,撑一条鸭母船捞沙准备盖猪舍用。老人拿着竹竿站在船尾,很熟练地驶船,他大声地向坐在船头有点害怕的阿明说:
“坐在船上不能随便乱动,眼睛不要看近水头才不会晕眩。”
“阿公,我到你那里好吗?我怕。”
“不要动。怕什么?今天的浊水溪有什么可怕,水流这么少,就像一个病人要断气那样奄奄一息的。以前,以前的浊水溪,哈!流水之急啊,水面上都起了一层水雾,那声音整年就像马群在奔跑不停。做起大水来,这些地方,只要你现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都变成大海那样,一个浪一个浪把什么都吞了。上至大埔、柯林,下至下三结这一带都是浊水溪的大水路,一淹就是几千甲的土地。”老人一谈到浊水溪的语气,就像在惋吊一位大英雄人物的晚年似的,想把这位英雄再从他的口里活现。“你想想看,几千甲的土地,一个晚上就沉到水底,等土地又浮出来的时候,几千甲地都给你摆满了厚厚一层的石头。你现在看了这种水就怕,要是看以前,包你倒栽下去。”
虽然,现在的浊水溪在青番公的眼里,看起来像病人的喘息,事实上一公里宽的河床,中间有几处沙洲,山里的泥沙土混浊了整条溪水流向大海,这情景也够壮观了。在年幼的阿明看来,他是荷不起极其渺小感的恐惧心。
“阿明,看!前面那一条线就是兰阳大桥,上面有一点一点的东西跑着是不是?那就是汽车。”
“好大的桥啊!就是用走路走不完的桥是不是?”
“有三千四百五十六尺长。这很好记三四五六。”
“那个桥是谁的?”
“是大家的。谁要过都可以过。以前没有这座桥的时候,罗东这边的人要到宜兰,那时宜兰叫做葛玛兰,或者是葛玛兰的人要到罗东这边来,都要坐渡船,每坐一次渡船要一枚钱仔,现在你看不到了,圆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老人沿途就把以前的事情说给小孩听。老人又告诉小孩,说要找沙得到下游,上游只有石头,因为沙轻都流到下游。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船已经驶到桥下,小孩仰着头看桥,所看到的只是桥的各部特写而已。这时候桥的中间有两部大卡车顶在那里,双方后面也跟着停了各种各样的车排列下来。本来是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因为桥幅窄没法容纳两部大汽车交错,所以在桥头两段都设有哨兵控制着红灯绿灯的。但是这天不知怎么了,桥头两端都亮了绿灯,才造成了这种情形。
桥上一时乱成一团,双方的司机在那里争执,没有一边愿意倒退,事实上半里路的倒车也不是简单的事,从南方澳渔港运鱼要赶到南部的卡车,冰水沙沙地流下来,赶着运一车工人要往苏花公路抢救坍塌的卡车也急得要发狂,跟在后头的车,有的幸灾乐祸地按着喇叭玩,前头的互相嚷得几乎要动物。桥下的浊水溪水理都不理地默默地流。
青番公把撑竿插在水里,把船拴牢,一边看着桥上的争吵,一边又重新把浊水溪这里早前的水鬼的故事,一则一则翻出来说给阿明听:“古早古早,浊水溪有很多的水鬼,这些水鬼要转世之前,一定要找人来交替,所以啊这些水鬼就......。”而这些水鬼的故事,从这座大桥建起来,人们甩开撑渡不用以后,就很久没人再提起了,今天统统又从青番公的口中水鬼一个一个又化着缠小足的美人,在溪水边等着人来背她过水。
1967年4月10日《文学季刊》第三期
关注一往文学,每晚给你推送短篇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