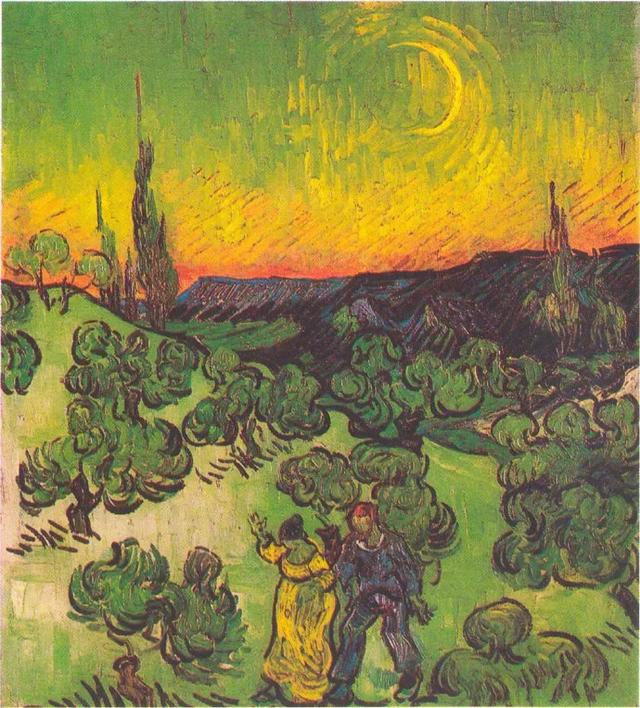↑玛沁县雪山乡,阿尼玛卿雪山下的唯格勒当雄冰川。阴柯河村的牧民昂保加(左)、旦增(中)、尖参三人正在自发进行雪线监测
红星新闻记者丨蔡晓仪 摄影记者丨陶轲 发自青海果洛
编辑丨余冬梅 何先锋
进入夏至节气,坐落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省黄河源头玛曲,平均温度依旧维持在10℃左右。三江源地区素有“中华水塔”之称,雪山已经化了一个月,融水徐徐汇入黄河,因裹挟丰富的矿物质呈现出乳白色。不出意外的话,这条母亲河的源头之水会在三江源两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雪山主峰处,来个180度的大拐弯,带着冰川融水途经切木曲支流,再一路奔腾向东南。
在江河的源头,水不仅仅是以河流的形式出现,更多的时候,水资源静默地以冻土的形式储存在草场之下,或以冰川的形式伫立在高山之巅。无论何种形式的存在,水资源对包括旦增达杰在内的当地牧民而言,都是头等大事。随着全球气候显著变暖,阿尼玛卿雪山20年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冰崩灾害。冰川脚下的雪山乡牧民们隐约意识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自2008年起,每年的5月和10月,阿尼玛卿雪山脚下,时常可见当地自发进行雪线监测的牧民和雪山乡保护站生态管护员的身影。十几年来,这群“神山守望者”穿梭在海拔4300米的冰川脚下,在天寒地冻中拉着卷尺,用油漆在岩石上标记雪线位置。牧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取了许多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用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

↑玛沁县雪山乡,阿尼玛卿雪山下红色的房子,是阴柯河村牧民旦增一家冬天的住所
1
集合
在牧民昂保加的倡导下,当地人自发组成了阿尼玛卿牧人生态环保协会,除了进行雪线监测,还会开展雪豹监测、水源监测、雕刻玛尼石和垃圾管理等环保工作。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雪山乡,35岁的旦增达杰和家人赶着200多头牛羊,从住了大半年的冬窝子举家迁到海拔4800米的夏季高山草甸牧场。旦增是雪山乡阴柯河村的牧民,冬窝子是玛沁县政府“2009年度游牧民定居工程”所建。
5月14日晚,天空飘起了雪花。旦增在家中收拾着隔天测量冰川用的装备,“卷尺、油漆、雪山监测表都要带上”。妻子在一旁为他准备糍粑等干粮。收拾完,5个孩子围着他,看他电脑里导入的雪豹捕猎视频。
15日早上8点,旦增穿好藏袍,准备下山。翻过几座山头,就能看到雪山一号隧道的高速出口。这里是三号监测点,海拔4330米,旦增要在这里和雪线监测小组的队员们集合。2006年,在牧民昂保加的倡导下,当地人自发组成了阿尼玛卿牧人生态环保协会,除了进行雪线监测,还会开展雪豹监测、水源监测、雕刻玛尼石和垃圾管理等环保工作。旦增年轻,有干劲,几个小组他都有参加。按他的话说,自己就像盐巴一样,“哪里需要撒在哪里”。
为了科学记录,近年来,牧民们商量着把雪线监测的时间固定下来,一年两次,分别是5月15日和10月15日。这两个日期他们摸索了好几年,“5月中旬是雪山刚化的时候,10月中旬天气开始变冷,雪山雪线不会融化。”
山里信号不好,牧民之间经常好几天都联系不上。但只要约定好的日子到了,他们就默契地知道要出发了。“有的像我一样从高山牧场下山,有的从100多公里外的州上(果洛藏族自治州)出发,下车后我们集合,步行到三个点位的冰川脚下测量雪线。”旦增介绍。
车还没到,旦增远远就看到了老队员多杰尖参在路口等着他,尖参带着一顶白色帽子,旁边还站着队长昂保加。尖参今年58岁,家就在高速路口附近,每年,他都会在约定好的地点迎接队友。
↑牧民昂保加(左)、旦增(中)、尖参三人正在进行雪线监测
按照计划,这一天,旦增一行人要在队长昂保加的带领下,把三个点位的冰川数据都监测完并做记录,分别是旦增家附近的哈龙冰川、尖参家附近的唯格勒当雄冰川和知亥代垭口冰川。这三座都是阿尼玛卿雪山的典型大冰川,近年来由于气候原因,表面高程整体均有所下降。
要是遇到雨雪天气,来不及赶到下一个监测点位,他们说好隔天再汇合,尽量在2天内测完。路并不好走,即使是土生土长的队员们,步行到最近的三号监测点也要近40分钟。高寒的黑色土壤上,铺满了拳头大小的岩石碎屑。遇到河水湍急处,队员们手抓着手从架起的钢管上过河。乳白色的冰川融水一年复一年地冲击,钢管也生了锈,人一站上去就嘎吱作响。
边走,尖参会边俯下身,挑出白色的石头垒在路边的玛尼堆上祈福。河边的许多石头都刻了六字真言,这是队里玛尼石雕刻小组的成果。“哪个地方有好水,我们就会在附近的石头上刻上六字真言。在山神信仰下,牧民们就不会在刻字的地方乱扔垃圾,破坏水源。”
2
监测
牧民们大部分没上过学,现场测量冰川时,他们能做的并不多。但他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得了许多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以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
海拔6282米的主峰玛卿岗日上,唯格勒当雄冰川的冰舌沿着山脊一泻而下。最先映入一行人眼帘的,是用红色油漆写着“2008.5.15”的黑色大岩石,这是队长昂保加14年前带队监测雪线时写下的,离现有冰川距离最远。这意味着,14年前的同一时间,这块岩石及同一海拔位置曾经被冰川覆盖,而如今只剩下裸露的黑石碎屑。
↑牧民尖参站在14年前他们自发监测的雪线标记处
“当时我们不懂雪线上升的具体情况,有的牧民说是几十米,有的牧民说是几百米,我们也不清楚,所以才想着监测一下。”昂保加介绍说。没有专业的设备,他们只能就地取材,找冰川前缘处不易移动的大石头,在上面用红油漆标记上具体的日期和数据。
昂保加留存了队里近十几年的雪线监测数据。其中一份雪山监测表显示,2017年10月,他们在阿尼玛卿雪山的唯格勒当雄冰川发现,冰川比前一年退后了245米,是往年的几十倍不止。
而在这一年以前,阿尼玛卿雪山刚发生了十年间的第三次大规模冰崩灾害。据当地政府通报,2016年,冰崩自海拔高程5900米的冰川顶部顺势而下,裹挟着底部炭质页岩及泥质板岩,运动过程中转化为碎屑流,堆积于海拔高程4300米的玛卿岗日冰川西侧晓玛沟沟口及青龙沟上游河谷区,并堵塞青龙沟形成堰塞湖。草场被覆盖,堰塞湖存在溃坝风险,对居住于下游的牧民构成直接威胁。
早在冰崩之前,住在山脚下的尖参就已经看到阿尼玛卿雪山的唯格勒当雄冰川在逐年退缩。在他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时,唯格勒当雄冰川一直延伸到公路的位置,“如今距离公路已经两三公里远,走路最快也要半小时才能到。”
在雪山脚下生活了35年,旦增也直观地感受到了雪山的变化。他记得,在七八岁时,离冰川近的那条河流水流量大,中午时必须骑马才能过河。“现在,那部分雪山已经化完,河里没水了。”雪山脚下生活的雪山乡牧民们隐约意识到,冰川退缩、雪线上升,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对自然的敬畏驱使着他们去守护神山。牧民们大部分没上过学,现场测量冰川时,他们能做的并不多。拉直卷尺,将雪山融化的程度、地点和时间等信息一一归档,用红色油漆在岩石上标记雪线位置,一年重复两次。牧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获得了许多冰川变化的真实数据,以朴实的行动支持着冰川保护。
昂保加介绍,环保协会刚成立时,只有6、7个牧民,现在已经扩大到66人,每年监测雪线和水源等活动的支出都由牧民们自费捐赠。2017年,协会被乡政府授予“携手牧民群众,创建绿色环保”的锦旗。
↑2017年,阿尼玛卿牧人生态环保协会被乡政府授予“携手牧民群众,创建绿色环保”的锦旗
3
协力
在赵卫东看来,近年来牧民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许多,但他们对冰川的了解还是处于低层次的阶段,“未来,我们希望能补充技术力量,实现对雪山的远程监测。”
几乎在牧民们自发进行冰川监测的同一时间地点,2009年3月,时任玛沁县自然资源局雪山乡保护站站长的才旦加也带领站里几位巡护员,出发前往阿尼玛卿雪山进行雪线监测。才旦加的父亲是雪山乡原乡长,他自幼随父亲在乡里长大,“小时候一推开门,就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壮阔的冰川。”
↑阿尼玛卿雪山下的唯格勒当雄冰川。距离2009年的冰川位置,已经退去了很远
2007年退伍后,才旦加进入保护站工作,一干就是15年。几年前骑在马上巡护时,才旦加不小心摔伤,左手总是习惯性脱臼。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全面实现园区牧户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一户一岗”,包括旦增在内的雪山乡牧民也成为玛沁县2300名生态管护员中的一员。
雪山乡保护站成立之初,全青海省的保护站一共只有4个,人力物力有限,才旦加就发动辖区内的生态管护员边放牧边做巡护工作,“一般的巡护事务性工作做完后,我们想着还能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刚好雪山乡在藏区四大神山之一的阿尼玛卿雪山脚下,我们看到冰雪融化得太快,以前整片都是白色的冰川覆盖,就从2008年开始筹划唯格勒当雄冰川的监测。”
在当时的玛沁县自然资源局,工作重心大部分放在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保护上,在许多人看来,雪山监测只是个“额外”的工作,“但雪线消退得太快了,我们就想看看十年后,到底会后退多少。”玛沁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赵卫东介绍。
↑才旦加带领组织巡护员前往阿尼玛卿雪山实地考察唯格勒当雄冰川、哈龙冰川雪崩处的变化情况 图据受访者
“第一年进山监测时,我们都非常害怕,路面的冰大部分融化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下面是黑色的沙子,前方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条黑黑的路。有时候两旁的石头滚下来,我们只能躲着走。”才旦加说,为了数据准确,他们还借来了GPS定位器,将采集的地理标本和经纬度信息标注在监测牌上。
2016年冰崩时,才旦加连续一周进山勘测,“满山都是冰川碎屑”。他发了一条朋友圈,“2004年至今是第三次阿尼玛卿雪山出现大的冰崩,听当地老人说,他们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出现过两次,2004年和2007年。现在冰崩很频繁,神山仿佛在说什么……”
↑2016年阿尼玛卿雪山冰崩时,才旦加连续一周进山勘测,几千亩草场被冰川碎屑覆盖
在赵卫东看来,近年来,牧民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许多,不仅自发监测雪线,也参与政府工作协力保护生态,“他们已经知道哪些是能干的,哪些是不能干的。尽管他们没拿工资,他们也知道应该去干。”
囿于雪线监测方式“原始”,目前牧民们对冰川的了解还是处于低层次的阶段。“未来,我们希望能补充技术力量,实现对雪山的远程监测,采集更多数据协助生态保护。”赵卫东说。
4
规划
沈永平发现,从去年到今年,各方力量都在计划启动冰雪监测等规划,“让大众对雪山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认识到遥远的雪山与每个人都有关。”
每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沈永平都会到中国西部大大小小的雪山进行科学考察。他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自1982毕业后,沈永平40年间就一头扎在冰川和水文资源研究中。他遗憾地发现,近年来,过去在冰川编目的地图航拍上有的一些小冰川,在他们实地调研时已经消失不见。
沈永平查阅数据发现,以阿尼玛卿雪山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尼玛卿雪山的雪线大概在5000米左右,2004年,雪线已经升到5200米,现在基本到5300米以上。“阿尼玛卿雪山的背面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一些小冰川的崩塌,由于没发生在雪山正面和几条大冰川上,没造成大影响,所以大家关注得比较少。”
冰川在长时间持续退缩或是稳定状态下突然出现的异常快速前进,被沈永平等冰川研究者称为“冰川跃动”,这也是近年来阿尼玛卿雪山一部分冰崩的原因之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整个青藏高原的冰川整体是在退缩的。”沈永平介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冰川编目通过人工的方式,根据航空卫星照片和地形图把中国的每一条冰川进行了数据登记,包括20多个参数,如经纬度、高程、长宽、面积、坡度等地理参数。
↑阿尼玛卿雪山下的唯格勒当雄冰川。常年雨雪冲刷下,原有的2009年雪线监测标牌倒下,此为雪山保护站2021年重设
1997年至2000年期间,国家科技部又开展冰川基础性调查研究,做了第二次冰川编目,主要通过卫星影像将大部分冰川再次做了调查,发现中国冰川大概退缩了18%左右。
“现在肯定退缩了20%不止。”沈永平介绍,气候变暖后,雪线不断上升,汛期时融水量增大,“可能以前六七月份才融雪,现在雪四五月份就开始化了。但四五月份融雪时,草场里的草还没长出来,融水只能白白流走,造成下游的春季融雪水灾;六月份草长出来时,融水都已经流完,这样就造成融雪时间与植被生长季节不匹配,植被缺水。”
在山下放牧的牧民更能敏感地感受到冰川的变化。曾经有牧民向沈永平反映,牛羊产出的奶,口感和品质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们就分析,可能是受气候的影响,当年的草长势不好,或是雨水来得晚,或是土壤发生了变化。”
沈永平做科考时,也遇到过唯格勒当雄冰川脚下的牧民,“他们每年都会在冰川前放一些石头,标记当年雪线的位置。当地政府和环保协会经常进山号召牧民保护环境,现在,牧民们已经成为当地环保的中坚力量。”
2021年底,青海省政府印发实施《中华水塔水生态保护规划》,标志着三江源中华水塔水生态保护将有章可循。在《规划》的指导下,沈永平发现,从去年到今年,各方力量都在计划启动冰雪监测等规划,“我们团队也计划,根据冰川在黄河源、长江源等地的分布和以往科考情况,确定监测哪些冰川和雪山、重点检测哪些数据、目前现有监测的不足及完善等,让大众对雪山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认识到遥远的雪山与每个人都有关。”
雪线监测完,返程的路上下起了大雨,雨从旦增的羊毛藏袍上滑下,不留痕迹。旦增只穿了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空空,随着他走路的节奏不断摆动。他哼起了小时候经常唱的藏文歌,每次来雪线监测时,丹增都很开心,“因为能看到冰川”。
如无必要,才旦加和牧民们一样,轻易不靠近冰川。雪山既神圣又脆弱,每年监测时,才旦加总不忍心踩在冰面上。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默默守望着,年复一年。
—END—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