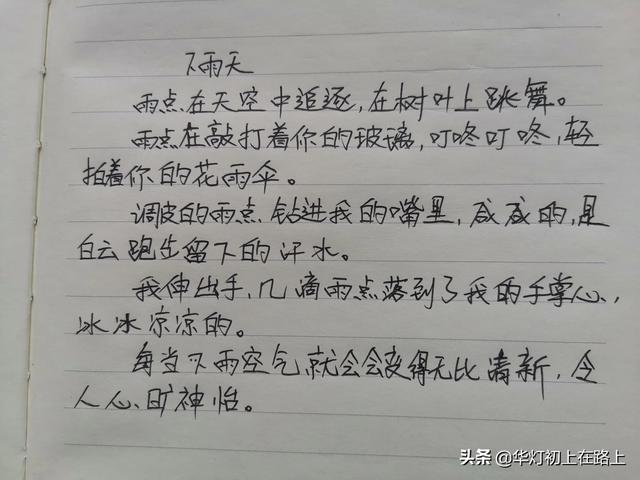今日三号,吉升万像[合十][合十][合十]感谢《西部散文选刊》公众号约稿,在今天发表我的纪实散文《记忆深处的故事》。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忆往昔看今朝深深知党恩。”我们这代人,见证了新中国从贫穷到富强的过程。 西部散文选刊 西部散文选刊 2022-01-02 14:55


主办《西部散文选刊》编辑部
2022年第1期·总第1144期

一
儿时的家在记忆里是温馨的。但是温馨中总是夹杂着因贫困而带来的丝丝苦涩。
冬去春来,草绿花开。终于挨过了漫长而寒冷的冬,跑出家门尽情地玩耍。跑累了玩饿了回家找娘要吃的。一抬头看到娘眼泪盈眶强装欢笑的面容,舔了舔上下嘴唇,把“我饿了”三个字咽回肚里。娘看出了我想说的话就问:“跑饿了吧?再忍一会儿,你达达(父亲)去表叔家借粮快回来了。”
话刚说完不大一会儿,父亲就拎着半布袋地瓜干进了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母亲脸上的愁容却依然没有散开。问父亲:“就借到这些吗?”父亲说:“表弟家粮食也不多了,他说河里化冻了,可以下河打鱼。打了鱼给咱送过来。地里的野菜也开始长了,把地瓜干压碎、掺上野菜可以凑合一阵子。”
娘没有说话,从布袋里拿出了三两片地瓜干,放到锅里煮熟后端到我的面前:“吃吧,吃吧,吃完饭看着家,我去东沙河里看看。”去东沙河干什么?东沙河里有杨树啊,应该是长出叶子来了,母亲要去东沙河里撸树叶。
我知趣地看了看碗里的地瓜干,拿了一片说:“达达和娘也吃吧,我吃一片就饱了。”
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但是谁也没有动地瓜干。地瓜干放在桌子上,从外面疯玩够了跑回家的弟弟看到后,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塞进了嘴里。
母亲从东沙河里撸回杨树叶煮熟后泡在盆里,两天后从盆里捞出来剁碎,和地瓜面掺在一起,加盐做成菜团子,我们全家改善了一次生活。那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吃的菜团。如今整天鱼、肉不断。忽然想吃娘做得那种菜团了。可是娘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想吃那种菜团需要自己动手。我去市场、去菜店、去超市,跑了许多地方就是找不到那两种食材了。杨树叶不再列入人吃的范围,地瓜面也买不到。回到老家东平农村问弟弟,弟弟说现在谁还吃那些东西呢?地瓜收下来就有下乡收购的全买走了。人们的主食是白面馒头。麦子收下来,过秤后存到面粉厂,不定时地去领面换馒头。
打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杨树叶和地瓜面这两种食材。只好用玉米面和菠菜叶替代,做出来的菜团,和小时候母亲做得那种菜团却是两种不同的味道了。

二
夏日来临,新麦子入囤,不再为吃饭发愁,却害怕暴雨来临。天一打雷,便不敢再出家门。只要大雨连续下上半天,家里的脸盆水盆就派上了用场。桌子上、门厅里、床前地下,到处都有盆盆罐罐在履行职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滴嗒嗒嗒的声音让人担心房顶会不会突然落下一块来。此时,能给全家人壮胆又带来欢乐的,就是父亲的板胡和他讲战斗故事的声音了。
板胡声声,驱赶着心内的恐惧。在父亲的鼓励下,我还会高歌一曲。此时,父亲是琴师,我是演员,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是观众了。除了唱朝阳沟和穆桂英挂帅外,父亲还教会了我两首有传承意义的歌曲。虽然歌曲的名字已经忘记,歌词和曲调依然记忆犹新。
第一首就叫妇女翻身歌吧:
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枯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毛主席,共产党,他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
受苦人当家做主人,幸福万年长。
还有一首父亲说是刘胡兰唱的: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队伍出发要上前线。
一心一意去打仗,后方的事情别挂在心间………
这两首歌曲一直印在我脑子里,每当在人生中遇到困难时我就会轻声哼唱这两首歌,就感到眼下任何困难和旧社会相比、和革命先烈们遇到的困难相比就都不算困难了。精神来了,克服困难的劲头儿也就来了。
如今住在100多平方的高楼里面,不再担心下雨房子会漏雨。回老家看看,弟弟们住的也都是水泥板盖顶的大平房,天花板上还有漂亮的图案。长方形的四合院里瓜果梨桃俱全。到了秋天果实成熟的季节,举手抬头都是好吃的水果,真正是过上吃不愁穿也不愁的日子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老家还没有电灯电话。坐在场院里看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对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印象颇深。老共产党员李月英嫂子对我说:“妹妹,好好努力吧,将来社会发展的要比电影上演的还好。所有老百姓都会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我们已经过上了。当然,这离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差很远。但是我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全民团结听党的话,这一天终究会来到。

三
清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映照在巍峨的泰山上。白云朵朵围绕着山顶飘来飘去,俨然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楼下东岳大街上人来车往。我临窗北望泰山美景,低头俯瞰街上的繁华景象,不由得思绪万千。儿时关于灯和路的记忆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村里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的照明工具都是煤油灯。我喜欢看书,就在头顶的墙上楔了个钉子,用墨水瓶自造了一个小煤油灯,瓶口缠上铁丝做成挂钩挂在墙上。在农活里劳累一天,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等弟弟妹妹都睡了,划一根火柴点亮小煤油灯看书。看着正起劲儿呢,传来了母亲的喊声:“小桂云你还不睡觉啊?这整天点灯熬油的,要花多少钱哪!”我立马吹灭灯火回答:“娘,我这就睡了呢。”母亲看灯灭了,也就不再过问。
我躺在被窝里回忆看过的内容,有时候想知道保尔•柯察金和冬妮的关系怎么样了?有时候想知道《挺进报》的命运怎样了?有时候是想知道鸣凤跳水后有没有被救?就再也睡不着,估计母亲睡着了,我再爬起来偷偷点上我的小煤油灯继续看。天长日久,我头顶墙壁上便被油烟熏出了一片黑色的印记。母亲会经常查看墙壁上那片黑颜色来断定我到底费了多少灯油。然后就是唠叨我这么大闺女了,还不知道会过日子。我沉浸在书中故事的美好里,把母亲的唠叨当作耳旁风,羞红着脸低头笑笑,行动上却依然我行我素。
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我通过考学来到了小城泰安。晚自习坐在明亮的电灯下,竟然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真的是幸福感爆棚了。
接下来的年代,经济和科技迅猛增长。仅仅几年的功夫(80年代中期)我们那封闭的小乡村不仅通了电安了电灯,还通上了电话。弟弟给我来电话报喜,告诉我家里所有的房间都安了电灯,附近小卖部里安了电话,娘让他告诉我,再有事不用写信了,打电话就行。写信听不见声音,打电话能听到声音。那时小城里虽然没有手机,学校小卖部里有电话,街上也有自助电话亭。想家了,花五毛钱就可以打电话给娘聊一会儿天。
又过了几年的时间,传呼机在青年人中流行起来。弟弟来我家帮着装修房子,腰里别上了传呼机。再后来传呼机换成了手机,通话也就更加方便了。想家时可以随时用手机和娘通话。
老一辈人经过旧社会和战争年代,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总是很容易满足。娘的脸上再也没有了愁容,整天笑眯眯的。只是有一件事谁劝也不改变主意,坚定不移的不让卖粮食。丰收了,缸里、囤里、屋顶上、院子里到处都是麦子和玉米。弟弟想趁着价位好卖掉一些,母亲不让卖,还批评弟弟没有挨过饿,不知道粮食的金贵。我和弟弟也就都一笑了之了。
从20世纪60年代我记事起到现在,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富强,人民生活也如芝麻开花步步高,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问题基本解决,。共产党和党的好政策是我们老百姓幸福的源泉,老百姓生活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深处,存留着共产党领导人民由贫穷走向富强的实况录像。记忆深处的故事,永远不可忘记。

作者简介:
张桂云(笔名慈云祥)。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精短小说 》签约作家 、《中华文学》签约作家。
作品发表于《海外文摘》《散文选刊》《精短小说》《散文诗世界》《西部散文选刊》《生态文化》《神州文学》《天池小小说》《文化艺术报》《山东商报》《齐鲁晚报》等报刊。其中有小说入选《2020中国精短小说年选》。散文、诗歌入选《中华文学》凤凰榜《已作丰熟》、《凛冬将至》、《与乡书》。著有散文集《梦里花开》,获奖若干。

主办《西部散文选刊》编辑部
2022年第1期·总第11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