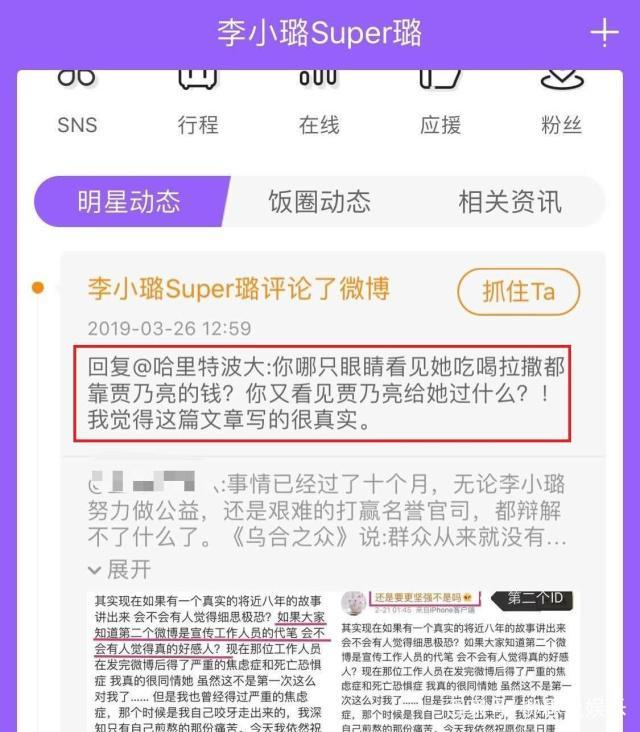安吉拉·卡特对萨德的文本采用了一种“抵抗式阅读”的路径,她从萨德这些性和血腥故事中,解构性别和色情的神话,解读隐藏在文本底下的社会观察和政治批评。同时,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也在性关系中找寻变革的可能。
“我现在要被媒体称为‘头号皮鞭女’了。”1979年,在《萨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临近出版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在写作这本书时的焦虑和担忧。
《萨德式女人》出版后,在评论界引发的争议证明,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卡特确实扔下了一颗炸弹。这本副标题为“文化史的操练”(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的书,是一本剖析萨德小说中人物原型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卡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色情观,以及她对权力结构在文本中再现和颠覆的相关批评。
当然,她也获得了一些支持性的评价——大部分来自当时的主流左翼媒体,但也引来了不少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对色情制品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那些人。比如,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将萨德视为“极端的厌女人士”,《萨德式女人》在她眼里不过是“伪女性主义批评”。还有一些评论家指责卡特以牺牲政治为代价,将美学作为特权,落入了萨德的陷阱。
时至今日,《萨德式女人》已经成为卡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色情文学批评领域极具颠覆性的文本之一,也是后人研究卡特创作和生平的入口之一。在自己的作品中,卡特本人也曾书写大量“萨德式”的场景和故事:幽暗、暴力、血腥、虐待、性倒错……最迷人之处,还是她对权力关系的再现和颠覆。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女作家,凭借《染血之室》《马戏团之夜》《焚舟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明智的孩子》等新颖无畏、独树一帜的作品,成为一代人的偶像,被萨尔曼·鲁西迪、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时至今日,她仍是女性主义的象征。
“色情产品是权力关系的外化”作为文学史上最知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构建的世界,不仅仅是色情的,也是渎神的,更是充满专制和暴力。他的作品常常被禁,本人也多次因各类“下流”行径而被捕入狱,或被关押进精神病院。在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五年半中,萨德写出了最知名的作品《索多玛的120天》。
他的所有作品,几乎没有温情和爱意;在他的笔下,剥削、控制、虐待才是世界的运行法则。
在20世纪女权主义兴起之际,这些残酷而淫荡的书写,曾遭到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在批评色情产品时,德沃金认为,对女性的仇恨本身就是男性性快感的来源,而男性的性欲是一种“醉心于对所有生命的内在蔑视,尤其是对女性生命的蔑视,可以肆意妄为”。
在德沃金那里,作为仇恨女性的男性代表人物,萨德侯爵和开膛手杰克被并列放在一起;捍卫自己享受异性性爱权利的女性,则被她认为是“合谋者”:她们甚至“比其他合谋者更卑微,在自己的劣等中体验快乐”。
卡特和德沃金对萨德的观点分歧,就源于两者对色情产品的认识不同。卡特把色情产品视为“权力关系的外化”,认为萨德的文学反映了一种“真实的两性关系”,它直指女性“长久以来处于屈从地位”这一历史现实的核心;《萨德式女人》也并非纯粹为萨德“辩护”:它“既非对萨德的批评研究,亦非对他的历史分析,而是20世纪晚期对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阐释。”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英]安吉拉·卡特著,曹雷雨、姜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卡特将色情视为一些神话原型的再现:这些神话在表面上虽然虚假,却在无意中揭露了性的现实——这是分析萨德作品如何反映真实两性关系的前提之一。在这本书的开篇,她首先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色情。在她那里,色情是一种对人类性交行为的抽象,它仿佛剥离了所有的历史、阶级和政治等事实性因素,遵循着一种“我们公认的通用语言”。她关心是这种“通用语言”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两性关系的理解。而在色情的“通用语言”中,在关于性行为的神话图式中,女性长久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由男人来处置而女人被处置,正如她在强奸中被处置一样。”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重述神话”被当做卡特最重要的成就。尽管在作品中使用了很多神话原型,但卡特并非神话的追随者;相反,她是神话的叛逆者和解构者。如果有人说她的作品有“神话色彩”,她会相当不满;在她看来,神话是由“非凡的谎言组成,旨在使人们不自由”,而她的工作是“去除神话色彩”。
卡特在《萨德式女人》里做的,就是以从分析萨德小说中的人物出发,去解构性别和色情的神话。
她首先分析了茱斯蒂娜(Justine)这个人物。茱斯蒂娜一生崇尚贞洁,她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但这些善的践行带给她的只是厄运,被强奸和性虐待,最后还不得善终,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被雷电刺穿胸腔的死亡结局。
在文学生涯中,卡特本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揭示父权制下的权力关系;在她看来,萨德将这种权力关系真实地再现了。她将萨德称为“道德色情作家”,他不会成为女性的敌人——她看重的并非淫秽书写本身,而是萨德书中“对妇女的蔑视”的揭示。
萨德给茱斯蒂娜的故事取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标题:“贞洁的厄运”。贞洁并未给茱斯蒂娜这样的女性带来福音,反而让她们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不断被剥削。卡特分析,茱斯蒂娜真正接近自由的时刻,是那些在路上的“逃亡时刻”;在这些不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也就是权力关系)的时间里,她可以暂时地摆脱奴役;一旦进入和他人的关系,她又再一次经历剥削。
卡特暗示,从萨德这些性和血腥故事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隐藏在文本底下的社会观察和政治批评。通过对这些情节和人物形象抽丝剥茧,卡特分析的其实是父权制话语是如何将女性气质建构起来的——她们都是男性欲欲望和想象建构的两种典型色情形象:“圣洁的女性”和“邪恶的女性”。
可以说,卡特对萨德的解读并没有“落入萨德的圈套”,反而在拆解萨德的神话。卡特对萨德的文本采用了一种“抵抗式阅读”的路径,它是对女性气质神话和女性在父权结构中的一种控诉。评论家埃莉诺·哈特尼(Eleanor Heartney)认为,虽然卡特绕过了萨德对女性的诋毁这一问题,但她试图超越了一种平面的、表面的解读,并从各种有见地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文本。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埃德蒙·戈登著,晓风译,守望者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颠覆权力的萨德式女人“萨德用性暴力的色情文学类型来描述女人的状况,但他相信,只有通过性暴力的手段,女人才有可能在破坏和渎神的实践中治愈社会给她们造成的伤痕。”从萨德那里,卡特看到了女性摆脱屈从地位的可能性。
与茱斯蒂娜完全相反,茱莉爱特(Juliette)是典型的“恶女”。她熟谙残酷世界的运行法则,先是利用自己的情人结识了很多权贵,周旋于其中获取利益,过着毫无良心的生活;在后来的逃亡中一路坑蒙拐骗,却总能脱离危险。对她而言,“逃脱奴役的唯一方法是拥抱恶行。”
与此同时,各种萨德书中的“非道德”性行为,比如鸡奸和性倒错,也被卡特视为权力关系颠覆的手段之一:“亵渎神圣是这些萨德式女人的基本特点。”在书中,卡特还提及了另一位重要的“萨德式女人”迪朗:一个茱莉爱特的重要女伴,一个“母亲”般的角色,却是“男子般不孕的母亲……她是长着阴茎的母亲,甚至可以强奸大自然”。
迪朗是一个跨越了传统性别气质规训的人,同时也是传统权力秩序的颠覆者。她拥有巨大的阴蒂,能够像男性那样去实践性行为,她的不育也破除了一种长期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生殖神话。她是一名生化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恶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投毒,形成了一个有着毁灭能力的、播撒瘟疫的“神”一样的角色,代表着“大自然对痛苦的漠视”。
这就是萨德式女人直面残酷法则的生存之道,而迪朗更是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因为在迪朗那里,“残酷实施的科学指令使世界重归混沌”。从萨德本人的一段经历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现实中这类萨德式女人的影子,而这个故事本身也就像是萨德小说情节的一些原型。
萨德侯爵,被称为情色小说的鼻祖。一生共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在监狱度过,作品大多都在监狱里完成。主要作品有《索多玛120天》、《艾琳和瓦尔库尔》、《闺房哲学》、《茱斯蒂娜,或曰贞洁的厄运》、《爱的罪恶》等。由于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节,后来的学者将主动的虐待症称为萨德现象( Sadism ),与马索克现象( Masochism )合称为 sadomasochism ,也即SM。
1768年4月3日,一个复活节的周日,28岁的萨德站在巴黎的胜利广场上,走向一个衣着破烂的女乞丐,她的名字叫罗丝·凯勒(Rose Keller),36岁,一个面包师的遗孀。萨德引诱罗丝·凯勒跟他走。他声称,自己需要一个能帮他整理卧室的女性。罗丝·凯勒先是犹豫,最后接受了萨德的建议。她被萨德的马车带到了一处乡村住宅。在这里,萨德控制了这个女人,把她的四肢绑在床上。
一个非常典型的萨德式酷刑场景,就这样被搭建好了:在幽暗而寂静的刑讯室一般的房间中,一根蜡烛是唯一的光源,而躺在床上的是一个恐惧的、赤身裸体的、被捆绑着的女性受害者。“行刑”结束后,罗丝·凯勒从窗户逃了出去,后来去警局报案。萨德被捕后,以私了结束此事。罗丝·凯勒撤销了起诉,她收到一笔巨额赔偿:2400法郎和价值7个法国金币的疗伤药物。
在萨德侯爵对警方叙述的事件版本中,罗丝·凯勒事先对这场“变态性行为”是知情的——也就是说,她可能在敲诈。卡特在《萨德式女人》中解读这个故事时,从中看到了受压迫个体的颠覆性力量:“一个来自第三等级的女人,一个乞丐,一个最贫穷的人,把富人特有的恶习转变成了伤害他们的武器。”
这个故事让卡特着迷,它就像萨德书写的残酷故事的一个注脚。而作为“头号皮鞭女”的卡特,也在自己的小说里,不断地再现和颠覆各类性别神话所构建起来的权力关系。
萨德侯爵诱拐罗丝·凯勒进行性虐待
“头号皮鞭女”的颠覆式色情对性别气质建构的反思,可能是卡特解构性别神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文章《前线笔记》(“Notes From the Front Line”)中,卡特谈到,1968年夏天,反文化运动的高潮使她“对作为一个女人的现实的性质产生了疑问”,开始思考关于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是“如何通过她无法控制的方式创造出来,并把它作为真实的东西推给她的”。
在出版《萨德女人》之前,她已经在尝试剖析父权制建构女性气质的路径。如果说茱斯蒂娜和茱莉爱特是女性气质的两种原型,那么她们的故事就是父权制存在的证据——几个世纪以来,父权制在一直在“掩盖”这种建构。
萨德将性视为变革性的力量,认为“女性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做爱,在她们巨大的、迄今尚未开发的性能量的推动下,她们就能以性交的方式进入历史,并在此过程中改变历史”。
卡特的文学,也在性关系中找寻变革的可能。
《新夏娃的激情》,[英] 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1972年,卡特开始写一本“萨德式”的小说,后来它被命名为《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故事有着反乌托邦色彩,把背景虚构在发生着社会动乱和失序的美国,各个武装派别如影子一般穿梭在情节里,但卡特并没有交代这些动荡的源头。
故事的主人公本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知识男精英,他在性行为方面颇有“浪荡子”的做派。抵达美国后,他先是被一个女性勾引,两人结成了一段非常激烈的性伴侣关系,其间穿插着各类污秽和渎神般的性交,而后对她造成伤害——她怀孕了,去做人流手术,差点丧失性命,失去了生育功能。
男主人公离开了这个被他伤害的女性,开始在美国大地上游荡。在途中,他被一个女权武装派别劫持,后者强行给他做了变性手术,而且是按照社会大众标准中最“完美”女性的模板打造的。在拥有女性的身体之后,她开始逃亡,经历了一系列性暴力和屈辱。
这个故事的灵感,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提瑞西阿斯(Tiresias),一个因触怒赫拉(Hera)而被惩罚变成女人的男人。书名中的“Passion”一词有受难的意思,卡特认为,提瑞西阿斯的故事仿佛暗示着,成为女人本身就意味着受难。
因触怒赫拉而变成女人的提瑞西阿斯
在书中,对传统性别神话的颠覆随处可见。比如,拥有男性身体时,他的最后一次性交是被强奸——被一个拥有四个巨大乳房的黑人“新神”所强奸,她是那个劫持他的女权武装派别的领袖。而作为女性的她,在逃亡过程中还要经历无数次的强奸。她被拐到一个极度男权的社群,这个社群是一个男诗人主导的,外表非常丑陋,只有一个眼睛一条腿,同时拥有七个女人,她们过得连猪都不如——在社群里,猪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而女人是连正常讲话都会受到严惩;她们被规定不能使用正常的语言,只能发出像动物一样的声音。
和萨德一样,卡特也爱书写性倒错。在《新夏娃的激情》中,主人公被男权领袖逼迫穿上了男子的礼服,和一个拥有完美女性形象的、穿着婚纱的男性举行了一场结婚仪式——这个情节难免让人想起萨德写过的一场同是性倒错的婚礼;而后,他们又在男权领袖的强迫和凝视中完成了性交。在逃亡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爱意——卡特说,爱是性的报复,然而这段爱情以其中一人的死亡告终。
卡特最重要的那些小说,无不是在解构和颠覆各种神话原型。她比萨德走得更远,如果说萨德的文学揭露了性别建构的神话本身,那么卡特的作品更是意图摧毁这些神话。“只有对这个世界进行猛烈的改造,并在一个绝对平等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才有(转变)的可能。”
参考资料: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安吉拉·卡特著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埃德蒙·戈登著
Catherine Gall:Are They Fact or Are They Fiction? The Sadeian Women of Angela Ca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