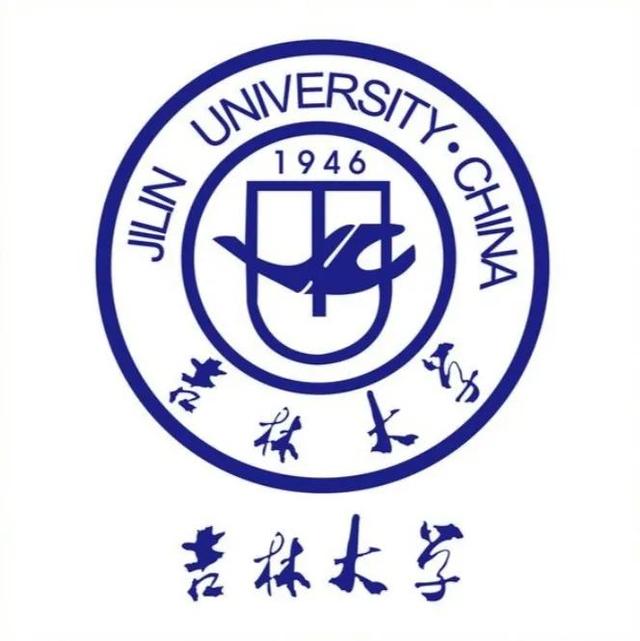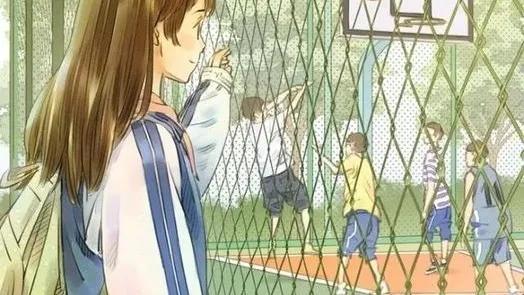距河南1500公里的广东,有320万河南人,省会广州市是大部分河南人到广东的第一站,而位于广州天河区的棠下村,则是河南人最喜欢的落脚点。这个方圆6公里的都市村庄,被人称为“岭南第一村”,也是远近闻名的“河南村”。
广州每两个出租车司机中,便有一个是河南人,而这些河南人,大多集聚生活在广州“棠下”。人们在这里喝胡辣汤、吃烩面,唱豫剧,讲河南话,男人开出租,女人做手工,俨然把老家河南的一切都搬了过来。广州为啥会有个“河南村”?村里的河南人是如何生活的?“河南村”的未来会怎样?针对这些问题,豫记华南中心的小伙伴们展开了探访。

店门口两张四方桌,红色的塑料高凳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异常显眼,三三两两的食客个个儿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噫~,今天晚上可以,跑了个大单……”,“唉!我今天不中,白忙活了一晚上。”
三十平米的门店,从昨天下午五点至此,已经迎来送往一整夜了。这家店的营业时间和一般饭店不同,下午五点到早上七点。这么诡异的营业时间,生意却异常火爆,6个工人十多个小时,几乎闲不下来。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正是一群开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而这些司机,大多来自河南。
2016年伊始,《广州日报》曾用两个版面报道《广州的哥村:全城最早苏醒的地方河南人占8成》,9月光明网也发表《探秘广州棠下“滴滴村”:聚集上万名河南司机》。
如果你到广东省会广州,你会发现每两个出租车司机里,就有一个河南人。
凌晨四点,是广州出租车交接班的高峰时间。不同于篮球明星科比“你看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的勤奋努力;也不同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中的生活美学。对于这些司机而言,凌晨四点,那是一夜的艰辛。
这些出租车司机的另外一个交接班高峰期是下午5点左右,在棠下村外的科韵路和棠德南路。每到这个时候,你都能看到长龙般等待换班的出租车。

而这两个出租车交班时间,决定了这个胡辣汤店的营业时间,这个非同寻常的营业时间背后,其实,也是一份河南人对河南人生活艰辛的体谅。
广州河南村是如何炼成的?
皆因河南的哥从厦门转战广东
据河南省统计处2013年河南人口发展报告,截止2013年底,1188万在外河南人中,有320多万流往广东;截止到2015年年末,在外河南人的数量依旧保持增涨的态势。而广东,这个距河南有1534.7公里、中国大陆最南部的省份,远超北京、浙江和江苏,始终占据在外河南人省份排名之首。
广东省省会广州,是大部分河南人到广东的第一站,而位于广州天河区的棠下村,则可以说每个河南人都广州的落脚点。天河棠下村被人称为“岭南第一村”,这个方圆6公里的都市村庄,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河南村”。

寻根溯源,天河棠下村这个“河南村”,并非一天造就的,最早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伊始,沉闷已久的人们纷纷外出淘金,周口市西华县红花镇打进楼村的金全新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校长职位之余,初尝贩卖树苗的甜头后,他愈发想要去外面挣大钱。
1992年,母亲去世再也没有人能阻拦他,他放下十年校长之位,前往厦门的老乡处寻求商机。那时的商机,就是开出租。和那些开租车的老乡不同,金全新到厦门两个月后就决定买一辆出租车。两个月后,金全新挣够买车的本钱,当时大力反对购车的老乡们也开始纷纷购入出租车。

在这些“领头羊”的带动下,西华人拉亲带友,厦门的河南籍出租车司机越来越多。在厦门,他们居住的前埔村也被称为“河南村”。
随着厦门出租车司机的不断增加,且买车费用逐渐增加,上个世纪末,有的司机便开始转战广州。当时的广州CBD天河区远没有现在繁华,租金低廉的棠下村理所应当地成为老金等司机的落脚点。

“那时候广州的出租车比厦门便宜,十几万一辆,我用那几年在厦门攒的钱,一下子买了14辆车,让俺哥、俺叔、俺同学都来这开车。”
现在回望,最早来广州的这批出租车司机奠定了当今天河棠下村被称为“河南村”的基础。由于早期定居在棠下的司机多为周口市西华县人,这也奠定了现在棠下村河南周口人居多的现状。
为了换班方便,也为了亲朋好友之间能有个照应,后来的河南司机和家人几乎都选择住在棠下村。靠着村里人和亲戚之间互相帮带,久而久之,棠下村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河南村”。
河南村的男人女人
最爱烩面胡辣汤
得益于棠下村出租车数量之大,棠下村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从业者和“出租车”这个词都有联系。有的是强联系,比如租房子给河南人的棠下村民、河南人开的修车行、还有西华逍遥镇李亚飞开办的胡辣汤店;有的是弱联系,比如王振华夫妻开办的衣物装饰手工作坊。
李亚飞开的富乐祥胡辣汤店,就位于棠下大街,凭借正宗的胡辣汤味道和水煎包、油条、菜角等花样繁多的小吃,开办4年来,生意异常火爆。

除此之外,棠下村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河南烩面馆、羊肉店,还有来自豫东版本的热干面店。来广州3年的扶沟司机老赵说,每天换完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河南饭馆吃点烩面或者喝碗胡辣汤。


如果说李亚飞的餐馆是男人聚集地,那么王振华的衣领加工作坊则是女人和小孩的聚集地。
来广州十几年的王振华和来自重庆的老公结婚后不久,就辞掉工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衣领加工厂。王振华的手工作坊内,常见的场景是五六名妇女围坐在桌子旁给衣领钉珠,边工作边聊一些家常,谁家的孩子学习好,谁家的当家的今天生意好……

小作坊内的工人,多为的哥们的家眷。白天,男人们外出开车,妇女们就在小作坊做点手工活儿,赚点外快补贴家用。作坊计件结账,没有严格的上班时间,也比较方便妇女们照顾家庭。如果孩子们放学看妈妈不在,首先就会到王振华的手工作坊内找寻。
由于户口限制,这些孩子只能在私立学校上学。星期天放假,爸爸在远方跑出租,孩子们在外面玩耍,妈妈在里面钉珠,玩累了,这些孩子也会跑进屋内替妈妈做些手工。

这是棠下村很多周口的哥一家生活的典型写照。
广州出生的“漂二代”
极少能回答出父母的出生地
如今,棠下村迎来了大量的“漂二代”。很多“广漂”父母在广州奋斗了十几年甚至是一代人,这些人在广州组建家庭并拥有了孩子。但这些孩子和他们父母那样的“广漂”一代不同,小孩子们自我身份认知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如果你问这些孩子:“你的老家是哪的?”他们会回答你:“我不知道。”或者“我是广州的。”极少有人能回答出父母的老家在哪个县哪个镇。

以老金为代表的河南人,通过资产积累,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现在不仅职业又回归成了学校校长,更通过买房落户,变成了新广州人。但他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广州,这种成长经历自然会影响其身份认知。

这不能说是个坏现象。这些孩子恰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写照,数百万河南人南下拓荒,棠下村重叠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广州梦”。

棠下村,这个方圆6公里的都市村庄,是在粤河南人的“麦加”。无数人从千里之外奔到棠下投亲靠友,待安定下来再从这里出发,散布到7434平方公里的广州城。通过族群聚集,广州又出现了以做二手家具为主的“河南村”和做服饰为主的“河南村”。
其实这里还是一些在广州的白领以及中产们一解乡愁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房租便宜,老乡多,成了很多河南人在广州的起点。那些大学毕业在这里租房的白领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小企业主,想家了,跑到这里,喝碗胡辣汤,吃点儿烩面水煎包等河南特色小吃。
生活工作感到憋屈了,跑到这里,在路边小店弄几瓶啤酒,整几个小凉菜,光着膀子怼上一顿,半醉半醒的状态下,用河南话吼上几嗓子,想想自己当初来到广州,住在这里的日子,憋屈感慢慢地就减弱了:妈的!有啥啊?大不了从头再来!

棠下的哥群体的奋斗史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以老赵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哥又在重复第一代的哥们奋斗的路。只是现在的出租车生意没有那么好做,“私家车越来越多,滴滴也很强,现在钱越来越难挣,但比在家强点儿。”
有忧愁,有烦恼。但不管怎样,还是要继续奋斗,这就是棠下村的河南人。
豫记版权作品,转载请微信80276821,或者微博私信“豫记”,投稿请发邮件至yujimedia@163.com豫记,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粮!,